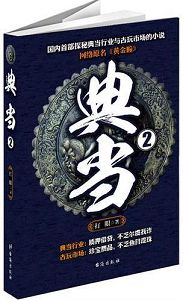薄伽梵歌(黄宝生译本)-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档溃骸叭欢挥姓獠啃?北荆挥邪啻锟ǘ窖芯克澡笪难踝鞒龅恼庖晃按蠊毕祝筒豢赡芑竦谜庵止饷ⅰ!泵拦д卟家捞啬显谒摹赌怕薅唷酚⒁氡镜谝痪淼佳灾兴档溃骸叭绻荒艹浞趾妥跃醯匚铡赌怕薅唷分械氖妨希敲矗鞣焦赜谟《任拿鹘痰难适呛懿煌晟频摹!焙衫艰笪难д叩矣海↗。W。DeJong)则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了解《摩诃婆罗多》,怎么能阐释印度文化?”
而我在翻译过程中,还深切体悟到《摩诃婆罗多》隐含着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与史诗通常的特征相一致,《摩诃婆罗多》中的人物和故事也与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这完全符合史诗时代人类的思维方式。但是,这部史诗并没有耽于神话幻想,而富有直面现实的精神。它将婆罗多大战发生的时间定位在“二分时代和三分时代之间”,也就是“正法”(即社会公正或社会正义)在人类社会逐渐不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这样,《摩诃婆罗多》充分展现了人类自身矛盾造成的社会苦难和生存困境。而史诗作者为如何解除社会苦难和摆脱生存困境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他们设计出各种“入世法”和“出世法”,苦口婆心地宣讲,也将他们的救世思想融入史诗人物和故事中。但他们同时又感到社会矛盾和人类关系实在复杂,“正法”也非万能,有时在运用中需要非凡的智慧。
无论如何,史诗作者代表着印度古代的有识之士。他们确认“正法、利益、爱欲和解脱”为人生四大目的。他们肯定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但认为这种追求应该符合正法,而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追求解脱。他们担忧的是,人类对利益和爱欲的追求一旦失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争斗,直至自相残杀和自我毁灭,造成像婆罗多族大战这样的悲剧。因此,《摩诃婆罗多》是一部警世之作。它凝聚着沉重的历史经验,饱含印度古代有识之士们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深刻洞察。自然,他们的“正法”观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但是,人类自从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历经种种社会形态,生存方式并无根本改变。马车变成汽车,依然是车辆;茅屋变成楼房,依然是房屋;弓箭变成导弹,依然是武器;古人变成今人,依然是人。社会不平等依旧,对财富和权力的争夺依旧,恃强凌弱依旧,由利害、得失、祸福和爱憎引起的人的喜怒哀乐依旧,人类面对的社会难题和人生困惑依旧。所以,《摩诃婆罗多》作为一面历史古镜,并没有完全被绿锈覆盖,依然具有鉴古知今的作用。我通过这次翻译工作,对《摩诃婆罗多》这部史诗由衷地生出一份敬畏之心。
如今,我们有了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汉语全译本,这就为国内学术界提供了研究的方便。新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成绩卓著。最近,译林出版社又出版了一套“世界英雄史诗译丛”,也是对国内学者长期以来翻译世界各民族重要史诗的成果总汇。有感于此,我在为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的《罗摩衍那·森林篇》撰写的前言中说道:“如果我们能对印度两大史诗、古希腊两大史诗、中国少数民族史诗和世界其他各民族史诗进行综合的和比较的研究,必将加深对人类古代文化的理解,也有助于世界史诗理论的完善和提高。”
我在从事《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中,自然会关注国内学术界研究史诗的状况。我发现国内的史诗学理论建设还比较薄弱,尚未对国际史诗学的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二十世纪著名的帕里(M。Parry)和洛德(A。B。Lord)的“口头创作理论”也是最近才得到比较认真的介绍。长期以来,国内学者在运用西方史诗理论概念时,有一定的随意性。而在史诗研究中提出有别于西方理论的某种创新见解时,也不善于与国外史诗进行比较研究,以促进自身理论的通达和完善。这里,我想从“什么是史诗”出发,提出一些值得商讨的问题。
史诗属于叙事文学。叙事文学分成诗体和散文体。史诗采用诗体,属于叙事诗。据此,我们通常把散文体叙事文学排除在史诗之外。例如,《埃达》和《萨迦》都记述冰岛古代的神话和传说。《埃达》是诗体,《萨迦》是散文体。这样,《萨迦》明显不能称作史诗,而只能称作神话和英雄传说集。现在,译林出版社将《萨迦》也收入“世界英雄史诗译丛”,我以为欠妥。至于《埃达》,是称作史诗,还是称作神话和英雄诗集更适合,还可以讨论。
史诗的分类也很复杂。国际上有口头史诗和书面史诗的分类,与此相应,有原始史诗和非原始史诗的分类。口头史诗是以口头方式创造和传诵的史诗,如《吉尔伽美什》、《伊利亚特》、《奥德赛》、《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贝奥武甫》和《罗兰之歌》等。书面史诗是以书面形式创作和传诵的史诗,如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塔索的《被解放的耶路撒冷》和弥尔顿的《失乐园》等。口头史诗本质上是集体创作,经由历代歌人长期传唱,不断加工和改编,最后定型,并以书面形式记载保存下来。书面史诗(或称文学史诗)本质上是个人创作,是诗人采用或模仿史诗形式。因此,口头史诗可以称作原始史诗,而书面史诗可以称作非原始史诗。国内现在似乎将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称为口头史诗,而将古希腊两大史诗和印度两大史诗称作书面史诗,我以为不妥。应该说,这些都是口头史诗,区别在于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是“活形态”的口头史诗。实际上,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史诗现在也正在以书面形式记载保存下来。
帕里—洛德的“口头创作理论”为口头史诗的语言创作特点提供了有效的检测手段。我们在翻译《摩诃婆罗多》的过程中,就发现诗中有大量程式化的词组、语句和场景描写。尽管在字句上并不完全互相重复,但在叙述模式上是一致的,或者说大同小异。这些应该是史诗作者或吟诵者烂熟于心的语汇库藏,出口成章。同时,《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些主要人物都有多种称号,甚至有的人物的称号可以多达十几或二十几种。这些称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这些称号的音节数目不等,长短音配搭不同,这就可以根据需要选用,为调适韵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另一方面,这些称号或点明人物关系,或暗示人物性格和事迹,具有信息符号或密码的作用,能强化史诗作者或吟诵者的记忆,以保持全诗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前后连贯一致。这些都是口头史诗明显不同于书面史诗的语言特征。国外已有学者对《摩诃婆罗多》中的惯用语进行专题研究,并编写了《〈摩诃婆罗多〉惯用语词典》。
在史诗的一般定义中,通常都确认史诗是长篇叙事诗。而现在国内有倾向将在题材和内容上与史诗类似的短篇叙事诗也称作史诗。这在理论上能否成立?如果能成立,那么,我们就应该在史诗定义中去掉“长篇”这个限制词,正如在小说的一般定义中无须加上篇幅的限制词。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国内一些论著中,将《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等诗篇确认为史诗。倘若此说能成立,那么,接踵而来的问题是,在中国历代诗歌中,凡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和英雄业绩的诗篇,是否也都能称作史诗?而且,在世界各国古代诗歌中,也有许多这类题材的民歌、民谣和短篇叙事诗,其中有些被吸收进史诗,有些与史诗并行存在,是否也可以一律称作史诗?这关乎世界文学史中文体分类的一个大问题,应当慎重处理。
说到史诗的题材和内容,西方传统的史诗概念主要是指英雄史诗。国内现在一般倾向分成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两类。创世史诗又进而分成创世神话史诗和创世纪实史诗两类。这主要是依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状况作出的分类,自有道理。但我们应该注意到,这是对传统史诗概念的延伸。在一定意义上,史诗成了长篇叙事诗的指称。由此,我联想到在印度古代文学中有一类与《摩诃婆罗多》同时发展的神话传说作品,叫作“往世书”,也采用通俗简易的“输洛迦”诗体,总共有18部。印度古代辞书《长寿字库》(约七世纪)将往世书的主题归纳为“五相”:一、世界的创造,二、世界毁灭后的再创造,三、天神和仙人的谱系,四、各个摩奴时期,五、帝王谱系。其实,《摩诃婆罗多》中也含有这些主题,但它们交织在主线故事中,并非史诗叙述的主体。所以,同样作为长篇叙事诗,《摩诃婆罗多》的叙述主体是英雄传说,而往世书的叙述主体是神话传说。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将往世书称作神话史诗或创世神话史诗?
我的困惑在于,如果我们将史诗概念中的英雄传说扩大到神话传说,长篇扩大到短篇,诗体扩大到散文体,这是对史诗概念的发展,还是对史诗概念的消解?因此,我迫切感到国内学术界应该加强史诗理论建设。否则,我们在史诗理论的表述和运用中难免互相矛盾,捉襟见肘。中国具有丰富的少数民族史诗资源,而且还保存着许多“活形态”史诗,这些是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我们必须重视对国际史诗理论学术史的梳理,同时,对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研究,必须与世界各民族史诗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这样,在综合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能提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创见,以充实和完善世界史诗理论。在这个领域,中国学者大有可为。
这些年来,我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摩诃婆罗多》的翻译工作中,对于相关的史诗理论问题无暇深入研究。以上只是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论困惑,企盼获得解决。学术研究的要义就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我和我的同事们译出了《摩诃婆罗多》,也就是为国内史诗理论研究增添了一份重要的资料。每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一批甘愿献身于基础建设的学者。这里,我又想起丹麦梵文学者泽伦森(S。Sorensen,1849—1902)花了20年时间编制《〈摩诃婆罗多〉人名索引》,以至他很晚才获得教授职称。然而,他却于这部索引开始排印的当年逝世,未及见到这部厚重的索引(16开本,800多页)面世。但后世从事《摩诃婆罗多》研究的学者都会感谢他的这部索引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部《摩诃婆罗多》全译本问世后,如果能受到国内印度学和史诗学学者们的重视和利用,我们这些年来耗费的时日和付出的辛劳,也就得到回报了。
(摘自《外国文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