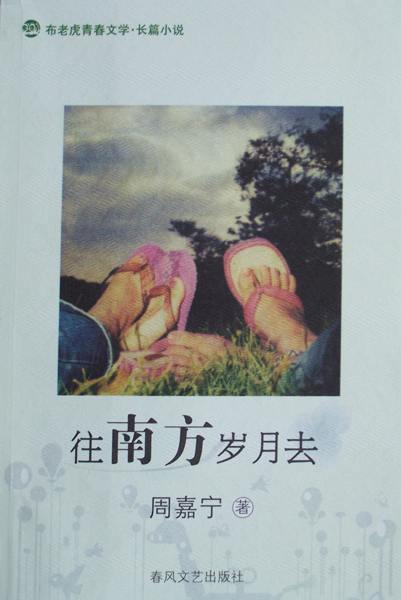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л�:��������-��11��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ˮ����ʮ���굯ָһ�Ӽ䡣�ٶ����������У����ʮ�������ϡ��������ϣ����Ƕ����˸��顣����ʦ˵��������ӡ�����㻹�Ǹ����ӣ�ת�۾��˵������ˡ�����
����������һ�仰����ʹ�������������¡�����ѧ���ã��д�����������ͬѧ�ﴫΪ�������ף�������˵Ū���û���ɵ�ӡ�����ʦ��˵��������һλ��ʦ�������г���ͷ�ظϵ�ҽԺ���ң�����ҽ���㽹�����ʣ����⺢�ӵIJ������������Ӱɣ���ֱ��ҽ��˵ֻ���ظ�ð�����ŷ�������������һ�Σ��ҵ�Сѧͬѧ��һλ������һ����ѧ���к���������һ���ţ���ͬѧ�������ڰ����������ۡ���ʱ����ѧ����Ů֮�����ɭ�ϣ�һ���������ţ����Ի���һ��Ů��������������ʦ��˵������������ʹ��̸�ģ�˵��Ůͬѧ֮��Ӧ�����������������꣬���ض�����ۣ�����ҪС�����������ʦ��̬�ȸı����ҵĴ�����������ҵ�����������Ҳʹ�ҽ����˽������ѹۡ���
�����뿪ѧУ�Ժ�β����ټ���ʦ����ͷ���ֶ�ΰ���ס������������һ�������������Ҽ���������ĺ���������������������������Ϊ����ʮ����ԥ��������������ƽӹ����μ����أ���
����Ȼ�����������¡�ѧ������������������ʦ����������ѧ������������˵����û������ѧ������������Σ�������·��Ҳ��������ѡ��ֻҪŬ���ˣ����ܳɾ���Σ���ʦ������ˣ�Ϊʲô���������أ�����
���������Ҳ���ԭ���Լ��롰�����������������ʦ�������������١����Ը�ο���ǣ��������������ٴ������ʧ֮���ۣ�����Ȼû���Ա�����������˵������ʱ��õ���ʶ���պ����ڷܽ�ȡ�����ž�������ѧ�������ġ�Ƥ��������ЧӦ���ɣ����ҵIJ��϶��䣬���ºܴ�̶��ϵ����ڵ�������ʦ�ļ�������
�����ټ���ʦ��ת���������꣬���ڼ��ȥ������һ�Ρ����������˺ܶ�óԵĿ���ң�����ֻ���˰�Сʱ��ȥ�Ӱ��ˡ�������������������������æ������ʦ���ݺ��������ʦ���У���ʱ����Ϊ��λ������ǩԼ�ĺ�ͬ�����Ǵ�绰�ֽ̡�����ʦ���������������ѣ�һλ������ʦһͬ��ı���ߡ�������Լ����λ����ɽ����������ʦ������ʱ��ԶԶ��������ʦ������·�ߵȺ�����̸�˴�����������㽨�����²��ϣ����������о���д�������������ʱ������Լ��һλ����ȥǰ�Ű��£����ǴҴҸ�ǡ�������
������ʦ�縸��2��������
��������ʦִ��Ҫ���ҡ��ƴDz�����ֻ�������������г������߱��ġ�����������ɽ���ĺ�ǽ���������֣����Ų��������ţ�����Ȱ����ȥ���������ϡ������£��ҷ������IJ�̬�Ѿ���Щ�ٻ�������Ҳ�Գ����ϣ������Ǵ�ǰ������������ӡ���
����ֱ���߹��찲�ţ�����ֹ��˵������ȥ�ɣ�ƽ���������ۣ�Ҫע�����塣����
���������ˡ��������ף������ڷ����վ�ţ����½���綶������һ�����ġ���
����������ڵ�λ�ӵ��շ��ҵ绰��ԭ������ʦ����������һֻ���Ӻ�һ���ţ��ĺõĺ�ͬ��װ���ŷ�����ڻ��������ʯ������֪����ϲ��ʯͷ����
���������Ҵ�绰������������ʦ���Ƿݺ�ͬ���������Լ�ȥȡ�ģ�������������������ⲻȥ������ô��˳�㵽�칫�������أ�����
��������æ���ҾͲ������ˡ���ͬ��ȥ���µ������á�����ƽ�����º͵ػش𡣡�
�����ҵ���ͷһ�ȡ�Ϊ���ҵĺ�ͬ����������죬����һλ��ϡ���˶��������г������Ǹϵ����ǡ���Ȼ��������ȥ��ʦ�������ߵô�æ����Ȼ��һ��С����Ҳ��������������
�������ã�����ͨ���շ���ת��һ���������ң�������һ������װ�ѵ��IJᡢһöӡ�º�һ���š���æ���ſ�������ʦд������������һһ�������еĻ������ˡ���˵����ÿ�ο���������£����ﶼ�dz����ˣ���ʱ���Ҫ��д��������˵����ӡ�̵ò��ã��ò������������ˡ��Ժ��к�ʯͷ������һ�����㡣�����IJᣬ�����ҷ�������һЩ���£���ö��������ӡ�£������Կ����ҵ����֡��ɷ���������š��IJ��ӡ�·�������չ�ȥ�������ò�˵���������ʦ������ð�������
����д������������Ǻþ�û������ʦ�ˣ���˵æ���绰�����ٴ�ż��дһ���ţ�̸������Ҳ���Լ������ǴҴҹ�ͨһ���绰����֪����ʦ��Ȼ��æ������Ӧһ����־֮Լд�������ʽ��������£��������ң�������ˡ���֪������Ը������ѧ������Ϣ������������һ������˵��ijλ�������˵�ѧ����Сʱ��Ҳ�ǻ�����������Ѫ�ģ������������ƺ�ҵ�Ѳ��ǵ��Լ�����ʦ���Ƿ���д�ú��˸У������м���¶��Щ��ʧ������
����ʦ���縸�ӣ�Ů������ʦ��ѧ����ֻ�и�����������ر������ѧ����������������Բ�м������ʦ����������������֮������Ը������ѧ���ģ����ܹ������ͻ���µµ��Ϊ������Ҫ���DZ����������ˡ�����ѧ��ǰ�̽��壬�Լ�ȴ��һ���ӷ۱�ĭ����ʦ����
������������ʱ���������Ѿ���ɫ�����������Ȼ�ڷ����ղ������½�����Ϊ�˻ر���ʦ��������
������ϯ���ˡ�����
�����й��ִ���ѧ�ݸ��ݳ��������绰�������Һ������μ�һ�������絳�ľۻᣬף�س���ʵ�ġ���¹ԭ����é����ѧ�����ص������������ڸ�����һ�ҽ��ӹݣ��ϰ�Ҳ�������ˡ���
�����Ҳ��������ˣ���������������ʱ����������������˻�����������ˣ�ʹ�Һ��Ѱ������ֻ�����ᣬ�Ͱ��Լ����������ˡ����ǵ�ʱ�������ѱ�ռ���ˡ���ڽ�ɽ������֪�������ǵ��������羿���ж��٣��ܾ�����Ƭ���������������˺����׳�Ϊ�Ļ���Ӣ�����۴������������٣�����ʶ�Ķ࣬��λƯ��Ůʿ������һ��ɢ����Ƭ����û����Ƭ���������ij���֮�ӣ�����һ���������£����ÿ��ˡ���
��������������ģ���������Ϊ�ڶ����֣�������ʹ�����ԺԺ��������������ʱסͬһ��Ͳ��¥�б���Ŷ�����������ӷ�ׯ����������������ᵽ�ϳǣ����ǽ��ڡ�֣������Ϊ��Ա������ѧ�ʣ����С��Ļ���������������С����飬��³Ѹ�����о�����
��������עĿ�ij���ʵ������עĿ������һ�����˽�̸�������͵͵ģ�Ŀ��������Ϲ��ų�˼��˿�����������ϲ�����ư��������ҵ�ӡ������Dz��س������ġ���¹ԭ�����ܴܺ�����
�����˽�����ʱ�������������١����������������죬���ŵ��ȳ�����Ե���ã���һλ��̳����������ҵ��ʱ��ϲŪ��ī�����������ֽ̣����ԡ���ʦ����֮��ÿ�μ��棬���������Ѻ����Ҷ�д��Ҳʹ�ҳ�Ϊ�Լ��۸��ֵ͡���˵���������ա���
�����й���Э����ϯ��������Ҳר�̵����������ʵ��ʾף�ء���ǰ��������Ʒ���ܸо�һ�ֺ�Ȼ֮�������ּ伤�����������ģ�����������ΰ�����DZ����á���˵�������������ë��ij�γ������ʣ����������̳�ְԱΧ��Ҫ���Ӱ����
����ϯ��ܻ�Ծ�İ��裬Ҳ��һλ��������̳��Ū�����������������ҡ����ġ������ഺ���͡��������졷�����Թ��ߵ����ݣ������������˵������±���ӵı���֪�࣬��¶��һ�����˸ж������Ĺ�ע����ϧ��û�ж������������Ʒ����
������ɧ�����͡����ˡ��߳����е��ϴ�Ҳ�����������࣬�������ء����ƺ���һλ���й���ͳ�Ļ�Ӱ�����Ĺ��ˡ���������ֻ����һ�������ԵĻ���ζ����
������ϯ�����ģ����б��������������༭����ӱ�������������֪����һֱ����ʶ���ˣ���ϧ��ʱ����֪������û�������������������ᡣ��
��������֮�⣬����һλ��Ծ���ר���Ļ�������Ӱ��������Ӱʦκ���ˡ�Сκ������˵㣬�ڿ�����˵Ҫ����Ʒ˵������Ƭ�ӵ�ȷҲ�ĵ�Ư���������ڲ������˲����̬���ر���ù⣬�Ƕ�Ҳ����������ϲ����һ�ţ��Ǽ�����������Ф�����ϼ��϶�������ǰ��һֻ��è��������Ծ�£�һ��һ����һ��һ������ͷ���Ծ�տ������Ӱ���õ�����������һ�ܹ����ɡ���Ÿ������������һλ������˵���������ֻ��Ӷ����ij�����Ƭ�����������¥�ˡ���
����һ�����ϵĿ��ˡ���٩���۾����䶼�����С���ʵ��һ��Ҳ�Ǻ�Ϊ��ʦ�ģ������˽�Ϊʦ�ij��ϣ�������İ취���dz�Ĭ���ź����ǣ���һ�ξۻ���ʶ����λ���������֡��������ָٺ�ʫ��������δ����������ɿ��������ĸ��ࡣ��
�������ٱ�ʱ���ϴ�˵������¹ԭ��Ϊ��ʮ�����й���̳����һ��Բ���ľ�š�������
����������ӡ��1��������
�������ӳ�վ������ʮ������䣬���ĸ����߸˶��ŵ�����¥���ǣ����ƺ��롭�����������ڵ绰�������ȥ���ҵ�·�ߣ�����������˺ܶ࣬�������������߱��ˡ���
��������䡢����ˡ���¥�ݣ�����¥�������졣����������һ������ӭ���������������Ҳ�����������һ�ӡ�����
���������˽��š�����û�̵�̺��̫���ˣ����û�Ь����
�����������Ӳ裬�������ܣ�һ��ɳ����ǽ���裬������СԲ���ϰ�����ͷ��С�˺�����������˵������ĸ�����ӿ������ԣ���û�й��ϳ��緹�������������ӣ�ͦ�����ģ�����һ��ůů�Ĺ����ӵ�ζ������
������һ��Ѱ���˼ҡ���
����������������������֮ʶ��������һ�ι��ڶ�����Ů��������̸���ϣ���Ϊ������ͬ���˺Ͷ�����Ů�ҳ����������ķ��Ը�����������̵�ӡ����������һ����־��֮�У���дһ������ƪ���ڹ�ע�����ķ�̸�����Dz�ͨ�����ĵ绰����
����ȥ�������죬��һ���������ڵ���ĩ��������������в�����Щ��̤ʵ�����ÿ������ż�ɽ��š����ñ����������¼�����ʣ��������𣿡���
��������Ȼ���ԡ�����������ȻӦ�ʡ���
����һ�߰��ղɷüƻ�˵����Щͦ�۵Ļ���һ�������������߽���һЩ�������һ����һ�����⣬���������Ӳ�������������������
�����Ҳ�ϲ���Աس�ʦ���ر��Ƕ�ͬ���ˣ���ֱ���������������ʣ�������˵����ƽ�����ң���ͬ��������˵���𣿡���
����������Ц�ˣ�������˵û��ʲô���ã������Ҿ��Ǵ���Ժ�ﳤ��ģ�������ӡ�����
����¼���ĴŴ�ɳɳ��ת���ţ�����ְ�ء���
����̸���ܱ���ϣ����Ǵӿ���һ����Ĵ���ɽ�һֻ��Ӭ�����������ִӴ�̨������һ������һȦ�첼������ɴ�������������ȥ�������ֲ�Ӭ�����������Ѿ����ټ�������һ�ᣬ��������ȥ�ӵ绰�����»�Ͳ������һ����С�������������ҵ�С��ķ�����ɵ������Ǿ���Ϥ�ĸ�ʣ��������и������С�����������ţ��������ţ�����һ��Ů������С��˵˵ЦЦ�������ݡ�������˵����¥�¿�����Ů��������С����ġ���
��������ʰ��ղŵĻ�ͷ��̸����Ʒ�������������Ƿ������ġ����ȡ������Ҳ���ôϲ�����������ź���û�п��������һش�������˵������ǰ��Ҳ��ϲ����������Ʒ������������Ȼ���������������ض������ȡ���ȴ�������ණ����Ҫ�������⡣����
������̸�ţ����������š�ԭ����һ�ҳ�����������Ҫ���ҵġ����ա�������������һֽ�л�û����������Ƭ�����ڲ輸�Ϲ���ѡ����������λС����һ�߷���һ�鿪��Ц��˵��������ʦ������ЦһЦ�������е���Ƭ����������ü��һ��������������ӡ�����
����������ֻ��˵�����Ҳ������࣬û�к���Ƭ������
�����ҳû����Ҫһ����Ƭ�Ա�����־�Ͽ��ǣ�����Ӧ�ʣ��ֵô���ߵ��ͳ�������ʣ�������һ�ſ����𣿡������ԣ���Ȼ���ԡ����������ش𣬲��ܾ��ҵ��κ�Ҫ��
�����ɷý���ʱ����˵��������д�ɺ�һ��������������Ŀ������
���������أ����أ����ȫȨ�����ɡ���˵�ţ���ȡ���Լ���ɢ�ļ�����ǧ˵����ǩ�����ң�������ɫ����������һ����������û����˼���ݵ�Ը������������Ũü��̹�ϵ�Ŀ�⣬��������˵������������̫�ƽ������ˣ���
�����ܶ��˶���Ϊ�������������˵��������DZض��������˸�ɽ��ֹ�ġ�������������������ȴ����Ҫ���ӡ��Ҿ���֪����������Ҳ������������ƽ������
�������ô�������ǡ���֪��Ϊʲô��ͻȻð���������ĸ����ͷ������֪������������λƽ�����ҵģ���һλ������ĸ�ף���������������˻�ȥ���뵽���˼ҿ�����Ͷ������緹���������ϳԣ����ֺαش������������أ���
�����ڡ���ǧ˵�����У��������Գ����������ں��˱��ϵġ�һ��˼�����䡢���ŷḻ���������������飬�ڱ������﹦�����͵����ң��������������ijɾͺ��������Ҿ�����������������һ�����ˡ�������
����������ӡ��2��������
���������������������������������̵�ӡ�����ֵ���ʱ������������˵��һ�仰�ǣ�����һ��ƽ����������
�����ҵ��������ѡ�����
�����������ںܾã�ֱ��1999��ŵ��Գ��С���
����5�����һλ���������ڻ��ݵ�һ�������������طꡣ�����к�ʱ���Ҿ��������һʱû�����������֡�����ô�������Ѷ����ˣ�����Ц���ʡ�����������������˵����ֻ��û���뵽�����������ˡ�����
����������λ����ֻ��һ��֮����ȴ�ܡ��ɡ�������ǰ���ڰ��ղμ�һ�����վ�������о�ѧ���ᣬ���ͬ�λ�ɽ������ϸ���������뵝�������ɽ���齥��ϡ���������춼����£�ֻʣ��������Ů�����Ե��������춼�壬����һ���ա������Ǿ���ð��ͻ�����塣����һ�����������������������Һ�����������ʿ֮һ����ǧ�˰�̬�Ļ�ɽ�����Dz��������ˡ���ɽ����������������Ȼ���ۣ�Ҳ������һ�η����в�����ʵ����顣��
������˵�������ѵ����㶫��˳��ȥ���ڿ����ɣ��ҿ��Ե����μ���Ӱʦ���úþ�һ�µ���֮�ꡣ��ʢ����ȴ���Ҵ�Ӧ�ˡ�������֪��������ĸУ�ڻ��ݣ�ʮ����û�������ˣ����ԭ������ͬѧ��һ�۵ġ���
�����ڶ���˴�ͳ��������졢�̺�����������ɳ��һ�ɱ��������������ȴ���⡣��ƾ����������С�֣�����һ��Ц�������ںܺ��棬ϸ������Ҫһ�����ڣ���ϧ��ֻ��һ�졣�������һᾡ�����������ź�������
�������ι۹��ʿ�����ϴ����ʻ��;���������ã���ó���ã�ֱ���߿ڹ�ҵ������һ·��̸�˰�Ȼ������֪Ϊʲô��������������Ȼ���ij��������棬����ȴ���á���
�������ڵ�֪������ǰ�����˻���һ���ز�����δȬ�������DZ��������ߺ������죺�����ɽ���������ڣ��پ��Ǵ������˵IJ���̸�����������룬�ܰ���ɢɢ��Ҳ�ð�����
������ȥ������ȫ��ȥ�������Σ����ſɸ����ˡ���ȥ�ĵط����ࡣ�ҹ���̫æ����ʱ�������棬������������棬���ٹ˵����Ͷ��ӡ����������˵����
�������Ժ���ỹ�ֻ࣬Ҫ���ˣ�һ����ʲôʱ���ȥ�治���أ����ҿ�ο������
������Ҫ������û�в���ã�����Ըʲô��û�У�û��Ǯ��Ҳû�з��ӣ�ֻҪ����һ�������塣�㲻֪�������������۵�˯���ţ�������һҹҹ�ؿ����Ҽ��ϣ���������������������̾��һ��������
�������Ǵ���Ҭ�֣��߽���ͷ��ӭ������ĺ��磬��������ʱ���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