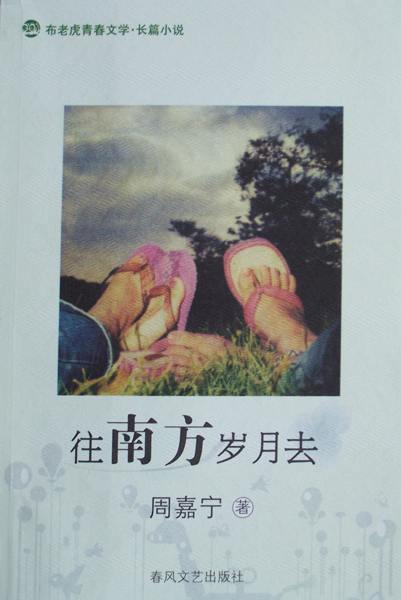岁月感怀:境由心造-第1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了一批年货,苹果、花生、瓜子什么的,让西医二院的职工享受和我们一样的“福利”。那时候副食品非常匮乏,我的一次失误,换来皆大欢喜。以后,我们系统的患者,无论转院、会诊还是找专家看病,只要我出面,全能搞定,由此赚了个“外交部长”的美誉。
蔡澄教授后来成为西安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当年有一次上夜班时,他曾亲手抄写过一张歌片送我,是当时正流行的西哈努克亲王谱写的一首歌:“敬爱的中国啊,我的心没有变,它永远把你怀念。”字迹非常工整、漂亮,那张歌片我至今保存完好。
我在西医二院结识的另一位长者是病理教研室的陈金典教授。他是河南人,身材不高,举止儒雅,眼镜片后面闪烁着睿智的目光,一见面就愉快地对我们微笑,听他说话别提多有意思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2)
我的第一堂解剖课,就是陈教授上的。他的第一句话是:“同学们,请大家肃静、向遗体捐献者行注目礼,以表达我们对他的尊敬。”站在阶梯上的一排排学生,一下子安静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在解剖课上说话或做小动作。而我上其他课,从来都是一心二用的。
白被单下覆盖着不知名的遗体捐献者。随着课程的进展,白被单被掀开,露出死者的遗体。从头颅、躯干到内脏,陈金典一边解剖,一边用低沉的声音从容不迫地讲述,被单始终遮盖着死者的耻骨联合部位,给他留下最后的尊严。
讲到取肺叶组织标本时,陈金典一句话就说明了原则:“上小下大,左三右四。”就凭这八个字,即使到现在,只要看一眼大小不等,被切成三角或四方形的肺组织标本,我就能准确无误地辨认它来自哪一片肺叶。由于景仰陈金典的缘故,我非常重视这门课,晚上经常一个人在解剖室观看各种标本。一次,放射科杨荫清教授读片回来,路过病理科,看见灯光下只有我一个人,面对泡在福尔马林中的人体器官研读,大为惊讶。从此我与杨教授交往渐多,进放射科也如履平地了。
再说陈金典。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堂“爱情课”,也是他讲授的,当然不是公开课。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在某县地段医院工作的进修医生,看上了一位也在进修的北京姑娘,我的好朋友。这位姓项的医生害上单相思以后,不知怎么被陈金典知道了,他鼓励说:“追,一定要追!”他的理论是,爱情就像做学问,穷追不舍才能成功!据说陈夫人郭真教授就是他当年千辛万苦、不屈不挠地追到手的。名师出高徒,尽管开局不利,那时候几乎全中国的女孩都不爱上海人,我的朋友很是犹豫。但好事多磨,项医生展开猛烈攻势,坚持不懈,到底追上了自己心仪的姑娘。后来他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的研究生,又到美国读博士,现已成为一位知名的病理学专家,在加拿大一所大学医学中心任终身教授。对于项医生来说,陈金典不仅是他专业上的导师,也是成就他美满婚姻的教父。
尽管我当时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但陈氏爱情理论让我懂得,凡能执著追求爱情的男人,也能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做成功。等到我自己“遭遇”爱情的时候,也着实被后来成了我先生的人狠狠地追了一把。几十年的生活实践,检验了陈氏理论的货真价实!
孙浩远是我们医院的医务部主任,内科医生。他身板笔直,表情威严,看上去更像一个骑兵团长。那时他四十岁,恰是一个男人雄风正健的年龄,虽然他是军人出身,却十分爱整洁,夫人大约是很为他的长相骄傲,天天从里到外,把他的每一件行头都熨烫得平平整整,出来进去的,格外精神。要是再穿上警服,那才叫一个威武。
和他交往,你会知道什么是坦诚正直。有一次我问他:你兵当得好好的,怎么学医了呢?原来,他出身贫苦,解放战争时期,一支队伍从他家乡经过,他瞒了年龄去当兵,为的是能吃口饱饭。部队一路南下,所向披靡。他回忆说“:三大战役之后,部队都打疯了,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有时候整团整师地缴枪,当了三年兵,一路上光受降了。”不久,全国解放,首长一问,才知道他刚十六岁,就说:“仗打完了,你还这么小,念书去吧。”于是他上卫校,成了一名军医,后来转业到我们医院。
据说他有八两到一斤的酒量。有一次过节,我们三位女将以水代酒,轮番出击,他对我们的捣鬼全无戒备,三下五除二就被灌倒了。不过,平时他还是很有两下子的。
别看他小时候没念过几天书,学历不高,但是人绝顶聪明,医术相当高明。他的原则是调整人体自身的抵抗力,能不打针就不打针,能不吃药就不吃药。特别是对诊治一种叫做克山病的地方病,很有一套。西安著名的心内科专家王世臣教授不止一次地对他的学生说,诊断和治疗克山病,新安医院的孙浩远医生有着令人钦佩的丰富经验和独到见解。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3)
有一年陕北发洪水,医院组建了一支医疗队,他任队长。那次医疗队本来没有我,但我钻了一个空子,由于院长惧内,我搬来夫人说情,顺利地站在了整装待发的队伍里。那次行动非常艰苦,我们开始乘车,路被洪水冲断,于是步行,走了一百多华里才到达灾区。路上,驮着药品、医疗器械的马陷到泥潭里,正在众人不知所措的时候,只见孙浩远大吼一声,跳将起来猛拉缰绳,硬是把马拉了上来,大家一片欢呼。我们在灾区巡回医疗的十多天里,孙浩远带领大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积极救治伤病员,出色完成了医疗任务,表现出超强的坚忍和定力。
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友好而单纯,在我成长时期,还结识了秦兆寅教授、毛履真教授、叶明刚教授、上官存民教授等名医,他们对我学习专业知识和学习人生经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正当年,而如今,他们中最年轻的也已年愈古稀。
我衷心祝愿这些令人尊敬的长者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小辈篇
渐渐进入中年,我也到了长者们当时的年龄,开始有了小辈朋友。也许,由于当今是一个后喻文化时代,也就是老辈应该向小辈学习的时代。小辈朋友能教我年轻、教我时尚,教我更加适应社会的变革。
交往时间最长的小友,是我曾经的同事李源,一位比我年轻十五岁的白领丽人。我们认识的时候,她刚从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我们医院妇产科。据她后来说,报到时,发现科里尽是老职工,很是失望。路过当时我所在的理疗科,看见我正激情四射地与人讨论问题,近视眼却不肯戴眼镜的李源朦胧望去,错把我当成同龄人,旋即加入谈话。等到看出我足可当阿姨时,我们已经相见恨晚,聊得热火朝天。后来,李源成了我最投缘的聊友。
那时候,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已经感到适应社会发展的速度有些力不从心,而年轻的李源带着通身的活力和令人眼花缭乱的信息,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她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生活态度不时感染着我,看外国大片、听流行音乐、读武侠小说,时尚文化元素的充值, 打破了我的固有娱乐方式,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内经济开始崛起,外企如雨后春笋,人们开始面对更多选择。虽然在一般人眼里,能进我们这种吃皇粮的单位,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我看出李源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李源思想活跃,意识超前,言行率真,聪明但不够有耐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医生”。也许她应该尝试不同的生活?我知道她英语非常好,拿过学校演讲比赛第一名,于是建议她应聘杨森,或者史克,辞掉公职。“那种环境可能更适合你。”我鼓动说。为了提高成功率,我悉心研究了当时手头仅有的资料,尽可能地了解外企的用人原则,为她量身定做了一套应聘方案,并客串人力资源主管,模拟招聘。
正像我所期待的,李源顺利地进入外企,后来又考上MBA。目前,她已在新加坡定居,从事卫生标准化管理工作,业绩突出。可以说,李源是我最早的小字辈“导师”,也是我在个人职业发展规划方面成功“培训”的第一位学员。
小友毛宏,最初是我的病人。这位当过武警,活泼好动的小伙子十分讨人喜欢。那年他因小臂骨折,复位后到理疗科接受康复治疗,于是,小毛、我的同事、针灸医生殷凤琳和我,渐渐成为聊友。我们的“锵锵三人行”热烈而持久,每天一次,什么都聊,但好像主要是互相说服对方,各自喜欢的东西最好。
现在看来,这种无意识的互通有无,使我获益匪浅。如我仅有的足球、武术、兵器等方面的常识,就是小毛给灌输的。我也经常动员小毛听音乐、读小说、看展览。有一次我和老殷带小毛听了一场俞丽拿、李坚母子的音乐会,善于在球场上折腾的小毛在音乐厅像一个受气包,整场一声没吭。出得门来大喊一声,妈也,可把我憋坏了。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4)
手臂功能康复后,虽然不再理疗,但小毛只要来医院办事,就会到我这里坐坐。他工作的机械厂,离医院仅一墙之隔。有一次,小毛突然跑来,神秘地说,我在韩森寨发现了一个“炸弹”!所谓“炸弹”,就是漂亮姑娘。这个年龄的小伙子,正是迷恋“炸弹”的时候。还有一次,小毛正眉飞色舞给我们讲述他在球场上的壮举,门突然大开,一个身体壮硕、表情严肃的男人站在我们面前。刚还倍儿欢实的小毛突然蔫头耷脑,溜墙根站得笔直。我定睛一看,“毛局长!”局长没应声,喝斥小毛:“一大早不赶紧上班,在这胡谝什么?”吓得小毛头都没抬,一溜小跑不见了人影。我一看表,还没到上班时间。
原来小毛是老毛的公子!其实毛局对下属相当平易近人,只有小毛见了他像耗子见猫。得知我和小毛有交往,老毛特地嘱咐:“多帮帮他,这孩子不爱念书。”
小毛至少小我十三四岁,但不知道为什么那样谈得来。这种“乱弹”持续了好几年,直到小毛结婚,生了一个像他小时候一样淘气的儿子。那时我也开始办理调离手续,和初为人父的小毛就很少见面了。
闵燕是我调回北京后结识的第一位小友,和我相差十岁左右,当时刚及而立之年。她是一位优秀的眼科博士,学识渊博,手术尤其精湛。我们是书友、文友兼艺友。每当有喜欢的书,闵燕总是积极地推荐给我,并且热烈等待我看完后和她讨论。记得她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南怀瑾先生的《谈历史与人生》。
一开始,她并不知道我有“借书不还”的不良习惯——不是我想占小便宜,只是喜欢的书舍不得还,一般情况下,我会在自己买到这本书时再还。闵燕性急,见我老不还书,又不好意思催,只好自己再买一本。其实爱书的人都有点毛病,别人向我借书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借,如果对方真是爱书人,我宁可买一本赠送。
后来,我们两人之间再借书,就有了“不许看到眼睛里拔不出来;不许一天到晚老看不还”的“契约”。
我们热衷于文字游戏。开始是汉显寻呼机,后来是电子邮件,再后来是手机短信,互发自创的段子、诗词或者对联。有一次,我从崇文门上地铁,车至宣武门,忽然觉得北京有很多地名极妙,就想了一副对联:天坛地坛日月坛,崇文宣武。遂发给闵燕,她反应真快,马上传来下联:白班夜班轮转班,费心劳神。接着又一条:内斜外斜垂直斜,瞄左膘右。原来是她的小友田蓓所作(闵燕在交我这个“老友”的同时,也交着自己的“小友”)。我看后大惊,后生可畏!还没完,过了两天,闵燕发来绝对“烟锁池塘柳”,求“炮镇海城楼”之外的下联。细看,真绝了!五个字偏旁包括“金木水火土”,明知数百年来多少人为它绞尽脑汁,还是忍不住进入又一轮的苦思冥想。
闵燕的专业是眼整形,这是一个“用血肉之躯重塑美”(闵燕语)的行当,需要良好的艺术感觉。出于对美术的兴趣,我们的游戏还包括摄影和电脑绘画。我曾为她的几十幅摄影作品写过短文,她也为我的文章配过电脑制作的彩图。我们还计划出一本“看图说话”,部分稿件送出版社已经好几年,可惜由于太忙,至今没有腾出时间补充稿件出版这本我们自己的书。
还有一位小友,是年龄小我一轮的蒋芫苇,她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广播电台记者编辑兼主持人。开始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合作一挡健康节目,她主持,我做嘉宾统筹。大约在七、八年前,我们一起去香港考察一个健康教育项目,随之熟悉起来。后来节目调整,不再有工作关系,成为纯粹的朋友。
我们之间的交往很特殊,平时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不打电话也不见面。差不多过个一年半载,必有一次长谈。由于平时都很忙,见面只为一个目的,彼此需要。
十多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形成代沟,我们有太多相似的感觉,太多一样的爱好。有时候积攒的想法多了,就打电话相约去喝茶,八大处、紫竹院,都是我们的据点。不聊则已,一聊就是几个小时。满脑子的想法被茶水浸润,变得像开水沸腾,喷薄欲出。经常一起来的还有小蒋的同事小隋,他常常一言不发地听我们热侃,不但充当忠实听众,还兢兢业业地兼职开车,负责买单。就像是一个奇迹,我们每次神聊后,都会获得灵感,建立一个良好的状态,我相信,不久前的那次长聊,将使我和小蒋的精神面貌面临新的提升,为下一次见面酝酿出精彩话题。
少时识长者 老来交小辈(5)
一年又一年,在生理年龄渐渐老去的时候,感谢小友们带给我无限的活力,使我在生命过半的时候,心理尚未衰老。
有意思的是,在女儿长大以后,我的一些小友渐渐变成了她的“老友”。除了几位记者朋友,还有李源。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达到不需要我牵线搭桥的程度。为此,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我的心是一面镜子
《》,是季羡林大师的一本散文集。我手里的这本书,是季老赠与我的同事柴洁医生的。书中收录了季老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写的近六十篇散文。封面上,睿智的老人在一叶苍绿中向我们微笑;扉页里,有他亲笔题写的一行遒劲大字:感谢柴大夫,季羡林,2000年5月。
这本属于柴洁的书,我已经珍藏了几年,使我有充裕的时间品味其中的每一篇文章。“谁的心都是一面镜子”,季老这样告诉我们。读书时便有了“我心如镜”的感觉,它照出光明,也照出阴郁;照出崇高,也照出世俗。而放下这本书,更觉得此时我的心像一条被某种思绪编织的带子,并且是一条漂浮不定、两头没有着落的带子。
柴洁医生与季羡林教授的关系是一种偶然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医患关系。2000年,季老因患白内障住院,作为著名眼科专家施玉英的助手,柴洁在季老手术期间,极尽一名医生的职责,给季老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季老尊重这位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多的年轻医生,为了表示感激,意将这部散文集签名赠送。不巧,柴洁医生出国深造,于是季老请我转送,季老说:“施教授我已当面致谢,送柴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