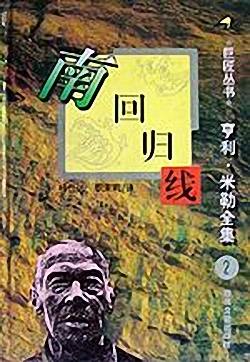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1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声。她挥舞着帽子、哼着歌儿走掉了。这是能整治你的婊子!睡起来倒还不错,我
想我喜爱她还要胜过我的处女呢。可跟一个对此根本无动于衷的女人睡觉是一件邪
恶的事情,直叫你的血发热……”沉思了一会儿他问,“若是她有点儿感情,你能
想象出她会是怎样的?”
他又说,“听着,我要你明天下午跟我一道去俱乐部……那儿有一场舞会。”
“明天不行,乔。我答应要帮卡尔帮到底……”“听我说,别管那个讨厌的家
伙!我要你帮我一把,是这么回事,”他又用双手比划开了“我搞到了一
个女人……她应允在我不上班的晚上来跟我过夜。可我还没有完全掌握住她,她有
一个母亲,你知道……算是一个画家之类的货色。每一回见面她都要唠叨个没完,
我想实情是当妈的吃醋了。若是我先跟这个妈睡一觉她就不会介意了,你明白这类
事情……总之,我想你也许会乐意要这个妈的……她还不错……若是没有看见她女
儿我自己也会考虑要她的,女儿年轻漂亮,一副水灵样儿你明白我的意思了?
她身上有一股纯洁的气息……”“你听着,乔,你最好还是找别人去……”“唉,
别这样!我知道你对此怎么想,我只是请你帮我一个小忙。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甩掉
那个老女人,我想先喝醉酒再躲开她可我认为那年轻的不会高兴的。她俩都是
缠缠绵绵的女人,从明尼苏达州还是什么地方来的。好了,明天过来叫醒我,行吗
?否则我会睡过头的,另外,我要你帮我找一间房子,你知道没有人帮我。给我在
离这儿不远的一条僻静的街上找一个房间,我只有呆在这儿了……这儿,让我赊帐
。你得答应帮我做这件事,我会时常给你买顿饭吃的。无论如何你得来,跟那些蠢
娘儿们说话急得我要发疯,我要跟你谈谈哈夫洛夫洛克·霭理士。老天,我已把那
本书找出来三个星期了,结果一次也没看过。人在这儿就跟烂掉差不多。你信不信
?我从来还没有去过卢浮宫,也没有到过法兰西喜剧院。这些地方值得去吗?
不过我看这也能多多少少叫人别胡思乱想。你整天干什么来着?
不觉得无聊?为了跟女人睡觉要干什么?听我说……到这儿来。
先别走掉……我很孤独呢。你知道吗?这种状况再持续一年我就会发疯的,我
一定得离开这个鬼国家,我在这儿无事可做。我明白现在在美国叫人不痛快,反正
都一样……可在这儿人会疯掉的……那些下贱的蠢货整天坐着吹嘘他们的作品,所
有这些人都一文臭钱不值。他们都是潦倒失意的人,这才是他们来这儿的原因。听
着,乔,你想过家吗?你是一个有意思的家伙……你好像还喜欢这儿。你在这儿发
现什么了?但愿你能告诉我,我真心希望能不再想自己的事情。我心里乱极了……
好像那儿有一个结……我知道我快要把你烦死了,可我一定得找个人谈谈。
我不能同楼上那些家伙谈……你知道那些狗东西是什么货色……都是写署名文
章的人。卡尔,那个小滑头,他自私透顶了。
我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可我不自私,这是有区别的。我想我是一个神经病患者
,我无法不想着自己,这并不是我认为自己重要……只是我无法去想别的事情,就
是这样。如果能爱上一个女人或许会好一些,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对我感兴趣的女人
。我心里乱糟糟的。你看出来了,是吗?你说说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处于我的位置
怎么办?听着,我不想再强留你了,可你明早得叫醒我一点半怎么样?你
若替我擦皮鞋,我还会多给你一点儿。还有,若有一件干净的替换衬衣,也把它带
来,行吗?见鬼,那件活儿都快把我累趴下了,却连一件干净衬衣都挣不来,他们
对待我们像对待一群黑鬼一样。唉,算了,见鬼!
我要去散步……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出来。别忘了,明天!”
同这个叫伊雷娜的阔女人的通信一直持续了六个多月。最近我天天都向卡尔汇
报,好叫这场恋爱开始,因为在伊雷娜那方面这件事可以无限期地发展下去。最近
几天来双方都写了雪片似的大批信件,我们寄出的最后一封信几乎有四十页厚,是
用三种语言写的。这最后一封信是一个大杂烩;其中有旧小说的结尾,有报纸星期
日增刊上摘抄下来的片言只字,有重新组织过的给劳娜和塔尼亚的旧信,还有从拉
伯雷和彼脱罗尼亚作品中胡乱音译过来的片断,总之我们都把自己累坏了。最后伊
雷娜决定要同这个通信人谈谈了,她终于写了一封信通知卡尔在她的旅馆里碰头。
卡尔吓得屁滚尿流,给一个陌生女人写信是一码事,去拜访她、同她做爱却完全是
另一码事。到赴约前最后一分钟他仍吓得发抖,我不由得想自己恐怕不得不代他去
了。我们在伊雷娜住的旅馆前下了出租车,卡尔抖得很厉害,我只好先扶着他沿这
条街走了一会儿。他已经喝下了两杯茴香酒,一点儿作用也没有。一看到旅馆他便
快垮了,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有一个又大又空、英国女人可以呆呆地在里面
坐好几个钟头的大厅。为了提防卡尔溜掉,服务员打电话通报他的到来时我一直站
在他身边。伊雷娜在家,正在等他。他跨进电梯时又绝望地瞥了我最后一眼,当你
用绳索勒住狗的脖子时它作出的正是这种无言哀求。穿过旋转门出来,我想到了范
诺登……我回旅馆去等电话,卡尔只有一小时时间,他答应在去上班前先告诉我结
果如何。我又翻检了一遍我们写给她的那些信的复写件,我试图想象这究竟是怎么
回事,可就是想不出。她的信写得比我们好得多,显然信是真诚的。现在他们搂在
一起了,不知道卡尔还尿不尿裤子。
电话铃响了,他的声音有些古怪,有点儿尖,既像是被吓坏了,又像是很开心
。他让我代他去办公室,“给那个狗杂种怎么说都行!告诉他我快死了……”“喂
,卡尔……能告诉我……”“你好!你是亨利·米勒吗?”是个女人的声音,是伊
雷娜,她在问我好呢。她的声音在电话上非常悦耳……悦耳。一刹那间我变得茫然
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对她说什么。我想说,“喂,伊雷娜,我认为你很美……我认
为你美极了。”我想跟她说一件真实的事情,不管听起来这有多么傻,因为我现在
听到她的声音后知道一切都已经变了。可是不等我镇定下来卡尔又接过了听筒,扯
着古怪的尖细嗓子说,“她喜欢你,乔。我把你的事全告诉她了……”在办公室里
我只得替范诺登读要校对的稿子。到了休息时间他把我拉到一边,脸色阴沉沉的,
“很难看。
“这么说这个小滑头快死了是吗?喂,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想他是去看那个有钱的女人了。”我平静地说。
“什么!你是说他去找她了?”他显得很激动,“喂,她住在哪里?叫什么名
字?”我假装一无所知,他又说,“我说,你是个不错的人。你为什么不早点几告
诉我这件风流韵事?”
为了安慰他,我最后答应一从卡尔那儿打听到细节就全部告诉他,我自己在见
到卡尔之前也急不可耐呢。
第二天中午时分我去敲他的房门,他已起床了,在抹肥皂刮胡子,从他脸上看
不出什么来,甚至看不出他会不会对我说实话。阳光从敞开的窗子里倾泻进来,小
鸟在吱吱叫,却不知怎么搞的,屋子比往常更加显得光秃秃的、更穷酸。地板上溅
满了肥皂泡沫,架子上挂着那两条从来不曾换过的脏毛巾。不知怎么搞了,卡尔也
一点儿变化都没有,真叫我大惑不解。今天早上整个世界都该发生变化,不论变好
变坏总得变,剧烈地变。可是卡尔却站在那儿往脸上抹肥皂,全然不动声色。
“坐下……坐在床上,”他说。“你会听到一切的……不过先等等……等一会
儿。”他又开始抹肥皂,接着磨起剃刀来。他还提到水……又没有热水了。
“喂,卡尔,我现在很焦急。你如果想折磨我可以过一会儿再折磨,现在告诉
我,只告诉我一件事……结果是好是坏?”
他从镜子前扭过身来,手里拿着刷子,朝我古怪地笑笑。
“等等!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这就是说你失败了。”
他终于说话了,字斟句酌地,“不,既没有失败,也没有成功……对了,你在
办公室替我安排好了吗?是怎样对他们讲的?”
我看出试图从他口中套出话来是不可能的,待他收拾好了会告诉我的,在此之
前却不会。我又躺下,一言不发,他则继续刮脸。
突然他没头没脑他说开了起初有点儿杂乱无章,后来越来越清楚,雄辩、
有力。把事情都说出来得费一番周折,不过他似乎打算要把一切都讲清楚,仿佛正
在把压在良心上的一个重负卸下。他甚至又令我想起上电梯前他曾那样瞥了我一眼
,他反反复复提起这一点,像是要表明一切都包含在这最后一秒钟里,像是要表明
如果他有力量改变局面,他就绝不会跨出电梯。
卡尔上门时伊雷娜穿着晨衣,梳妆台上摆着一桶香槟,屋里很暗,她的声音很
好听。他给我讲了屋里的全部细节,香槟酒、侍者是怎样把它打开的、酒发出的声
响、她走上前来迎接他时那件晨衣又如何沙沙作响他告诉我一切,唯独不谈我
想知道的。
他去找她时大约是八点,到了八点半,一想到工作他便局促不安。“我给你打
电话时大约是九点是不是?”
“是,差不多。”
“我当时很紧张,你瞧……”
“我明白。往下讲……”
我不知该不该信他的话,尤其是在我们编造了那些信之后。
我甚至不知道是否听清了他的话,因为他讲的内容完全是荒诞不经的。不过,
若是知道他就是这类人,他的话倒也像是真的。
接着我又想起他在电话上的声音又恐惧又开心的古怪调子。现在他为什么
不更开心一些呢?他自始至终都在笑,活像一只红润的、吸饱了血的小臭虫。他又
问一遍,“我给你打电话时是九点钟,是不是?”我厌烦地点点头,“是的,是九
点。”现在他肯定当时是九点钟了,因为他回忆起曾掏出表来看了看。再次看表已
是十点钟,到了十点钟她正躺在长沙发上,两手握着自己的乳房。他就这样一点儿
一点儿他讲给我听。到了十一点他们便拿定了主意,他们要逃走,逃到婆罗州去。
去他妈的那个丈夫吧!她从来没有爱过他,若不是他年纪大了、缺乏激情,她根本
就不会写第一封信。“后来她又对我说,‘不过,亲爱的,你怎么知道以后你不会
厌烦我呢?’”听到这儿我大笑起来,我觉得这话很荒谬,忍不住要笑。
“你怎么说?”
“你指望我说什么?我说,哪一个男人会厌烦你呢?”
接着他向我描绘后来发生的事情他怎样俯身亲吻她的乳房,怎样在热烈吻
过它们以后又把它们塞进胸衣里去,总之就是塞进那玩艺儿里去不管她们叫它
什么。过后,又喝了一回香槟。
到了午夜前后,侍者送来了啤酒和三明治鱼子酱三明治。据他讲,在此期
间他一直急着要撒尿。他曾勃起了一回,不过又软下去了。他一直感到膀脱就要胀
破了,可他是个狡猾的小滑头,认为眼下的场面需要谨慎从事。
到了一点半她提议租一辆车去逛波伊思公园,卡尔心中却只想着一件事如
何撒泡尿。“我爱你……我崇拜你,”他说。
“你说到哪儿我都跟你去伊斯坦布尔、新加坡、檀香山,只是现在我一定
得走了……太迟了。”
卡尔就在这间肮脏的小房间里向我讲述这一切,太阳照进来,小乌在疯了似的
吱吱叫。可我仍旧不知道她是不是漂亮,他也仍不知道她是否漂亮。这个白痴,他
连自己都不了解。他宁愿认为她不漂亮,那屋里太暗,还喝了香槟,他的神经又疲
惫不堪。
“可你应该了解一些她的情况假如这些不全是你他妈的编造出来的。”
他说,“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不,她并不漂亮,现在我敢肯定这一
点了。她前额上有一缕白头发……我想起来了。这还不算很糟你瞧,我还差点
忘了。她的胳膊胳膊很细……细而且干瘦。”卡尔开始走来走去,可忽然又站
住了。
“若是她年轻十岁我或许不会考虑那一缕白发……甚至也不注意她的细胳膊。
可是你瞧,她太老了。这样的女人每过一年都会老一大截,明年她就不是老了一岁
,而是老了十岁,再过一年就老了二十岁。我却会显得越来越年轻,至少在五年之
内“可这事儿是怎么拉倒的?”我打断他又问。
“这事儿根本没没完,我答应星期二五点左右去见她。
你知道,这很糟!她脸上的皱纹在白天会显得更难看。我估计她是想叫我星期
二跟她睡,大白天睡没人会跟这样一个女人在大白天睡,尤其是在那样一家旅
馆里。我宁愿在不上班的晚上干……可是星期二晚上要上班。还不止这些,我当时
还答应要给她写封信的。现在怎么给她写信呢?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屁,只要她
年轻十岁。你认为我该跟她去吗?去婆罗州或别的什么她想带我去的地方?我不会
射击,我怕枪和所有那类玩艺儿。再说,她会要求我没日没夜地跟她睡觉……除了
打猎就是睡觉,别的什么也不做……我办不到!”
“也许事情还不像你想的那么糟,她会给你买领带之类的东西……”“也许你
愿跟我们一道去,嗯?我把你的情况都告诉她了“你有没有说我很穷?有没有说我
需要东西?”
“我什么都说了。见鬼,只要她年轻几岁一切都好了。她说她快四十了,这就
是说五十或六十了。这跟同你妈睡觉差不多……不能这样干……这不行。”
“可她准还有一些迷人之处……你说你亲吻了她的乳房。”
“吻她的乳房这有什么?再说光线暗,我告诉你了。”
卡尔正穿裤子,一只纽扣掉了。“你瞧,这见鬼的西装全烂了。我已经穿了七
年了……不过没有掏钱。以前是套不错的衣服,现在却发臭了。那个女人还要给我
买西装哩,这是我最想要的。可我不喜欢叫一个女人替我付钱,这种事我一辈子也
没有干过,这是你的主意。我情愿一个人过日子。屁,这是一个不错的房间吧?有
什么毛病?比她的房间瞧着要好得多,是吗?
我不喜欢她住的豪华旅馆,我反对建那样的旅馆,我对她说了。
她说她不在乎住哪儿……说只要我要她来,她就来跟我住在一起。你想象得出
她带着大箱子、帽盒子和所有那些她随身带来带去的废物搬到这儿来的情景吗?她
的东西太多了太多衣服、瓶子和其他东西。她的房间像一个诊所,她的手指头
上划破了一点儿便不得了啦,她要找人来按摩,头发要烫过,不能吃这个,不能吃
那个。我说,乔,只要年轻一点点她就很理想。
一个年轻女人的任何毛病都是可以谅解的,一个年轻女人也不需要有脑子,她
没有脑子倒更好。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即使聪明,即使是普天下最最可爱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