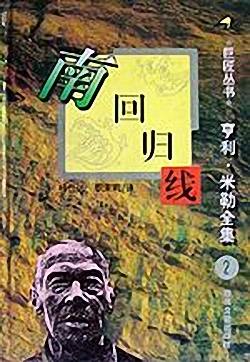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有关疾并夹板、工作台和新鲜空气的理论。这篇论文断断
续续写了六个星期,更倒霉的是,我还得校对这鬼东西。这是用法语写的,一种我
平生不曾见过听过的法语。不过它每天给我带来一顿丰盛的早饭,一顿美式早餐,
有桔汁、燕麦片粥、奶油、咖啡,有时还变花样,有火腿鸡蛋。我在巴黎期间只有
这一段能吃到像样的早餐!
这多亏了纽约曼哈顿东区罗克威海滩上的跛孩子以及毗邻小湾、小叉里令人伤
心的景象。
有一天我碰巧遇到一个摄影师,他在为慕尼黑某个性欲倒错的人拍一套巴黎下
流场所的照片。他问我愿不愿脱下裤子摆好姿式让他照,还有其他一些动作。我想
到那些瘦得皮包骨的小矮个儿,他们看上去像旅馆侍者和送信的。人们有时会在书
店橱窗里摆的色情明信片上看到这些人物,他们是今天鲁纳街和巴黎其他臭名昭著
的地方的神秘幽灵。我不大喜欢在这些社会精英面前展示自己身体的这个主意,可
是这个摄影师向我保证这些照片将会严格地由私人收藏,而且最终要拿到慕尼黑去
,我便应允了。当你远离家乡时你会允许自己稍稍放荡一场,尤其是出于一个值得
的、替自己挣口饭吃的动机。回想起来我毕竟不是一个过于拘谨的人,甚至在纽约
时也不是这样。在那儿有时夜里我那么狼狈,不得不出去在邻里间乞讨。
我们不去旅游者熟悉的参观游览场所,而是到一些小地方去,那儿的气氛更合
适一些。我们可以下午去那儿,先玩一会儿纸牌再干活。这位摄影师是个好游伴,
他十分熟悉这个城市,尤其是这儿的墙。他常跟我谈起歌德、霍亨斯陶芬王朝时代
及黑死病流行期间对犹太人的屠杀。这都是有趣的话题,而且总与他正在做的事情
有某些含混的联系。他对电影剧本也颇有研究,有一些惊人的见解,不过谁也没有
胆量去实施他的意见,看到一匹像沙龙门那样被劈开的马会激发他大谈但丁或达·
芬奇或雷姆卜兰特,他会从维莱特的屠宰场跳上一辆出租车带我赶到特卡德奥博物
馆,为的是指给我看使他着迷的一块头骨或一具木乃伊。我们仔细游览了第五、第
十三、第十九和第二十区,我们最喜欢的休息地点都是阴郁的小地方,比如国家广
场白杨树广尝护墙广场保罗一魏尔伦广场许多地方是我本来就熟悉的,可是听了他
的独到见解后我对所有这些地方有了全然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碰巧沿
着霍尔城堡街散步,吸进了医院床上发出的恶臭味——这股臭味在第十三区弥漫—
—那么我的鼻孔一定会快活地张大,因为这股气味同放置很久的死尸和甲醛气味混
合后便会产生另一种气味,这是我们在想象中穿过黑死病酿成的欧洲尸骨陈列所的
旅途中会闻到的种种气味。
通过这个摄影师我认识了一个唯灵论者,他叫克鲁格,是一位雕刻家兼画家。
出于某种原因克鲁格很喜欢我,当他发现我乐意倾听他的“深奥”见解后我简直无
法从他身边逃开。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人,“深奥”这个词似乎具有一种灵丹妙
药的功效,正像《魔山》中裴波尔克伦先生对“安居”的反应。
克鲁格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圣人、一个色情受虐狂、一个肛门类型的人,他遵循
的法则是拘泥细节、正直和诚心实意,在休息日里他会毫无愧色地打掉一个人的牙
齿,叫它落到此人的肚子里去。他似乎认为我已成熟了,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据他说是一个“更高阶段”。我已作好准备进入他指定的任何阶段,只要不少吃的
不少喝的就行。他唠唠叨叨地对我谈“线魂”、“成因体”、“切除”、奥义书、
普洛提诺、讫里什那穆提、“灵魂的业力受职仪式”、“涅磐的知觉”,全是从东
方吹来的胡话,像瘟疫后散出的气息。有时他恍恍惚惚说起自己上一辈子的模样,
至少是他想象中的模样,或者讲述他做过的梦。照我看这些梦十分平淡无奇,甚至
不值得一位弗洛伊德主义者去费神,可是他自己却认为这都是深藏不露、奥秘难测
的奇观,因而我一定要帮他解析这些梦。他把自己整个翻过来,像翻一件己磨光的
外套一样。
我一点一点地取得了他的信任,我钻到他心里去了。我已把他掌握得牢牢的,
他会在大街上追上我,看是否能借给我几个钱花。他想叫我活下去,以便活着完成
向更高阶段的过渡。我就像树上一只正在成熟的梨,我不时出现退步,吐露我需要
更多的尘世的滋养——去看一次狮身人面像或是去圣阿波罗街,我知道每当肉体的
要求变得太强烈、每当他变得软弱时便要去那儿。
作为画家他一钱不值,作为雕刻家他更不值钱,可他是个好管家,这也就不错
了,而且他还是一个十分节俭的管家,什么都不浪费,甚至连包肉的纸也不扔。每
逢星期五晚上他便为同行艺术家们打开自己的画室,有很多饮料,很好的三明治,
如果偶尔剩一点什么我第二天便来把它消灭掉。
在布里埃舞厅后面还有一家我常去的画室,那是马克·斯威夫特的画室。假如
这位刻薄的爱尔兰人不是天才当然也是一个怪才,他有一个犹太女人,是给他当模
特儿的,他俩在一起已住了多年。现在他厌烦她了。正在找借口甩掉她,不过因为
吃光了她当初带来的嫁妆,他现在正苦于找不到既不赔钱又能摆脱她的方法。最简
单的办法莫过于同她闹翻,迫使她宁愿饿死也不再忍受他的残酷行为。
他的这位情妇是个相当不错的女人,人们至多不过会说她已没有身材了,她养
活他的能力也完蛋了。她自己也是画家,那些声称了解情况的人中流传这样一种说
法,说她比他更有才能。
不论他待她多么苛刻她仍是公正的,她不允许别人说他不是一个大画家。她说
,正是因为确有天才他才是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别人从未在墙上看到她的油画
,只看到他的,她的作品都掖在厨房里了。有一次我也在场,有一个人坚持要看看
她的作品,其结果很令人不快。斯威夫特用他的一只大脚指着她的一幅油画说,“
你看这一幅,站在门口的这个男人正要出去撤尿,他会找不到回来的路,因为他的
头在……再看看那边那幅裸体画……画阴部之前她干得不错,我不明白她当时在想
什么,可她把那儿画得那么大,画笔一脱手掉进去就再也捞不出来了。”
为了给我们讲解裸体画该是怎样的,他拖出一幅巨大的油画,这是他才画完的
。画的是她,这是在犯罪心理激发下的绝妙报复,是一个疯子的作品——恶毒、琐
屑、邪恶、机智。你会产生一种感觉,即他是透过锁眼窥视她的,是在她没有防备
时画下她的——比方说她呆呆地掏鼻孔或搔屁股时。在画上,她坐在马鬃填的沙发
上,呆在一间没有通风设备的房子里,一间没有窗子的巨大屋子,这儿活像松果腺
的前叶,她身后是一道通向阳台的曲曲折折的楼梯,楼梯上铺着令人不愉快的绿色
地毯,这种绿色只能出自一个快要毁灭的世界。最突出的东西是她的屁股,它一边
大一边小,上面尽是疤痕,她像是微微从沙发上抬起了屁股,仿佛要放出一个响屁
。她的面部却被斯威夫特理想化了,显得甜美而又纯洁,纯得像咳嗽药水。她的胸
部被画得很大、被阴沟里的臭气充得胀大起来。她像一个放大了的胎儿,生着一副
安琪儿的迟钝、甜蜜容貌,正在月经污血的海洋里游泳。
然而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喜欢他,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人,一个脑子里除了绘
画什么都不想的人,而且还狡猾得像一只山猫。正是他启发我想到去发展与菲尔莫
的友谊,菲尔莫是一个在外交界供职的年轻人,他也加入了围着克鲁格和斯威夫特
转的那一小批人。斯威夫特说,“让他帮帮你,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钱全花在自己身上时,当一个人用自己的钱过得十分舒适自
在时,人们便总会说,“他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至于我,我看不出除此之外
还有什么更好的可以花钱的地方。对于这些人,人们不能说他们大方或吝啬,他们
毕竟把钱投入流通了——这才是要紧的。菲尔莫明白他在巴黎呆不了多久,他打定
主意要在这段时间里玩个痛快。由于一个人有朋友陪着玩得更有趣些,他自然会来
找我这样一个有充裕时间的人充当他所需要的伙伴。人们说他是一个令人生厌的人
,我想他的确也是,不过需要食物时比厌烦更糟糕的事情你也可以忍受。不管怎么
说,他还是在其他方面使我的夜生活变得有意思多了,尽管他蝶蝶不休地说话,通
常是谈他自己或他一味崇拜的作家——尽是阿纳托尔·法朗士和约瑟夫·康拉德之
流。他喜欢跳舞,喜欢喝好酒,喜欢女人,于是别人就能原谅他还喜欢拜伦和维克
多·雨果了,他刚出大学门才几年,有的是时间去改掉这些爱好。我喜欢的是他的
冒险精神。
由于我同克鲁格呆在一起的那一短时期内发生了一件古怪的事情,我和菲尔莫
更熟了,也可以说更亲密了。这件事情是柯林斯刚到后不久发生的,柯林斯是菲尔
莫从美国来时在路上认识的一个海员。我们三人去吃饭前常在圆形露天咖啡座定期
会面,总是喝茴香酒,这种酒使柯林斯心情舒畅,也为后来灌下去的甜酒、啤酒、
白兰地等垫了底。在柯林斯呆在巴黎的这段时间里我过的是贵族的日子,只吃鸡,
喝名贵葡萄酒,吃以前听也不曾听说过的甜点心。过上一个月这种养尊处优的生活
我就只好去巴登一巴登、维希或艾克斯菜班了。此时我在克鲁格的画室里过夜,
我正在成为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因为我从未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回来过,不到中午很
难把我赶下床来,克鲁格从未公开责备过我,不过他的态度很清楚地表明我正在变
成一个讨厌鬼。
有一天我病了,好饭菜在我身上生效了。我不知道自己生的是什么病,总之不
能下床,我一点儿力气也没有,也丧失了勇气。克鲁格不得不看护我,为我煮汤喝
,为我干别的,这对于他是一段很难的日子,尤其是他马上就要在画室里举行一次
重要画展了,这是为一些有钱的鉴定家举办的私人画展,他指望从这些人那儿得到
赞助,我睡的帆布床就摆在画室里,再没有其他房间可以安置我了。
要举行画展那天早上克鲁格一醒来便十分不快,若是我还能站起来,我知道他
准会照我下巴上揍一拳,然后把我踢出去。
可我直挺挺地躺着,衰弱得像一只猫。他想哄我起床,想等参观画展的人一来
便把我锁进厨房里。我也意识到自己这是在给他捣蛋,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眼前,
人们不可能有兴致看绘画和雕塑。克鲁格打心眼儿里认为我快死了,我自己也这么
想。这就是他提议叫救护车拉我去美国医院时我提不起一点儿劲来的原因,尽管我
也有一种负罪感。我只想舒舒服服地就死在画室里,我并不想被人赶起来找一个好
点儿的地方去死。我不在乎自己死在哪里,真的,只要不叫我起来就行。
听我这样说,克鲁格吓坏了。假如参观的人到了,画室里摆着一具死尸比睡着
一个病人更倒霉,那会彻底毁掉他的前程,不论这种前程是多么黯淡。他当然不会
这样对我讲,不过我从他焦虑不安的神情中看出这是使他烦恼的原因。这使我变得
固执起来,我拒绝让他往医院打电话,我不让他打电话叫医生,我什么都不让他做
。
最后他被我惹火了,不顾我的抗议便开始给我穿衣服。我身体太弱,无法抗拒
,只能有气无力地低声咕哝——“你这个狗东西,你!”屋外很暖和,可我还是像
条狗一样不住地发抖。
他给我完全穿好衣服后便又在我身上盖了件大衣,然后溜出去打电话。“我不
去!我不去!”我不停地这样说,可他只是砰地关上门走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了
,一句话也没对我说便忙着收拾画室,这是最后的准备工作。过了一会儿有人敲了
敲门,是菲尔莫,他告诉我柯林斯正在楼下等着呢。
菲尔莫和克鲁格两人把手放在我身下将我扶起来,拖着我朝电梯走的路上克鲁
格态度柔和些了。他说,“这是为了你好。
再说,这样对我不公平。你知道这些年来我是怎样挣扎过来的,你也该替我想
想。”他真的快掉眼泪了。
尽管我觉得很不幸、很苦恼,他这番话还是差点儿使我笑起来。他比我年纪大
得多,是一个糟糕的画家、一个糟糕透顶的艺术家,尽管如此他也该交一回好运—
—至少一辈子该有一次机会。
“我并不是跟你过不去,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喃喃道。
他答道,“你知道我一直是喜欢你的。等你好些了可以再回到这儿来……住多
久都由你。”
“当然,我明白……我一时还死不了。”我勉强说了一句。
不知为什么,一看到柯林斯在楼下我的精神就好多了。如果有谁显得充满生气
、健康、快活、豁达,这个人便是他。他把我抱起来放在汽车座位上,好像我是个
洋娃娃,而且动作很轻柔,被克鲁格粗暴地搬了一回后我很欣赏这一点。
我们驱车来到旅馆——柯林斯下榻的旅馆——柯林斯同旅馆主人谈了几句。我
听得见柯林斯对这位主人说,没有什么疾箔…只是有一点儿累了……几天就会好的
。我看到他把一张皱巴巴的钞票塞在那人手里,然后迅速、灵巧地转身回到我身边
说,“来,振作起来!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说着,他把我用力拉起来,用一只
胳膊撑住我的身体,带我朝电梯走去。
“别让他以为你快死了!”显然死在别人手上是不得体的,一个人应该死在自
己家里,也可以说是悄悄死去。他的话很鼓舞人,我开始把这看作一个拙劣的笑话
了。上了楼,关上房门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给我盖上被子。柯林斯热切他说,“
你现在不能死,他妈的!那样你会叫我难堪的……再说,你到底有什么病?过不了
好日子?拿出点儿勇气来!过一两天你就能吃上等腰肉牛排了。你以为你生病了!
别急,等你生了一回梅毒再说!那才叫你胆战心惊呢……”他又幽默地谈起他沿着
长江的旅行,路上头发掉了,牙齿也烂了。处于这样的衰弱状态中,他讲述的这段
往事对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安慰效果,使我完全忘记了病痛。这家伙胆子真大,也
许为了我的缘故他有几分添油加醋,可我当时听他讲故事时并不想挑刺。我全神贯
注地听,我仿佛看到了长江肮脏混浊的河口、汉口的灯光、众多的黄面孔、穿过三
峡飞流直下的舢板和被龙口中吐出的带股硫磺味的火舌映红的湍流。多么奇异的经
历!中国苦力们如何每天围在小船周围,打捞被船上人扔下水的垃圾废物;汤姆·
斯莱特里如何在弥留之际从病榻上撑起身子再看一眼汉口的灯光;那个英俊的欧亚
混血儿如何躺在一间屋子里往自己血管中注射毒药。还有千篇一律的蓝褂子和黄面
孔,他们中有千千万万的人被饥馑弄得惟悴不堪,忍受疾病折磨,他们靠吃老鼠、
狗和树根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