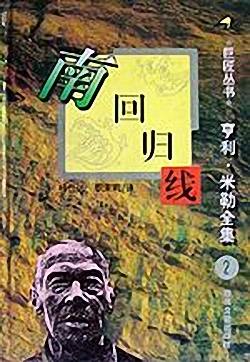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3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不到。一个人一露面这个世界便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腰压断。总有过多的腐朽
柱子立着,过多令人痛苦的人性有待人去繁衍。上层建筑是一个谎言,其基础则是
巨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如果说在过去千百年间真的出现了一个眼睛中流露
出绝望、饥饿神色的人,一个为创造一种新生物把世界翻个底朝天的人,那么他带
给世界的爱便会化为忿怒,他自己则会变成一场灾难。如果我们不时读到探究真理
的书、刺伤人使人冷酷无情的书、令人叫苦落泪诅咒谩骂的书,我们就知道这些文
字是那个被压趴下的人写的,他唯一的抵抗就是诉诸文字了,而他的文字总是比世
界上撒谎压人的重量更有力,比胆小鬼们发明的要压垮人格之奇迹的刑台和刑车更
有力。如果哪个人敢于直抒胸臆、秉笔直书他的真实经历,真正的真实,那么我想
世界将毁灭、将被吹成碎片,没有神、变故和意志能重新弥合起这些失去的碎片、
原子和不可摧毁的要素以再造一个世界。
自从最后一个贪吃的人、最后一个懂得“喜悦”的含义的人出现以来的四百年
间,人类在艺术、思想和行为上都在持续不断地衰败。这个世界完蛋了,连一个干
脆利落的屁也不曾留下。哪一个绝望的、饥肠辘辘的人会对现存政府、法律、道德
、准则、理想、思想、图腾和禁忌表现出丝毫敬重?如果谁知道念出那个在今天被
称之为“缝”或“洞”的谜一般的东西意味着什么,如果谁对被贴上“淫秽”标签
的现象怀有最低限度的神秘感,那么这个世界便会分裂成几块。正是对淫秽的惧怕
,即事情干巴巴的、被人操过的那一面,使得这个疯狂的文明社会显得像个火山口
,创造性精神和人类母亲大腿间正是这种张开大嘴打哈欠似的空幻感。一个饥饿、
绝望的精灵出现并使一只土拨鼠锐声尖叫是因为他懂得在哪儿敷下性的炽热导线,
是因为他懂得在无动于衷的坚硬表现下藏着丑恶的创伤,其伤口永远不会愈合。于
是他把这段炽热的导线夹在两腿间,他使用难以令人接受的卑下手段。戴上橡皮手
套也没有用,所有能冷静、机智地加以处理的都是表皮上的东西,而一个志在创造
的人总是要钻到底下、钻到开放的伤口上、钻到正在化脓的对淫秽的惧怕上。他把
发电机拴在最脆弱的部分,叫人操过的火山口是淫秽的,比一切更加淫秽的是隋性
,比最难听的赌咒发誓更亵读的则是麻痹。如果只剩下一个裂口的创伤,它一定得
向外喷射,尽管喷出来的只是蛤螈蝙蝠和侏儒。
每一样东西都装在另一样东西里面,有的是完全的,有的是不完全的。地球不
是健康和舒适的干旱高原,而是一位仰卧的硕大女性,她天鹅绒般的躯体随着海浪
而涨大,起伏,她在大汗淋漓、极度痛苦的王冠重压下蠕动。赤身裸体性交后,她
在星星紫光笼罩下的云彩中滚动。她的全身在狂热的激情支配下放出光芒,从慷慨
的乳房到隐约可见的大腿。她在四季和岁月间邀游,一场盛大的狂欢以突发的狂怒
攫住她的躯体,抖去了天空中的蜘蛛网,于是她以暴躁的兴奋心情降落在自己的旋
转轨道上。有时她像一只母鹿。这只母鹿跌进了陷阶,它心怦怦跳着躺在那儿等待
钦声敲响、猎狗狂吠。爱与恨、失望、怜悯、怒气、厌恶——这些在行星间的乱交
中又算得了什么?当夜晚提供了耀眼的太阳般的欣喜时,战争、疾并残酷和恐怖又
算得了什么?若不是记起回到野蛮时代和星团,我们睡觉时嚼的糠又是什么?
莫娜每逢性欲亢奋时常常对我说,“你是一个伟大的人。”藏在我灵魂深处的
这话常会跳出来照亮我下面的阴影,尽管她把我扔在这儿听任我死掉,尽管她在我
脚下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大坑。我是一个普通的人,嘶嘶响的灯光使我头晕。我是一
个零蛋,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沦为嘲弄人的东西。由硫磺燃着的男女从我身边走过
,穿着黑色号衣的搬运工打开了地狱的双颚,声名在拄着拐杖走路,它被摩天大楼
骗了,被生着锋利牙齿的机器的大口嚼烂。我穿过高大的建筑物朝清凉的河边走去
,我看见光束像火箭一样从骷髅的肋间直刺天空。如果我像莫娜所说的真是一个伟
大的人,我阿谀奉承人的愚蠢行为又该作何解释?
我是一个有灵有肉的人,我的心并没有钢梁拱卫,我有过欣喜的时刻,我伴着
燃烧的火星歌唱。我歌唱赤道、她生着红毛的大腿和从视线中消失的岛屿。不过谁
也没有听见我唱,朝太平洋彼岸发射的一炮落进太空里了,因为地球是圆的,鸽子
们朝下飞行。我看到她隔着桌子望着我,眼光中一派悲怆。在她身体里扩散的悲伤
将鼻子碰在她脊骨上,碰扁了,搅拌成怜悯的骨髓已变成液体。她轻巧得犹如浮在
死海海面上的一具死尸,她的手指痛得流血,血变成了口水。随着潮湿的黎明来临
,钟声敲响了,这钟声沿着我的神经纤维无休无止地回荡,这撞击声伴随着铁一般
的恶意在我心里当当响。奇怪的是钟声竞会这样响,更怪的是钟破裂了,于是这个
女人转向黑夜。她的蛆一般的言辞咬透了床垫。我在赤道下移动,听见了张着绿色
大口的鬣狗可怕的哈哈大笑声,看见了生着光滑尾巴的豺、羚羊和有斑点的豹子,
它们全被留在伊甸园里了。这时她的悲哀扩展了,像一艘无畏战舰的舰首,她沉下
去的重量使我的耳朵被水淹没了。稀泥被洗掉,蓝宝石滑出来,通过快乐的神经细
胞淘洗出来,它的光谱被拼接在一起,船舷泡在水里。我听见炮架像狮爪落地时一
样无声无息地转动,看到它们在呕吐、在流口水。天幕垂下来,所有的星星都变成
了黑的。黑色的海洋在流血,沉思默想的星星孕育着一大块一大块刚刚肿胀起来的
肉,同时鸟儿在头顶上盘旋,幻党的天空中落下臼杵,还有正义包扎起来的眼睛。
所有在这儿讲到的东西都用想象中的脚沿着死去的球体平行移动,所有用空眼眶看
到的东西都像开花的草一样绽开。在虚无缥缈之中出现了无限的符号,不断上升的
螺旋下裂开的口子在缓慢下沉。陆地和海洋和谐地连为一体,这是用血肉写就的诗
篇,它比钢丝和花岗岩还坚硬。经过无尽的长夜,地球向一个未知的创造物飞速旋
转而去……今天我在熟睡中醒来,嘴边挂着快活的诅咒,我不断地自己咕哝谁也听
不懂的话,像在念一篇连祷文——“做你想做的事……做你想做的事!”干什么都
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欢乐;干什么都行,但是要叫它带来欣喜。当我向自己提到下
面这些东西时脑袋里塞得满满的——搞同性恋的人、叫人恐惧的人、叫人发疯的人
、狼和羊、蜘蛛、蟹、梅毒张开了翅膀、子宫的门总闩着、总敞着,像坟墓一样作
好了接待准备。淫欲、犯罪的神圣——我崇拜的人就过着这种生活,那也是我崇拜
的人的失败,是他们留下的话,是他们未说完的话。那是他们拖在身后的善与恶、
他们造成的悲哀不和、仇恨和争斗,而超出这一切的是狂喜!
我以前的偶像的一些所做所为使我流泪,那是捣乱、混乱、暴力,最主要的还
是他们引起的仇恨。一想到他们残缺不全的肢体、他们选择的荒诞风格,他们所从
事的工作的浮夸和乏味、他们耽溺于其中的杂乱无章状态以及他们在自己身边设置
的种种障碍——我便觉得异常高兴。他们陷在自己拉的屎中不能自拔,他们都是喜
欢不厌其烦地絮絮叨叨的人。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差一点儿就会说,“指给我一个
说起话来没完的人,我就会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人!”被称作他们的“详尽探讨”的
东西正对我的胃口——这是争斗的征兆,这是缠绕着各种纤维的争斗,是不和谐精
神的气氛和环境。你指给我看一个能说会道的人,我不说他不够伟大,可我会说他
吸引不了我……我向往那些会叫人生厌的特性。我想到艺术家毫不含糊地给自己规
定的任务是推翻现存价值观念、是把周围的一片混乱按自己的方式整理得井井有条
,散布争斗和不和以得到情感上的解脱并使死者复活,于是这时我兴高采烈地跑到
那些伟大而又不完美的人那儿去,他们的困惑滋润了我。他们结结巴巴的话在我听
来犹如仙乐。我在漂亮地膨胀起来,在被打断之后接着往下写的书页上看到被抹去
的小段插入的闲话、肮脏的脚注,也可说是胆小鬼、骗子、贼、蛮子和诽谤者留下
来的。我从他们美妙的喉咙的肿胀肌肉上看出把轮子翻转过来时,从掉队的地方加
快脚步赶上来时,他们一定费了惊人的力量。在日常烦恼和骚扰后面,在软弱和懒
惰的人的下贱、矫饰过的恶意后面,我看见那儿立着人生中令人心灰意懒的象征,
我看到那个制定秩序、散布争斗和不和的人,他深受意志力的影响,这样一个人势
必一次次为自己的行为受苦受难,直至被绞死拉倒。我从他的高雅手势后看到一个
荒谬的幽灵在徘徊——他不仅崇高,而且还荒谬。
我曾一度认为做到有人情味是一个人可望达到的最高目标,可我现在明白这意
味着要毁掉自己。如今我骄傲地说自己没有人味,我不属于其他任何人和政府,任
何信条和原则都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与人性这部吱吱作响的机器毫无关联,我是
属于地球的。我睡在枕头上这样说,这时自己可以感觉到太阳穴处冒出了两只角。
我可以看到我的疯狂的祖先围着床在跳舞,他们宽慰我、给我打气、用毒蛇般的舌
头抽打我、用藏在暗处的脑袋朝我嘻笑。我不是人!我带着疯狂的、幻觉般的狞笑
这样说,哪怕天上落下鳄鱼我也要一直这样说下去。我的话后面是那些咧着嘴嘻笑
、藏在暗处的脑袋,有些死掉的人的脑袋长时间地笑,有些像患了牙关紧闭症一样
笑,有些又扮出鬼脸来狞笑,这是一直在进行中的事情的预演和结果。我自己狞笑
的脑壳是看得最清楚的,我看到自己的骷髅在风中跳舞,毒蛇从腐烂的舌头里爬出
来,描写欣喜的膨胀的书页被粪弄脏了。
我把我的脏东西、我的屎尿、我的疯狂,我的欣喜都投进通过肉体地下铁道流
动的大循环中去,所有这些自然的、不受欢迎的、醉后吐出的东西将通过这些人的
脑子无休止地向前流动,一直流到一个装着人类历史、永远不会枯竭的罐子里。同
人类并驾齐驱的还有另一类生物,他们就是那些没有人性的人,是艺术家这类人,
他们受已知的冲动驱使掌管了无生命的人类,他们用狂热和激情鼓动人类,以此把
这团生面变成面包,把面包变成酒,再把酒变成歌曲。他们从废弃的肥料和死气沉
沉的废料中造出一首散发着臭气的歌。我看到这一类人在洗劫世界,他们把一切翻
个底朝天,他们的脚总踩在血泊中,他们的手总是空的,总是在抓抓不到、握不上
的神。为了使撕咬他们的要害的妖魔平静下来,他们毁掉了能够得到的一切,他们
用力揪自己的头发以领悟、了解这个永远难以理解的难题,他们像发疯的熊那样大
吼大叫、乱撕、乱顶,他们做这些事情时我都看到了,我看到这是对的,没有其他
道路可走,一个属于这一族类的人必须站在高处,口中胡说八道,把自己的肠肚剖
出来。这是正当的、正义的,因为他必须这样做!任何达不到这一吓人场面、任何
不那么令人战栗、不那么可怕、不那么疯狂、不那么令人兴奋、不那么具有污染性
的东西都不是艺术,都是伪造的,是人性的,是属于生命和无生命的。
比方说,每当我想到斯太甫罗根,我便会联想到某一个妖魔站在高处向我们扔
自己撕裂的肠子。在《魔鬼》中发生了地震,这不仅是降临在富于想象力的人头上
的大灾难,而是一大半人类被埋葬于其中、永远被消灭的大地震。斯太甫罗根就是
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所有这些矛盾的总和,它们不是使一个人麻痹
就是领他爬上高处。没有一个地方太低,他进不去;也没有一个地方太高,他不敢
爬上去。遗憾的是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一个被置于神秘的中心的人,他的光芒为
我们照亮黑暗的深邃和广大。
今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血统,我没有必要去求助占星术或查阅家谱表。我对星
星上或我的血液里写着什么一无所知,只知道我是由人类的某些神话中的创始人繁
衍的。那个把神圣的瓶子举到唇边的人、那个跪在集市上的罪犯、那个发现所有的
尸体都会发臭的纯洁的人、那个跳舞时手中发出闪电的疯子、那个撩起长袍朝大地
上撒尿的修道士、那个翻遍所有图书馆要找到《圣经》的宗教狂——所有这些人合
成了我,所有这些人造成了我的仟侮、我的欣喜。假如我没有人味儿,那是由于我
所生活的世界已经超出人性的界线了,那是由于做个有人味儿的人像是在做一件可
怜的、令人遗憾的、凄凉悲苦的事情,它受到种种理智限制,受到种种道德规范的
制约,由种种老生常谈和这个那个主义固定范围。我将葡萄汁一饮而尽,我从中得
到了智慧,不过我的智慧并非来自葡萄,我沉醉也根本不是因为酒……我想绕过那
些高大荒芜的山脉,一个人会在那儿渴死、冻死。这就是“超瞬时”历史,就是不
存在人、兽、草木的绝对时空,在那儿一个人寂寞得发疯,语言则只是词语而已,
那儿的一切都是自由自在的,与时代不谐调的。我想要一个男人、女人、树木都不
讲话的世界(因为如今的世界上话讲得太多了)!
我想要一个河流能把人载到各地去的世界,不是成为古老传说的河流,而是能
叫人同别的男女,同建筑、宗教、植物、动物接触的河流。是上面有船只的河流。
人们在这样的河里溺死,并非淹没在神话、传说、书籍和以往的尘土中,而是淹没
在时间、空间的历史中。我要能造出莎士比亚和但丁这样的大海的河流,要不会在
以往的空泛中干涸的河流、大海。对了,让我们有更多的海吧,新的、挡住过去的
大海,创造新的地质构造、新的地形景观、陌生而且令人恐惧的大陆的大海,在摧
毁的同时也保护我们的大海,我们可以在上面航行,去探求新发现、新视野的大海
。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大海、更多的动乱、战争和大毁灭吧。让我们得到一个男男女
女大腿间都装有发电机的世界,一个充满自然的愤怒、激情、行动、戏剧、梦幻、
疯狂的世界,一个孕生欣喜而不是干放屁的世界。我坚信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应寻求写一本书,哪怕它只有一大页呢。我们必须寻找碎片、碎屑、脚趾甲,任何
含有矿物质、任何得以使肉体和灵魂复活的东西。
也许我们命中注定要遭厄运,也许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有希望活下去。如果是
这样,那就让我们发出最后一声听了叫人胆寒、叫人毛骨惊然的吼叫吧,这是挑战
的呼叫,是战斗的怒号!悲伤,去它的!挽歌和哀乐,去它们的!传记、历史、图
书馆和博物馆,去它们的!让死人去吃掉死人。让我们活着的人在火山口边上跳舞
吧,这是临死前的一场舞,不过它仍是一场舞。
我们时代的伟大诗人弥尔顿说,“我爱流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