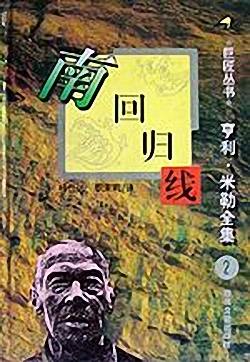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3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油漆都已脱落,石头被掏空,楼梯扶手嘎嘎直响。楼梯顶上那盏微弱的红灯发出的
光穿透了铺路石上散出的潮气形成的苍白、模糊的蒸汽团。我大汗淋漓、惊慌失措
地爬上最后一段楼梯,即塔楼。我在一片漆黑中摸索着走过空寂无人的走廊,每个
房间都是空的、锁上的,都正在朽掉。我伸手在墙上摸匙孔,握住门把手时总会慌
乱一阵。总有一只手抓着我的衣领,预备把我猛拽回去。一进屋我就锁上门,我每
天晚上都在创造奇迹,这个奇迹便是不等被人扼死、不等被人用斧头砍倒就进屋。
我听见老鼠在走廊里跑过,在我头顶上的粗椽子之间大咬大嚼。灯光像正在燃烧的
硫磺一样耀眼,屋里充满从未通过风的房子里的那种又亲切又难闻的恶臭味。装煤
的箱子像我离开时一样仍摆在角落里,炉火熄了,这极度的寂静倒叫我觉得像是听
到了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水声似的。
于是我独自呆着,带着极度空虚的渴求和恐惧,整间房子都听凭我的思绪驰骋
。除了我和我所想的、所畏惧的一无所有。
我尽可以去想最最异想天开的事情,尽可以跳舞、啐唾沫、做怪相、诅咒谩骂
、掩面大哭——谁也不会知道,谁也听不见。一想到这种彻底的独处生活就足以使
我发疯,就好像一个人利落地生下来,一切牵挂都割断了,分割开,赤裸裸的、独
自一人呆着,同时也尝到了幸福和痛苦。你有的是时间,每一秒钟都像一座大山一
样压在你身上,你在时间中被溺死。沙漠、大海、湖泊、大洋。时间像一把砍肉斧
头在一下下砍击中逝去。虚无、大千世界、我和非我。Oomaharumooma。每一件事
物都得有一个名称,每一件事情都得通过学习、考验和体验才能掌握。亲爱的,别
客气。
寂静是乘着火山状的降落伞降临的。在那边贫脊的群山中,机车正拖着商品朝
广阔的冶金地区隆隆驶去。它们在钢铁路基上滚动,地上洒着矿渣、炉渣和紫色矿
石。车里装着海带、鱼尾板、钢材、枕木、盘钢、厚金属板、叠合材料、热轧钢箍
、软木条和迫击炮车,以及佐泽斯矿石。轮子是U…80毫米的,或者更大。机车经过
盎格鲁—诺曼式建筑的堂皇标本,经过了步行者和男同性恋者、露天冶炼炉、使用
贝塞麦法的磨坊、发电机和变压器、生铁块和钢锭。众人都自由自在地在五星状的
胡同里过来过去,行人和男同性恋者、金鱼和玻璃丝样的棕桐树,驴子在抽泣。在
巴西广场有一只淡紫色的眼睛。
我很快回想了一遍我所认识的女人,这就像一条我用自己的痛苦锻造的铁链,
一个套着另一个。这是畏惧分居、畏惧总也长不大。子宫之门总是拴着的。恐惧和
希望。血液里蕴藏着天堂的吸引力。来世,总是来世。这完全起源于肚脐,他们在
这儿割断了脐带,在你屁股上掴一掌,然后全妥了!你来到这个世界上,随波逐流
,是一只没有舵的船。你先看看群星,再瞧瞧自个儿的肚脐。你身上到处长出眼睛
来,腋下、两嘴唇间、头发根上、脚心。远的变近,近的变远。里外处于永恒的变
化之中,成为蜕下的皮。你就这样一年年四处漂泊下去,直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
死滞的中心,你将在这儿慢慢腐烂,慢慢变成粉末后又重新散落到各处,只有你的
名字留下来。
第15章
待我设法逃离这座感化院已是春天了,那还是因为命运的巧妙安排。有一天卡
尔打电报通知我“楼上”腾出了一个空位置。他说如果我打算接受这个工作他就寄
路费来。我马上拍了回电,钱一寄到我就直奔火车站,跟勒普罗维西厄或其他人什
么都没有说。正如人们所说,我是不辞而别了。
我一下车便立刻来到一号乙的那家旅馆,卡尔就住在这儿。
他一丝不挂来开门,这天他是晚上休息,同往常一样床上有个女人。他说,“
别管她,她睡着了。假如你想睡女人就睡她好了,她还不坏。”他拉开被子让我看
看她的容貌,可是我还不想马上睡女人。我太激动了,像一个刚刚从狱中逃出的犯
人。我只是想看、想听。从车站一路走来,像是做了一场大梦,我觉得自己已离开
了很多年。
直到坐下来好好打量了一番这间屋子后,我才悟到自己又回到了巴黎。这是卡
尔的房间,一点儿不错,像一个松鼠笼和厕所的结合。桌上几乎找不到一块能放他
的袖珍打字机的地方,而且总是这副样子,无论他是否和一个女人同居。一本词典
总是打开压在一卷涂了金边的《浮士德》上面,总摆着一只装烟草的袋子、一顶贝
雷帽、一瓶红酒、信件、手槁、旧报纸、水彩、茶壶、脏袜子、牙签、克鲁什深嗅
盐、避孕套,等等。洗身盆里扔着桔子皮和吃剩的火腿三明治残渣。
卡尔说,“食品橱里有吃的,自己拿吧!刚才我正要给自己打一针呢。”
我找到了他说的那个三明治和三明治旁他啃过的一块奶酪。他坐在床边给自己
注射弱蛋白银,与此同时,我吃光了三明治和奶酪,还有一点甜酒。
他用一条脏裤头擦擦自己的阴茎说,“我喜欢你写来的那封谈歌德的信。”
“我马上就给你看我的答复,我要把它写进我的书里。你的问题在于你不是德
国人,要理解歌德你必须是德国人。得了,我现在不打算给你解释了,我已经把它
全写进书里……顺便说说,我现在又新弄到一个女人——不是这一个——这一个是
个傻瓜。我是几天前才把她弄到手的,我说不上她还会不会来。你不在时她一直跟
我一起住,那天她爹妈来把她领走了。他们说她才十五岁。你能想到吗?他们还把
我吓得屁滚尿流……”我大笑起来,卡尔正是一个把自己置于这种狼狈境地的人。
他说,“你笑什么,也许我会为这个坐牢的。还好,我没有叫她怀上孕。不过
这也很奇怪,因为她从来不采取妥当的措施照顾自己。你知道是什么救了我?照我
看,是《浮士德》。就是!
她老子正巧看见它放在桌上,他问我懂不懂德文。事情这样一件件连下去,不
等我省悟过来他已经瞧开我的书了。幸好我凑巧把莎士比亚的剧本也摊开了,这使
他大力吃惊,说我显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
“那个姑娘呢?她怎么说?”
“她吓得要死。你瞧,她来时戴着一块小手表,可慌乱中我们找不到这块表了
。她老妈一定要叫我找到它,否则就叫警察。
这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形了。我把整个房间翻了个底朝天,可还是找不到那块见
鬼的手表。那当妈的气疯了。尽管她对我很不客气,我还是喜欢她,她比她女儿长
得还漂亮呢。瞧,我要给你看看我刚刚开头写给她的信,我爱上她了……”“爱上
当妈的了?”
“对了。为什么不行?假如我先看到的是她妈,我绝不会再瞧女儿一眼。我怎
么知道她才只有十五岁?你睡一个女人之前总不会先问她多大了,对吗?”
“乔,这件事情有点儿古怪。你不想哄我吧?”
“哄你?瞧,瞧瞧这个!”说着他给我看了那个姑娘画的水彩画,画的是娇小
可爱的物件——一把刀子和一条面包、桌子和茶壶,每一样东西部越画越高。卡尔
又说,“她爱上我了。她像个孩子,我得告诉她什么时候刷牙、教她怎样戴帽子。
瞧这儿,瞧瞧这些棒棒糖。我每天总要给她买几根棒棒糖,她喜欢棒棒糖。”
“那么她爹妈来带她走时她怎么样,大吵大闹了吗?”
“哭了几声就完了。她能干什么?不到法定自立年龄……我不得不保证不再见
她,也不写信。我现在等着瞧的就是——她会不会躲着不露面。她来这儿那会儿还
是处女。关键在于,她不跟男人睡能熬多久?在这儿时她怎么也睡不够,差点儿把
我累趴下了。”
这时床上那个姑娘醒了,正揉眼睛呢。照我看她也挺小的,长得不丑,不过蠢
得要命,想马上知道我们在谈什么。
卡尔说,“她就住在这个旅馆里,二楼,你想到她的房间去吗?我替你安排。
”
不就是她从前常挨揍,你是了解这些法国娘儿们的,她们一恋爱就会失去理智
。”
很明显,我不在这儿期间已经发生了一些事情。听说了菲尔莫的不幸我很难过
,他从前对我好得要命。同范诺登分手后,我跳上一辆公共汽车径直来到医院。
我估计他们还没有认定菲尔莫是否完全神经错乱了,因为我在楼上一个单人病
房里找到了他,他仍享有正常病人的一切自由。我去时他刚刚洗完澡,一看到我他
便失声痛哭起来。他立刻说,“全完了,他们说我疯了,也许还得了梅毒。他们说
我有夸大妄想。”他倒在床上轻声啜泣,哭了一阵又抬起头来微笑了——真像一只
刚刚睡醒的小鸟儿。他说,“他们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普通病房里,或疯人院里?
我可付不起这笔钱,我只剩下最后五百美元了。”
我说,“这正是他们留你住在这儿的原因,等你的钱花光了他们会很快叫你搬
走的。你不用操心。”
我的话一定说动了他,我话音未落他就把他的表、表链、钱夹、兄弟会证章等
东西全交给我。他说,“把这些收好。这伙王八蛋想抢光我的所有东西。”突然他
又大笑起来,这种古怪、郁郁寡欢的笑声会使你坚信这个笑的人愚不可及,不论他
是不是真的蠢,他说,“我知道你会认为我疯了,可我想弥补我做的事情,我想结
婚。你瞧,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性病,我把病传染给她,又叫她怀了孕。我对医生说
了,我不在乎自己会怎样,可是我要他准许我先结婚。他说是要我等好一点了再说
,可我知道永远不会好了。我这就完蛋了。”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也笑了,我不明白他这是怎么了。总之我只得答应去看看
那个姑娘,向她解释解释这些事情。他要我支持她、安慰她,还说了他可以信赖我
之类的话。为了宽他我自己也说不上想不想去,看到卡尔又同她调起情来,我才决
定去。我先问她是不是大累。这是一个没有用处的问题,一个婊子永远不会累得分
不开她的两条腿,尽管有些人会在你趴在她们身上折腾时睡着。总之我们商定到她
的房间去,这样这一夜我就不用给旅馆老板付钱了。
到了早上我租了一个俯瞰底下小庭院的房间,背着夹板广告牌做广告的人总到
这个小院子里来吃午饭。中午我叫卡尔一同去吃早饭,我不在期间他和范诺登新近
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去库波勒饭店吃早饭。我问,“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卡
尔答道,“为什么非去库波勒?因为库波勒全天都上麦片粥,麦片粥是叫你吃了拉
屎的。”我说,“明白了。”
于是生活又像以前一样,我们三人步行上下班,常发生小口角、小争斗。范诺
登仍为了他的女人、为了把肚子里的脏东西冲洗出来而发牢骚,只是现在发现了一
种新消遣,他发现手淫不那么令人烦恼。他把这个新闻告诉我后,我着实诧异了一
阵,我认为像他这样一个家伙不可能在自慰中得到乐趣。他又向我描绘他是如何弄
的,这就更使我十分诧异不已了。用他的话说,他“发明”了一种新技艺。他说,
“你拿一个苹果,挖掉果心,然后在里面抹一些冷奶油,这样它就不会化得太快了
。哪一天试试看!一开始会叫你神魂颠倒的。不管怎样,这个办法很便宜,也不用
费多少时间。”
他换了一个话题,又说,“对了,你的那位朋友菲尔莫住进了医院。我想他是
疯了,反正这是他的姑娘告诉我的。你不在时他找了一个法国姑娘,他俩一度打架
打得很厉害。女的是一个大块头、很壮实的婊子,是那种粗蛮的女人。我倒不在乎
跟她睡一回,只是怕她会把我的眼珠子抠出来。菲尔莫经常脸上、手上带着抓破的
伤痕走来走去,有时她也显得被人揍肿了,要的心,我答应了他提出的一切。我并
不觉得他确实疯了。只是有点儿灰心丧气。是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心理危机
,是道德准则的突然萌发。我对这个姑娘抱有很强烈的好奇心,想知道整个事情的
内幕。
第二天我找到了她,她住在拉丁区。一弄明白我是谁她便变得非常友好,她自
称叫吉乃特,块头很大、消瘦、健康,有一颗门牙崩落了一半,是那种农家女的外
貌。她精力充沛,眼神中流露出狂躁的意味。她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哭,然后,想起
我是她的“乔乔”的老朋友——她就是这样叫他的——她便跑下楼去拿来几瓶白葡
萄酒。她要我留下同她一道吃饭,她执意要这样。喝了酒后她一阵高兴,一阵伤感
。根本什么也不用问,她自己就像一部自动上发条的机器一样说开了。最使她担忧
的是——待他们放他出院后,他能重新去工作吗?她说她父母很有钱,不过生她的
气,不赞成她放纵无忌的行为。他们尤其不喜欢菲尔莫,他没有礼貌,又是一个美
国人。她恳求我宽她的心,说他仍能回去工作的,我便毫不犹豫地照办了。然后她
又恳求我讲讲她能否信他的话,即他要娶她。现在肚子里有个孩子,又得了性病,
她已不可能再嫁给一个法国人了。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不是?当然,我宽慰她道。
这一切我都清楚极了,只是有一点,菲尔莫怎么居然会爱上了她。不过一次只能做
一件事情,我的职责是安慰她,于是我就给她讲了一大通胡说八道的话,说一切都
会好的,而且我还要作他们孩子的教父呢,等等。这时我才猛地想起这件事很古怪
——她竟还要这个孩子,尤其是他可能一生下来就是瞎子。我尽量委婉地告诉她这
话,她却说,“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要一个跟他生的孩子。”
“哪怕他是瞎子?”我又问。
“我的天呀,别说这些了!”她呻吟道,“别说这些了!”
我仍然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我的职责,她便像一头海象一样猛哭开了,又倒了一
些酒。过了才几分钟她又纵情大笑,她笑是因为想起了他俩上床后常常打架。她说
,“他喜欢我跟他打架,他是个野人。”
我们坐下来正吃饭,吉乃特的一个朋友进来了。她是一个小婊子,住在大厅顶
端。吉乃特马上打发我下楼再去取些酒,待我回来,她俩已经把该谈的都谈到了。
她的朋友——这位伊韦特——在警察局工作。据我推测,她是一个向警方提供情况
的线民,至少她试图叫我相信是这样的。显然她不过是一个小婊子,只是对警方和
他们的工作很着迷罢了。吃饭时她俩一直竭力劝我陪她们去参加一场风笛舞会,她
们想快活一下——“乔乔”住进了医院,吉乃特很寂寞。我告诉她们我得去上班,
不过晚上不当班时我会来带她们出去玩的。同时也讲明了,我没有钱可花在她们身
上。吉乃特一听这个大为惊愕,不过假意说那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只是为了显示她
是一个多么讲交情的人,她竟执意要雇一部车子送我去上班,她这样做是因为我是
“乔乔”的朋友,那么也就是她的朋友啦。我暗想,“还有呢,一旦你的‘乔乔’
出了什么问题,你就会飞快地跑来找我。那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是一个怎样的朋友了
!”我对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