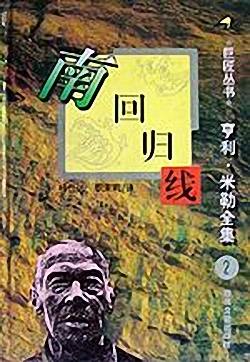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他去饭馆里吃饭纯粹是为了体谅我,他说让我在一边看着他大吃大喝很难受。
我喜欢范诺登,不过我不同意他对自己的看法。譬如,我不同意他自以为是哲
学家或思想家这种看法。他是一个被女人迷得神魂颠倒的人,就是这样。他永远不
会成为一个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永远成不了作家,尽管他的大名在五百支红灯的照
耀下闪闪发光。目前,周围我所尊敬的作家只有卡尔和鲍里斯。
他们着了魔,心灵深处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疯了,不能分辨音调了,他们
是受难者。
莫尔多夫倒是没有发疯,不过他也在以自己的古怪方式受罪,莫尔多夫语无伦
次,他没有血管。心脏和肾。他是一个便于携带的箱子,里面有无数个抽屉,每个
抽屉上都贴着标签,上面的字是用白墨水、棕色墨水、红墨水、蓝墨水写的,还有
朱红、橘黄、淡紫、储、杏黄、大蓝、乌黑、安如葡萄酒色、青鱼色、日冕色、铜
绿色、奶酪色……我把打字机搬进隔壁一间屋里,这样写作时便可从镜子中看见自
己。
塔尼亚同艾琳一样,盼望收到厚厚的信。还有一位塔尼亚,这位塔尼亚像一颗
饱满的种子,把花粉传播到各处,抑或我们也可以说,这有点儿像托尔斯泰和掘出
胎儿的马棚一幕。塔尼亚也是一个狂热的人,她喜欢小便的声音、自由大街的咖啡
馆、孚日广尝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买来的颜色鲜艳的领带、昏昏暗暗的浴室、波尔
图葡萄酒、阿卜杜拉香烟、感人的慢节奏奏鸣曲、扩音机,聚集在一起谈论的一些
趣闻轶事,她的乳房是焦黄色的,系着沉重的吊袜带,她总问别人“几点了”,喜
欢吃肚里填了栗子的金黄色的松鸡,她的手指像塔夫绸般光滑,蒸汽似的昏暗光线
变成了冬青,她患有脚端肥大症、癌症和檐妄症,她的面纱热呼呼的,打赌用的筹
码,铺着血红色的地毯,两条大腿软绵绵的。塔尼亚这样说以便叫人人都听见,“
我爱他!”
鲍里斯喝威士忌喝得浑身发烧时塔尼亚便会说,“坐在这儿!啊,鲍里斯……
俄国……我该怎么办,我都快叫它撑破了。”
到了夜里,我一看到鲍里斯的山羊胡子垂在枕头上便要发歇斯底里,啊,塔尼
亚,你那热呼呼的阴部如今在哪儿?那副又肥又厚的吊袜带、那两条柔软而又粗壮
的大腿又在哪儿?我的胯下有一根六英寸长的骨头。塔尼亚,我要弄平你那充满精
液的阴部上的每一条皱纹。我要先叫你肚子疼、子宫翻个个儿,再把你送到你的西
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喂,他懂得怎样生火,我却明白如何叫女人欲
火中烧。塔尼亚,我把灼热的精液射进你的身体,我叫你的卵巢发热。你的西尔维
斯特这会儿有点吃醋了吧,他觉得不大舒服,是吗?他感觉到我的硕大的阴茎留下
的东西了。我把你那玩艺儿撑大了,我把皱纹都熨平了,跟我干过以后,你尽可同
公马、公牛、公羊、公鸭子和一只瑞士圣伯尔拿僧院驯养的雪山救人犬干。你可以
把癫蛤膜、编幅和蝴蝎塞进你的肛门。只要愿意,你可以奏出一串和音急速弹奏,
或是在肚脐那儿拴上一只齐特拉琴。塔尼亚,我在操你,你就得这样叫我操下去。
若是你不喜欢叫我当着众人的面于,我就在暗中干。
蔚蓝色的天空上鹅毛般的云丝被吹散了,干枯的树木无限延伸,黑呼呼的树枝
像一个有梦游症的人那样打着各种手势。这些阴沉的、鬼怪般的树木的枝干苍白得
像雪茄烟灰。这是一种超然的、全然欧洲式的静寂,百叶窗放下了,店铺闩上了,
这里或那里偶尔可见一盏红灯,表明有人在幽会。其正面粗暴甚至可怕,除了树木
投下星星点点的影子,一片洁净。从奥坦格利经过使我想起另一个巴黎,那便是毛
姆、高更的巴黎,乔治·摩尔的巴黎,我想起那个可怖的西班牙人,他那时正以杂
技演员的步子从一种作风跳跃到另一种作风,使全世界大吃一惊。我想起施本格勒
同他那些可怕的宣言,并且不由得惊异——风格,广义上的风格,是否全完蛋了?
我说我脑子里尽是这些念头,不过这也不是实话。只是到了后来,当我走到塞纳河
对岸、当我把辉煌的灯光甩到身后时我才允许自己胡思乱想这些事儿,眼下我什么
也不想,只感觉到自己这个活生生的人被河水映出的奇迹搞得很伤心,因为这河水
映出了一个已被遗忘的世界。沿河两岸,树木佝偻着身子,在这面没有光泽的镜子
上投下情影,起风时这些树便发出一阵沙沙声,河水翻腾着流过时它们也会流下几
滴眼泪。这条河使我默默无言,我找不到可以倾诉心曲的人,哪怕是一点点也好…
…艾琳的毛病在于她只有一个手提包,却没有阴户。她总想把厚厚的信塞进包里,
信上都是大量闻所未闻的事情,现在她叫劳娜,因而也有阴户了,我知道这一点是
因为她给我们送来了一些下面的毛。劳娜——一头疯狂的驴子,在风中乱闻乱嗅,
以此取乐。在每一座山坡上她都要扮演妓女的角色,有时还在电话亭和卫生间里。
她为金·卡罗尔买了一张床和一只铭刻上他的姓名首字母的刮胡子时用的杯子。她
躺在托特纳姆广场大道上,撩起衣裙用手指弄自己那个地方,还有蜡烛,用罗马蜡
烛和门把手弄。全国找不到一个男人的那玩艺儿大到能令她满意的程度……一个也
没有。男人的玩艺儿一进入她身体便会蜷起来,她需要胀大的阴茎、自动爆炸的纸
火箭和滚烫的蜡油、木焦油。你若是由着她,她会割断你的命根,叫它永远留在她
身体里。劳娜这样的阴户在一百万女人中才有一个!这是试验室里的阴户,没有一
种石蕊试纸能显出它的颜色。这个劳娜还是一个骗子。她从未替卡罗尔买过床,她
用一个威士忌酒瓶砸他的脑袋。她满嘴脏话和承诺。可怜的卡罗尔,他的阴茎只能
在她体内蜷起来然后死掉,只要她吸一口气他那玩艺儿就会掉出来,像一只死泥鳅
一样。
大量的、厚厚的、闻所未闻的信件。一只没有带子的手提包。一个没有插钥匙
的锁孔。她有一张德国人的嘴、一对法国人的耳朵和一个俄国入的屁股,而阴户却
是世界通用的。当国旗挥动时,它便一直红到喉咙处。你从于勒——费里林荫道进
去,从维莱特门出来。你把你的小羊尾放进粪车里,自然是两个轮子的红色粪车。
在乌尔克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水顺着河堤流去,在桥下静静地流淌,仿佛一面镜子
。劳娜如今躺在那儿,河道里满是玻璃碎片。含羞草在哭泣,窗户上有一个潮湿的
、雾状的屁。劳娜是一百万女人中的姣姣者。全是阴户和一截直肠,你可以坐在里
面看中世纪史。
莫尔多夫首先显得像某人的一幅漫画,甲状腺似的眼睛,米什林式的嘴唇,声
音像豌豆汤。他在背心里掖了一个小梨,不论你怎么看他都是那副尊容,随身带着
有个坠子的鼻烟盒,象牙柄的,还有棋子、扇子、教堂地图。他发酵的时间太长,
现在已变得毫无形状了,成了失去维生素的酵母,没有橡皮底座的花瓶。
他家族中的女人们在九世纪曾两次改换祖先,到了文艺复兴期间又换了一次。
他在一次次战乱中、在众多的黄肚皮和白肚皮下留存下来。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前很
久,一个鞑靼人便朝他的血液里哗过唾沫。
他的为难也就是一个侏儒的困惑。透过松球状的眼睛,他看到自己的侧面轮廓
投影在一幅无法计量的幕布上,他的声音使他陶醉,因为它尖细得如间一个针头一
般。他听到的一声大吼对于别人只是尖细的叫唤。
他的头脑,他的头脑是一个圆形剧场,场上的演员一人扮演好几个角色。莫尔
多夫,多才多艺而且不出错,一个个依次扮演着他的角色——小丑、耍把戏的、杂
技演员、牧师、登徒子、江湖骗子。这个圆形剧场太小了,于是他在剧场里安放了
炸药。观众都吃了迷幻药,于是他便把它炸毁了。
我徒劳地企图接近莫尔多夫。这就像企图接近上帝一样,因为莫尔多夫就是上
帝——他本来就是上帝。我只是记载下……我以前就对他有一些看法,现在我放弃
了,而另一些看法现在正在修正中。我把他抓住了,结果发现手中不是蟑螂而是一
只靖蜒。他的粗鲁冒犯了我,然而他的脆弱又叫我为之倾倒。
他滔滔不绝直到把自个儿憋得透不过气来,随后又像约旦河一样沉默无语。
每当我看着他小跑着走上前来迎接我,伸出一对小爪子,眼睛里流着泪,我便
觉得自己在同……不,这句话不能这么说。
“像在喷泉上跳跃的鸡蛋。”
他只有一根手杖———根普通的手杖。他的衣袋里装了一张张纸,都是治疗悲
观狂的处方。他的病现在痊愈了,替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因而悲痛欲绝。这正
如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背着他的古吉拉特语字典到处走。“对人人都不可避免”
,这后无疑就是指“绝对必要的”。博罗夫斯基会觉得这话不可理喻,一星期里每
天他都要换一根手杖,还有一根是复活节专用的。
我们彼此间有这么多共同点,看别人便犹如在一面裂了缝的镜子里看自己。
我一直在翻阅我的手稿,每一页上都是潦草涂改过的手迹。
全是文学!我有点害怕。这多么像莫尔多夫,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非犹太
人的异教徒,而异教徒受苦受难的方式是不同的。
据西尔维斯特讲,他们虽有痛苦,但却不患神经病,而一个从未患过神经病的
人是不懂什么叫作痛苦的。
于是我清楚地回忆起我痛苦时是多么快活,那正像带着一头小熊仔上床睡觉,
有时它会用爪子抓你,那时你才真正知道害怕。平时你不会怕——你可以放掉它,
或者把它的头砍掉。
有些人无法抵御钻进野兽笼子里、同野兽在一起厮混的欲望,他们连手枪、鞭
子都不带便进去了,正是恐惧使他们变得无所畏惧……对于一个犹大人,全世界便
是一个野兽横行的笼子。笼门锁上了,他在笼子里,没有手枪、鞭子,但他勇气十
足,甚至嗅不到笼子角落里的兽粪味。围观者在拍手,可他听不见,他认为这场戏
是在笼子里面演的,他认为这个笼子便是整个世界,门锁上了,他独自一人无助地
站在那儿,发现狮子不懂他的话。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人斯宾诺莎?它们
干吗不咬他?“给我们肉吃!”它们吼道,而他却站在那儿吓呆了,脑子全乱了,
他的世界观也变成一个荡到空中再也够不到的秋千。狮子举起爪子扇一下,他的世
界便被打得粉碎。
同样,狮子们也失望了。它们期待的是血,是骨头,是软骨,是筋,它们嚼了
又嚼,然而词汇是无味的树胶,树胶是无法消化的。你可以朝树胶上撒糖、助消化
药、百里香草汁和甘草汁,待树胶被树胶收集者裹起来后便好消化了,这些树胶收
集者是沿着一个业已下沉的大陆的山脊来的,他们带来了一种代数语言,在亚利桑
那沙漠中他们遇到了北方的蒙古人,这些人像茄子一样光滑。这是地球呈陀螺仪状
倾斜后不久的事情,当时墨西哥湾流同日本湾流分道扬镳了。在地球的中心他们找
到了石灰岩,于是他们将自己的语言绣在地壳底下。他们吃伙伴的内脏,森林围住
了他们,围住了他们的骨头,脑壳和饰有花边的石灰岩,他们的语言便消失了。人
们有时在这儿或那儿仍找得到一个兽群遗骸,一个被各种塑像所覆盖的头盖骨。
这一切与你有什么关系,莫尔多夫?你口中的话是杂乱无章的,说吧,莫尔多
夫,我正等着你说呢。当咱俩握手时,谁也感觉不到透过我们汗水浇下的大量的水
。每当想词儿时,你总是半张着嘴,唾液在你腮帮子里面流淌。我一跃跳过了半个
亚洲,我到那儿丢捡你的手杖,尽管这是一技普普通通的手杖。
在你身体一侧戳一个洞,我便可以搜集到足够塞满大英博物馆的东西。我们站
上五分钟便可吞没很多个世纪。你是一个筛子,我的模糊想法便是通过它滤下去并
且变成言语的,言语后面是一片混乱,每个词是一条、是一杠,只是杠还不够,永
远无法做成一只筛子。
我不在家时窗帘挂上了,它们看起来像在来苏水里浸过的奥地利蒂罗尔州出产
的桌布。屋里光芒四射,我迷迷糊糊地坐在床上,想着人类诞生前是什么样子。突
然钟声响了,这是一种稀奇古怪、绝非人世的曲调,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的大草原
上。有些曲子缕缕不绝、余音绕梁,有些则一倾而出,缠绵悱恻。如今一切又都归
于寂静,只有最后一个音符仍在飘荡,这只是一只微弱的高音锣,响了一声便像一
个人苗一样熄灭了,它几乎无法划破这静谧的夜。
我曾跟自己订立了一个无言的契约:写过的东西不再改动一行。我对完善自己
的思想或行动并无兴趣,我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完美与屠格涅夫的完美等量齐观(
还有什么比《永久的丈夫》更完美的?)。于是,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类完
美。
然而在凡高的信中还提到一种超出这两类完美的完美,这便是个人战胜了艺术
。
现在只有一件事使我极感兴趣,这就是记下书中遗漏的一切,就我所知,还没
有人利用空气来给我们的生活指示方向,提供动机的各种元素,只有杀人狂似乎在
从生活中重新汲取一定量的他们早先投入生活中的东西。这个时代呼唤暴力,可我
们只得到了失效的炸药。革命不是尚在萌芽中便被扼杀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
便丧失殆尽,人们便转而求助于思想,这已是常规。提出来的建议没有一项能维持
二十四小时以上。我们要在一代人生活的这段时间里生活一百万次,在对昆虫学、
深海生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学到更多……电话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永
远无法把这件事情想清楚。
有人来租这所公寓了……
看来我在波勒兹别墅的生活要结束了,好吧,我就收拾起这些手稿走路好了,
别处也会发生一些事情。事情总是在发生,不论我走到哪里,那儿总有戏看。人就
像虱子一样,他们钻到你皮肤下面,躲藏在那儿。于是你搔了又搔,直到搔出血来
,可还是无法永远摆脱虱子的骚扰。在我所到之处,人们都在把自个儿的生活弄得
一团糟,人人都有难言的隐痛。厄运、无聊、忧伤和自杀,这些都是从娘胎里带来
的。四周的气氛中弥漫着灾难、挫折和徒劳无功。搔吧,搔吧,直到一块好皮肤也
不剩。这结果令我兴奋不已,我不但不灰心丧气,反而很开心。我高声呼唤更多。
更大的灾难和更惨重的失败,我要叫全世界乱成一团,我要叫每个人都把自己搔死
。
连这些支离破碎的笔记我几乎都没有时间记,因为我是被人逼迫过着节奏快而
又忙乱的生活的呀。来过电话后,一位先生和他太太来了,在他们谈话期间我上楼
去躺下来,我躺着,盘算下一步该怎么办。当然不能回到那个妖怪的床上整夜翻来
覆去用大脚趾头弹面包屑。这个令人作呕的小杂种;若是还有比当妖怪更糟糕的那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