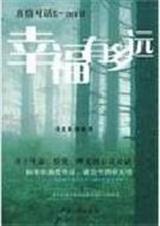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й��˵��Ҹ���-��16��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ı߽磨Լǰ200��300�꣩��һ�ڡ�����δ���Ĺ�ȥ��9��
����88��Ȼ�������ǵ���Դ��20���͵�����˼������ʷ��ѧ��ӳ���У��Լ�������ʱ�����Ķ��й���ʷ���ڵĿ���ϰ���У����������˶�����ѭ���۽����Ļ������������Dz�û�п�����ʷ��չ�ľ�ͷ�����ʡ��롰�ġ���ijЩʱ���ǿ��Ա�ͨ�ģ�������һ����Ϊ�ӹ㷺�۲��������ѧ�ṩ�����ۻ�����������Ϊ�����й���ʷ�ϣ���ƽʱ�������ڷdz�ǿ���ġ��������˷����������Ķ���ʱ��֮�����٣��纺֮ǰ���أ�����ǰ���峯������ǰ�Ǻ��ܣ�����ǰҲ����ˡ�����������ʱ����������ص�ʱ�ڣ��������������ռ��ͳ�ε�λ�ij����н�Ȼ��ͬ������ż������������������������ʱ�����������ͳ�κ��ƻ�������䣬��Ҳ���ɳ�Ϊ�����ҡ���ʱ����������ڴ˲������·��ִ�ͳ����������ѭ����ͼʽ�������ѧ�ҷ�����ͨ���ٳ��ִ�����֤��ͼ���������ĺڡ��ס���ɫ��ϵ�С�����1948����Ӣ��д�͵ġ������й���ѧʷ���У�������˵��������������ּ��������������������䣨����Ȼ����ֻ���ɺϡ�����ͼ����������Э��������Ȼ����������Ϊ��һ˼�����������������ִ������������Ȥ�ģ�ɫ��Ҳ������������ͬ��������ƣ����維����ġ�������ʱ�ڣ�����������������ۣ����ǿ���˵����˹������ɫͳ�Σ��ʱ����������ɫͳ�Σ�����������������ɫͳ�Ρ�����������
������ҫ�ŵ�ƽ���ϵ�ңԶ����⣬1912��1949��������ΰ����ռ�Ŀ�����DZ�����Ϊ���·��ֵġ���ͬ�������һ������ҵ��ǣ��˿���һ������Ϊ���ǵ������Ѿ���ʱ���������ʣ����ԡ�����������ɽ�����������˾�����Ӱ�죬��ʹ֮�����ڽ���̨��質������̸��С�����������ʱ�ڣ���Ҳ��Ϊ����ֲ���й���˼�����������ѧ�Ҿ�����������Ҵ�δ��ʧ�����ڳ�����1959����ĿΪ���й���ͬ˼�����ϡ�һ��ĵ����У�������һ�����ڳ������а�˼���ѡ����Ҳ���Կ�����һ�㡣�ڵ����б���˵����������ʹ��ͨ�е������ʡ����С�һ�ʷ��롰���а�ļ������ɣ���Ϊ�����������������а��һ�����õ��뷨���������������ұ����˸�����ں���������֮���ȷʵ������ѡ���ˡ���ͬ����Ϊ���룬����ָ������ͬ�ۡ�Ϊ�й�������������˶���ǰ���Ǽ�����ܺõ����á�����ȷ�����ǣ���Щ��һ����ͼ�ں��¾ɵ��˺���Ϊ�˶��ܵ���������Ȼ��������Ŭ������Щ������������ʷ��Դ��Ŀ�ġ���������һ���Ǵ���ʷ����Ϯ�������˿����������������ģ���ǧ���������Ǵ�δ��ͼ������һ�㡣����������µģ������ʷ��ѧ��ɵ���ѧ֮�佨����ϵ�Ͳ������˾����ˣ�����������ϵ����������ʶ�ġ����ܵģ������������������Ȼ��Ϊ��
�������֣�����ı߽磨Լǰ200��300�꣩�ڶ��ڡ�λ�����羡ͷ�Ĺ��ң�1����
�������Ϸ�����Ϊ������ģʽ��������
����ʱ�չ۵Ļ����ı�Դ�����������أ�һ�������ؾ����ͻ�������������棬����������ģ���������ع����á����ڹ��ҵ�ͳһ�뿤�صĻ��֣����С��������������һ�����ܸУ���֮������������ĸ��ܣ����������ڴ��֮�У���ңԶ�Ļʶ�ͳ�Σ����һ������Ͽ���رߵ��⽻���ߡ�������Ԫǰ���������ڵ��ܳ�ĩ��ʱ��ֻ�н����й���������ı��������й��˵�����������������ɿ������й��������ֵ������������˿��ƣ������������������۹��Ķ�����Ե�����DZ����ʣ����ϵ�������Խռ�ݡ������أ��й���ͬĿǰ���������Ӧ�������̶̿�����������Щ�ߵع��ң�����������Ԫǰ125�꣬��平�ʹ������������ϸ�ļ��ء�ʱ�չ��ڶ����еķ�չ������������Ȼì�ܵ���������ʵ�ϻ�Ϊ����ĺ�����Ը��˿ռ����ǿ���Ե�ѹ�����������е���������ģ��չ�������ڵ��ҵ�����������һ��������ĵ���һ��ɢ���ڡ���Ƕ�ڻ����������Ҹ��Ĵ���Ȼ�С������������˼��Σ�յش����ţ�������δ�ܹ���ֹ���������Ұ���ܺ����Ѻ�����ֹ�������ɻ���ƾӣ�����������Ϊ���ҹ����ṩ��˼���������ʱ�������Ǽ����Ա�����۵Ľ�����������������ƾӵĿ����ԣ����ߣ����پ۽��������ֹ�������ⲿ����������ӿ����������ĸ��ܣ���Ȼ������ı���Ҳ˵���������ĸ��ܡ������س���ʼ�����ƻ�������ȫ�ı��ˡ���Ϊͳһ�Ĺ��ҽ��������������Dz����ܵġ�������������ͳ���£�����õ���ͳһ����չ��90��������������֮���е�һ�鵺�죬�����෴��������֮�ط�Χ��ֻ�к���һЩ��Ұ֮���Ĵ��ڡ����ڸ�ҥ������ġ�ɽ�������Ϊ���оܾ����������������ǵı����أ���Щ�˰���ǰ����˵�����������̵���ʿ��ͬʱ���������м����������е�˼��ͻ���������ⷢչ����Ȼ��Щ˼��������ڣ���������Ѱ���ӱ��������ʱ���ͻ�����״�Խ��һ�������Ӷ�ʹ��Щ˼���һ�������ƽ�������ȷ���������Ҹ������紦��ңԶ���������磬�����ǽ�����������Լ����ڹŴ������µĿɼ������ֲ����С�������Ϊ�������Ż��в����й�Ȩ��ͳϽ�������������������ۡ���������������ʱ�����ţ��й�ֻռȫ�����1/81�������Dz��ܳ����ֹ۵㣬����ڽ���ʱ���ܳ��������۹�����ʱ����ɽ������д�ɣ������жԱߵ���������ķ����������档�Ӵ������ǵ��ܹ�֤���IJ������������ܵó��Ľ����ǣ���Щ������Ϊ����Ҿ�������ٵIJ���Ҳ������Ҫ�����á���������
���������ĸ�ɽ�붫���Ĵ���ʵ�����й��Ļ���ɢ����Զ���������������Ϊ�˶���ο��������Ϊ�˶���㨣������ն�����Ϊ��ϲ���ˡ���������ʹ��ȷ�ŵ����ǣ���Щ�������Ҳ��Ϊͨ�����õĴ��ţ����ǰ�Ŀ��Ͷ��Զ���IJ����ŵĴ�֮�⣬Խ�����ص�ɽ����Ͽ���Լ��������˵Ļ��죬���Ǹе�����������������һ�������������������һ�����������ӱ������������ơ������������Ŀռ���չ��ǰ����˵��ҥ�����������������������������������Ҹ��볤������֮�ء���ס�ڱ߾����ص�����ɽ��������˵ͳ���������ɾ�������Զ�ĺ��ϣ����й��Ķ�����Զ��һ�顰���������ع��Ļʵ����״�����ȥ̽Ѱ����ֱ������ʱ���˵��������ȫ�õ�ʵ�֡����������ʱ��ǰ140��ǰ86�꣩������̽Ѱʮ��ʢ�У���۷dz������ڷ���������ڹ�͢ʱ�ۼ���һ����ʿ���������Ŵ�˵����Щ���ҵIJƱ���ʹ�й���ʢ���ʵ۸��У���һ�����ƺ���ѿ����������ÿһ���䣬�ѵõ��ִ��о����ǵ�֤ʵ�������Է�����ȡ�˿�����ΪҲ��������Ȼ�ģ���Ϊ���������˷�������Ȥ֮ʱ��Ҳ�ܵ��˳�Ū������̽Ѱ������Ʒ�Ĺ����У���һ���������Ū����ʼ�ʣ��Ǿ��dz������ϵ��ɵ�����������
����91����ЩңԶ������֮�صļ��أ�����������Ϊ��Щ����������֮�صľ���ʢ����ңԶ��������������س�����������Ƶ�������ε������ı�Ե������������˴��ִ����Χ����Ϊ���������Χ�ı仯������ͨ��ʱ�������ص���ȥ������Ҳ�����������Ľ������Щ�������������ݵ�������ȫ��˵�̵ģ���û�зḻ����ġ���������������ܷ��ֵġ�ׯ�ӡ�һ��Ĺ����������Ԣ�Ե����ʡ���Ȼ����û�������˹�ͬ�������Ĺ۵㣬�����˻��ǽ��������Ĺ۵㡣��λ������һ������������������β����۳���ֻͨ������ı仯����һ���������У���������
�����������ż�³�³������ɫ��������Ի��������ɫ����Ҳ��³��Ի����ѧ����֮�������Ⱦ�֮ҵ���ᾴ��������ͣ�����ֹ����������ӣ�Ȼ�����ڻ����������ǡ�������Ի����֮����֮��dz�ӣ������ı�������ɽ�֣�������Ѩ����Ҳ��ҹ����ӣ���Ҳ��������Լ���̵������ڽ���֮�϶���ʳ�ɣ���Ҳ��Ȼ�Ҳ�����������֮�����Ǻ���֮���գ���ƤΪ֮��Ҳ����³�����Ǿ�֮ƤҮ����Ը������ȥƤ������ȥ��������������֮Ұ����Խ�����ɣ���ԻΪ����֮�����������ӣ���˽��������֪������֪�أ���������䱨����֪��֮���ʣ���֪��֮���������������˵��ڴ��������֣��������ᡣ��Ը��ȥ�����ף�����ศ���С���Ի�������Զ���գ����н�ɽ�������۳����κΣ�������Ի���������������ӣ���Ϊ�۳�����Ի���������Զ�����ˣ���˭��Ϊ�ڣ�������������ʳ�����ö����ɣ�������Ի���پ�֮�ѣ��Ѿ�֮���������������㡣�������ڽ������ں�����֮���������£���������֪������;��߽����¶��������Դ�Զ�ӡ����������ۣ������������ǣ���Ң�����ˣ��Ǽ�������Ҳ����Ըȥ��֮�ۣ�����֮�ǣ�����������ڴ�Ī֧����
�������֣�����ı߽磨Լǰ200��300�꣩�ڶ��ڡ�λ�����羡ͷ�Ĺ��ң�2����
����92�ں�����������������֮�ص�����У���Ҳû���κ��������롶ׯ�ӡ�һ���������ĸ���һ�������������ϼ���������꣬������鸣��ֻ�ܾ���һ����·����������������ǡ�ׯ�ӡ�һ�����ɫ������������һ�����˻���֮��������ʫ����桪���������������ӱܵŶ����������������߸�Ϊ�侲����Ϊ���ԣ�����³����뷨��һ�£��ڡ����ӡ����й��½��оͿɼ���Щ�ַ������ã�������Щ�ַ���Ӧ��Զ����ȫû�и�Ϊ��̵��������壬��Ҳ������չ�ָ����ǵ��Ǵ�ʱ�˵ص����磬�й�����������ѽ�ϳ�һ���෴��ɵ����壬��һ��ר��������ڵ����Ϻ͵����϶���������λ�õġ�����֮������������ѡ��Ĵʾ����������������º��ѿ������Ƕ��й������ﻹ�������������Ķ���ʮ����Ȥ����Ϊ���������Դ���й���Ըͨ������ʷ����������ͬʱ��������ֱ������һЩʱ����Ȼ�������˶������������������ƽ�⣺��������
��������֮�����й��ɣ���֪����֮���ӣ�����ç֮��������֮�����������ʺ������棬����֮�������գ�����ҹ�ޱ档����ʳ���£������ߣ���Ѯһ������������Ϊ��ʵ����֮�����������ĺ�֮�룬ν����֮��������ϱ���Խ᷶������������������֮��ȣ���һ��һ�����֮�ֲ죬��һ��һҹ�������������ޣ�������ֳ�����ն���о������ڣ�����֣�������Ϊ�����ɳƼƣ�һ��һ�£���Ϊ��֮��Ϊ��ʵ����֮�м�����������֮�����й���Ի����֮�������������ۣ��������֮���������������磬����ʳ�ݸ�ľʳ����֪��ʳ���Ըպ���ǿ���༮����ʤ�������壬��۲�������Ϣ�����������ߡ���������
����93����ȷ�����ǣ������������й��������ط����������ã�һ��������ȱ���������Զ�����Ϊ��������ڣ���һ���棬Ҳ���Ա���Ϊ����������Ҫ��ͬʱ���ֶ������һ�ּ��˵Ĵ��ڡ�һ���Ǻڰ�����ƽ����˯�Ĺ��ȣ���һ������������ִ�����ѵĹ��ȣ��ڴˣ������Ѿ����Կ������ӶԹ�ç������ͬ�����Կ���������Ϊ��ç��������Ĵ��ڶ�����һ�ּ��˵Ĵ��ڣ���Ȼ���dz��ڵ��̵������������ĸ���������������ǹ�ç�������͵���˳��ȱ������Լ���������������ǰ�������Ķ�����ʱ����������ռ�����ơ��������ǵ��ң������������ɱ������ۣ������������Ҳ��Ϊ������ڵģ���ʵ���ܱ���Ϊ��һ�����롪��������ǰ�Ļ������������ֻ��μ�����������������ľ������������һ���棬���������һ�������궯�����ĸ������������Ȳ�������ִռ�����ǵ������Ȼ����а�������ڵ������������á��������������Եر����������й���һ���;��Ƶ۵Ĺ����У��������ǽ����Ƶ�����ͳ�ι��ң�Ȼ��������������Ĺ��£���������
�������Ƶۣ������Σ����ڻ�����֮�����ڏm��֮����̨��֮������֪˹�����ǧ��Ƿ��۳�����֮���������ζ��ѡ������˧������Ȼ���ѡ���������������Ȼ���ѡ���֪��������֪����������ز�䡣��֪������֪�E��ް�������֪���棬��֪��˳��������������������ϧ��������η�ɣ���ˮ���磬����ȣ���̢����ʹ��ָ����ޯh�����˿�����ʵ���������������������v���ӣ�����������£��������ġ�ɽ�Ȳ����䲽�����ж��ѡ��Ƶۼ�廣���Ȼ�Եá�����������̫ɽ����֮Ի�����о�����ի�ķ��Σ�˼������������֮��������������ƣ��˯���������ˣ���֪���������������ӣ���֪֮�ӣ���֮�ӣ��������Ը����ӡ��ֶ�ʮ�а��꣬���´��Σ�����������֮�������۵Ǽ٣����պ�֮�����겻ꡡ���������
����94����ǰ���ἰ�ĻƵ�֮���һλ�;������������Ŵ�˵ɫ�ʵ���ʷ��������һ���ƺ�Ҳ����������صĹ������ݴ�ͳ˵��������λ�ڹ�Ԫǰ1001��ǰ946�꣬��ʷ��ʵ�����ˣ����ڡ����ӡ�һ�����Ŵγ��ֶ���һ���ȵ������������������ǵ�����Щ�ط������о������������˺�����ij��������ҹ���ķ�չ����Щ��Ʒ����������Ԣ���Ե��������ı�Ҳ�ܿ��Եÿۡ��꾡����Ҳ���������е��£�����������������������ʵ�����������������Ե�������һ��������������ǰ����λ����ǰ���ġ�ׯ�ӡ��Լ������ӡ�ƪ���У����Dz������Կ����������ȱ��ֳ��ľ���֮���ƽ�ȣ����һ����Կ���������������֮���ƽ�ȣ���Ů֮���ƽ�ȣ���������
������֮��ˮ��Ҳ���Զ�ʧ;����֮һ����������֮������֪�����ݼ�ǧ��������Ի�ձ�����֪����֮�����ޣ�����˪¶�������������ľ֮�ࡣ�ķ�Ϥƽ���������졣����֮����ɽ��ɽ�����죬״�����I�����пڣ�״��Բ������ˮӿ������Ի��寣�����������ζ��������һԴ��Ϊ������ע��ɽ�£���Ӫһ��������Ϥ�顣�����ͣ�����������������ӣ��������������Ķ����ǣ��������ɣ�����٭�ӣ�������������Ů���Σ���ý��Ƹ��Եˮ���ӣ��������ڣ��������ʣ���֯���£������������ز���䣬�����ܸ���������ϲ�֣���˥��˥�࣬����������Я����ҥ�����ղ����������������寣���־��ƽ������������Ѯ��������ԡ��寣���ɫ֬��������Ѯ��Ъ�����������Σ���������꣬���顣�ȷ�����Ľ������Ȼ��ʧ���������ڣ��������������¡�
�������֣�����ı߽磨Լǰ200��300�꣩�ڶ��ڡ�λ�����羡ͷ�Ĺ��ң�3����
�������������������ɵõ������֮�ء�������
�����������Ǵ����й��ļ���֮������żȻ����Ϊ��һ˼��Դ����ӡ�ȣ����ɣ�����֪��ӡ�ȵ�������Ҳ�����õ�λ�ö��ڼ���֮�������˶��⣬����ʱ�й��Ķ������ǵ���ѧ˵�����ġ�ǰ�����������λ�ڴ˵أ�Ҳ�������й���ǰ������ʱ������ѧ�������У������Dz���Ѱ��������Ϊ�е��ǻۣ��������ȶ�����ӳ���������Ȥ����������������ǰ�����Ŵ�����ͼ�ϵ������Ͷ�����ָ��������õķ�����ǰ���ἰ�Ĵ�˵����ʷ�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