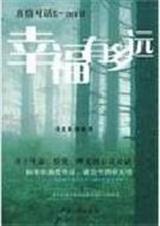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笆觯糯烨蛲忌系奈鞣胶投狡渲赶蚓褪翘焯玫姆较颉8萸八峒暗拇担飞系闹苣峦踉谙蛭骱拖虮钡穆眯兄刑岬焦魍跄福欠⑾治魍跄柑焯玫牡谝蝗恕F鹣龋臃⒁羯侠纯矗拔魍跄浮闭庖淮仕坪醪⒉槐硎臼裁矗梢运凳且桓鐾饫创剩皇侵泄鞑康男」慌銮善渥詈笠桓鲆艚趍u的发音在书写上的文字是“母”,而“母”表示“母亲”的意思,但到了后来,人们对这一词义进行了想像,“西王母”就由表示“王母”统治的仙境的这样一个地名变成了人名。因为在汉朝开始出现大量关于昆仑山这一地区的传说。另一方面,《列子》中的看法也大部分与古代历史典籍《穆天子传》、《竹书经年》中的评价相似。它用精确的笔触记载了穆天子对这一地区统治者的造访:
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而封之,以诒后世。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王谣,王和之,其辞哀焉。犹观日之所入,一日行万里,乃叹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谐于乐,后世其追数吾过乎。
由于已可辨明天堂所处的方向,天堂观有了发展。以一种非常贵族的、精英的意识来看,西王母王国不再是有一个天堂般秩序的国家,而是一个保有幸福的避难所。“王母”的宫廷有无数的仆人则表现了皇帝宫廷的性质。尽管其他人也拥有一些重要的物品,名义上的长生成仙,但实际上只有帝国的统治者才享有完全的幸福。居住在北方天堂里的这些人被统治者毫无怜惜地抛弃了。在道家哲人刘安(前179…前122年)的文集《淮南子》中保留了一份相对来说较早的记载,此记载在这方面指出:
96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地,浸入黄水,黄水三周复其原,是谓丹水,饮之不死。……昆仑之邱,或上信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据后代记载,仙桃据说也是在昆仑的悬圃中成熟的。“长生成仙”一而再、再而三地刺激着人们对这个国度探险的兴趣,而这一国度又是如此难以找寻。正如受神话影响的早期传说中记载的,仙桃被带回来了,有时甚至是偷回来的。此外,关于它还有许多新的各种各样的传说不断被人们讲述流传至今。另一方面西王母山宫中的生活只有很小的吸引力,它并非一个人渴望获得幸福的所在,除非这个人就是国王自己,因而西王母的王国成为一个容纳各不相同的迸散了的神话碎片的储蓄器,但它绝不是承诺之地,能兑现人们的理想,使人们的理想于现世有意义。
在对远离中国东海岸的海上三神山的描述中,隐约体现了这一点。这三岛的名称是蓬莱、方丈、瀛洲。起初,它们是很普遍的地名。然而这三个词暗示了超自然元素的存在:“莱”是传说中贤人“老莱子”姓名中的一部分,一开始,他的传记是与老子的合在一起的;“方”则不仅意味着“方正”,还意味着“神奇”,而“瀛”不仅指普通的海洋,而且还指包围着陆地的有很多岛屿的海洋。这三词还包含不同的变体(种种变体还有“方壶”,“三壶”即三岛,两者都依次使人想到北方天堂里的壶瓴山)。不久,这三个岛屿代表了幸福的实质。在历史著作《史记》中,看不到秦始皇期许长生不老药失望的记载。但在《史记》的另一章中却很严肃地讨论这三个岛屿。尽管它表明所有这些都是秦朝宫廷里术士们的欺骗,而方士们谈到这些岛屿存在时也总是那么不折不扣:
97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二节 位于世界尽头的国家(4)
在现实主义的历史学家的记载中,这些天堂般的岛屿是作为海市蜃楼出现的。《列子》一书则把它们变为纯粹神话般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许多别样的奇异时刻也决定着事实。实际上,这样的描述是毫无意义的。其更为深刻的意义是作为一个更为拓展了的论点的一部分(此处略),它是作为所有重大秩序之间相互依存性的颇富色彩的象征:
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无谷,其下无底,名曰归虚。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舆,二曰员峤,三曰方壶,四曰瀛洲,五曰蓬莱。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鹘源陨到杂凶涛叮持圆焕喜凰溃又耍韵墒ブ郑蝗找幌Ψ上嗤凑撸豢墒伞6迳街匏撸K娉辈ㄉ舷峦梗皇侵叛伞O墒ザ局咧诘郏劭至饔谖骷Ьブ樱嗣钩际寰偈锥髦A蛩暌唤谎伞N迳绞贾牛写笕司僮悴挥蕉呶迳街R坏龆:细憾ぃ槠涔破涔且允伞S谑轻酚摺⒃贬蕉搅饔诒奔蛴诖蠛#墒ブデㄕ呔抟诩啤?br>;
汉以后的五百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燃烧着宗教热情的年代。人们大量描绘着人类世界周围的海上三神山。它们已显示了印度影响的痕迹,刚才所引的故事已被认为是如此,至少神负山就已显示了印度的影响。环绕“九洲”的大洋据一般人看来,似乎点缀着这些纯粹的幸福之地。它们形成的链环是太阳经过的地方,它们的大小与地理位置也越来越被人们审慎地、精确地描绘出来,事实上绘出所有这些岛屿或神山的图是不难的,这些观念产生是因为这些岛屿就是山,正如谎言所暗示的。和以前祈求福地的实践相对照,此时则采取通过天上的飞翔来到达福地的行为方式。最近的岛屿也有千百里,因而任何人都不能到达,除非他是神仙才能依靠双翼的飞翔才能到达福地。
98但当描述的福岛数目大量增加时,对那儿情景的描绘则变得更平淡无味了,没有实在内容,往往用原先的岛屿之名作为题目,如“蓬莱”,大量的记载叙述都显得缺少情感,毫无艺术感地被牵强附会地连缀成篇。这些描述因而只是一些神话、鬼怪故事、哲学以及伪科学理论的断简残篇。为它们在创造所谓天文探索的兴趣时,它们从来也没有考虑过真正的科学知识结构。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再去处理关于天堂的记载,而是要分析文中表现的完美的普通国家,这些国家具有我们熟悉的国家机器中的统治者和官员:“居民的风俗与吴人相像”(吴,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再如,在这样的记载中还这样简洁地写道:在其他方面每件事和中央之国一样。绝大部分情况下于中国而言,这些岛屿只是作为地理名称而存在(即如《列子》中的古莽国,阜落国一样),也或者是科学理论的通俗呈现而已。天上和地心四个方向的五个天堂作为一个范例,据其占主导方面的色彩和材料(黄、绿、白、红、黑)早就被认为是五行的王国了。总的说来,能够唤起读者对天堂回想的还是读者看到的对获取长生不老的方法审慎而精确的描绘,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求仙得道的方式,天堂般的国家就不会存在了。尽管在描述中加上了新的长生不老药仙丹,增添了诸如仙草,或者珍稀的犀牛角之类的药膏,但它们也还流于陈词滥调,没有一个形象具有山涧溪流般的清新与活力。事实上,在更多情况下,它们只是无力的模仿。我们看到传送给人幸福的小溪流取代了所有居于中央而滋养人生命的泉流。这些小溪中充斥着成千的珍奇物品,而且在描述上通常用这样的枯燥的模式化的语言,“……啊,有一个泉叫……他喝了泉水后就成仙了。”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二节 位于世界尽头的国家(5)
100与人间天堂的膨胀相比——这种膨胀日益受佛教的间接影响,显然,对天上的天堂的描绘还是极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尽管从汉以来天堂的存在一直是人们信仰的主要内容,但这也是可能的——天堂的开放性使人们很少能想像真实的世界。更早一些时候人们迷恋于穿越云中山峦而到达天堂,而不是成为云中宫阙的一分子。另一方面,云雾缭绕的天堂般的山峦是天国的一个区域,它还有其特别之处,即根植于现世。《淮南子》中即提到过这一罕见的山峦,据说它与天国联通,形成上天与下界之间的一座桥梁。
稍后,银河也被看作类似于桥梁的连结物,因为它被认为是大海向天国的延伸。如诗人、文人张华在所著《博物志》中,用精神的笔触这么写道:
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滨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斋粮,乘槎而去,十余日,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
这是一段在早期的古典文献中很少见的文字,在这段文字里不仅描绘了云中世界,而且也描述了彼岸天国。《列子》中也可见到。一度周穆王这个伟大的上天与下界之间的漫游者被赋予了超人的经验。《列子》中记载了周穆王宫廷中受其崇拜的术士“化人”,这些术士提出许多使周王满意的要求,周王倾其所有珍宝为自己建成一座“中天之台”,给他们提供了芳泽娥媚,珍馐美馔、艳服华裳,而所有这些也都没有辜负方士们对幸福生活的期待。接着《列子》写道:
谒王同游。王执化人之祛,腾而上者中天犹止。暨及化人之宫。化人之宫构以金银,络以珠玉,出云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据,望之若屯云焉。耳目所观听,鼻口所纳尝,非人间之有。王实以为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王俯而视之,其宫榭若累块积苏焉。王自以居数十年不思其国也。化人复谒王同游,所及之处,仰不见日月,俯不见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得视,音响所来,王耳乱不能得听。百骸六藏悸而不凝,意迷情丧,请化人求还。化人移之。王若殒虚焉,既寤,所坐犹向者之处,侍御犹向者之人,视其前,则酒未清,肴未昲。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更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疑亡。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
第三部分:世界的边界(约前200—300年)第二节 位于世界尽头的国家(6)
对上天的恐惧和对大地的深情
101天国观是盛宴后的狂欢,因为与人间天堂相比,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在任何地方,天堂都被人们体会为彼岸的超卓的极富自然力空间。不是被人们发现或重新发现的天堂里的生命,而是天国里的生命它要求一种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即“飞翔”的特性,也是惟一的大自然不能给予人类的运动方式。中国的故事和传说都把天国作为幸福的处所,因而这就非常清晰地以人们喜欢的形式反映了正在改变中的价值观,概言之这一价值观是哲学与超然存在的一致。在《庄子》一书后面的一些篇章中讲到在超越尘世的天空中的漫步,或者讲到人死后的幸福生活,有着一种真正可以理解为彼岸世界的东西,而在《庄子》的前些部分中任何一章都未发现。但中国人的思维明显地指向现世世界,因而只有在短暂的过渡时代,才会承受上天下界两个世界的分离。准确地说,在天堂的描绘中,再度采取了与现世相结合的方法。从一个难以想像的,超绝的梦中形象到一个几乎令人尴尬的真实的地理上可以标明的地方,这种变化可以通过它们所有的过渡形式而考察到。如前所述,天国逃脱了这种人们难以理解的命运——使天国变成了被人们殖民的,可以度量的、计划的事物,因而它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超自然的空间,但这并非其存在的原因。准确地说天国被人们遗忘,它不比那连绵的岛屿和山峦更能满足人们的目的。无数的时代在圣人的传说中描绘着天国的主人身着华服来到人间倾听天籁,他们显然是从上界来的;同样,已经成仙的圣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山中来到地上已屡见不鲜。但很多实例中都很难看到天国是否就是他们真正的家,或者也很难看到他们并不仅仅是通过驾云来缩短遥远的人间天堂与人们居住的陆地之间的路程。
在古老的年代,人们对域外世界的设想是通过对现世朴素的认同开始的。将近周代末年就对真正的超俗事物有了好感,尤其是在与死亡相关联时。汉朝则产生了进一步的差别,一度曾通过把超绝脱俗的东西置入现世来制造某种天堂与人世的合成物,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后来陪葬品的渐渐的变化。这种进步性变化是把天堂置入人间的说明:商以前伴以活人、动物以及符号,因为在商以前,书写还不为人所知;在商与周早期,容器上有了文字说明。这种方法一直沿用至汉朝。汉时使用这些东西的模型、仿制品,一度将它们放进坟墓,例如,人、祭文都用陶土制成以代表真的实物。在实际操作中,还增加了以前没有放进坟墓的物品,如房屋、庭院。坟墓本身也是一所房屋,用石头精心建造,装以墙饰,浮雕、彩绘。公元头四个世纪里,建筑了无数这样的墓穴,墓穴中塞满了陶俑,一直沿袭到唐朝,只不过是以更为精美的形式来制造了(如唐三彩马)。它们表明彼岸世界是多么近,某种程度上,每一个愿望、每一个想法在现世还是纯粹的精神的,在彼岸世界里自动地就成为现实了。
102因而,人们还尽力地把天堂与人间连在一起做出很大努力,尽管这时还不能认为天堂与奇异的地下世界一样生动。而从道教观念的发展中可以看出——对于道教来说,“长生不老观”、“求仙”已成为其天堂观的核心。汉语中的“仙”一字,词义在开始与后来产生了非常有趣的发展,它表示两个完全不同的意义。据其语音来看,这个字和“升”相关,事实上与“升”字等同。“升”,“升到空中”,在书写上,二者之间惟一的不同,“仙”这个字后来意味着“长生者”,书写上仍可看出“人”的意思来,这在早期的文本中也得到了证实,于是也就意味着一个能够飞翔,意味着这个人有奇异的双翼,人们常常把他想像为全身披着羽毛,但最初他并未被赋予特别的智者的品质。只在公元前四世纪、公元前三世纪,人们第一次感到了彼岸世界的存在,彼岸世界作为一个独特的区域于一两个世纪之后再次失去其重要地位。只有“仙”,这些飞翔的永生者成了富有意义的关键性形象。例如:他们成为两个世界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