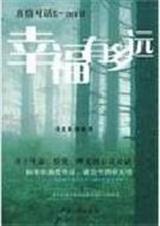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5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45
孙逸仙的综合法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1866…1925年),是理解1900—1930年这段时期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创建了一套乌托邦理论——更为精确的说法,是他如何将许多不同的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理论接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一套指导其坚强实践的理论。诚然,在他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理论曾经做出了不断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性的。他在秘密社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组织了推翻满洲统治的国家革命。因为自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不能得以执行,作为共和的第一位总统,他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即放弃了这个职位。在他将死之时,他又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和苏联。由于他的激进主张有渐进性和许多过渡阶段,直至今日,他仍然能被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当作共同的代言人。“三民主义”作为他的政治理念,现在已经被阐释为相互不同的许多形态。而他自己对“三民主义”的定义如下:
何谓三民主义?即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如满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义是也。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
346正如最后一句话所表明的,这是他死前对自己“三民主义”的又一次定义,而之前他对三民主义进行详细阐发的时间为1922年。但“三民主义”的最初缘起,可以追溯到革命早期的1911年。这样,我们也就毫不奇怪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翻译成西方文字时,何以有那么多不同的表述方式了。用“民族”、“民权”、“民生”是一种表达,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表达。1912年之后,孙中山被迫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中心,因此,他也就越发需要对他的政治理念进行更为精练的表述,使之更容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1918年,他出版了自己主要著作的第一部分《建国方略》,其中包含了他的“心理重建”。在这里,他抱怨大家将他的三民主义当作“一个乌托邦”。奇怪的是,他将这归因于人们“知易行难”的思想。而他所持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是“知难行易”。他认为,如果说行是艰难的话,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掌握恰当的知识。对新的、乌托邦式的思想逐渐习惯,才构成了真正的障碍,甚至“敌人有意地破坏精神”,也经常会使它不断更新。但一旦这个知识上的困难被克服以后,他的计划将随之而自动实现。
事实上,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试图阻止他的思想被当作乌托邦理念模型而传播。他认识到,要个体与社会同时获得幸福,必须要通过一条在绝对自由与绝对秩序之间的道路。它们二者(自由与秩序)其中任何一个通过破坏对方而产生优势,所得都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在1921年所作的一次演讲座中,他说道: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8)
几千年来的政治历史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学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中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了,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中国的政治,是从自由入于专制……当唐虞的时候,尧天舜日,极太平之圣治,人民享极太平等自由的安乐。而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从前(我国)人民在太平时代享有自由太多,不知道自由是怎么样宝贵,于是不知不觉的把自由放弃了。野心君主,便偷巧利用这机会,所以酿成秦、汉以后的专制。……中国古时有尧舜的好皇帝,政治修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向来是很自由的,老子说“无为而治”,也是表示当时人民享有极端自由的情况。当时中国人民,因为有了充分的自由,所以不知道自由的宝贵。普通外国人,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便以为中国人民不知道自由的好处,不讲究自由……近年以来,有许多青年学者,稍微得了一点新思想,知道了自由两个字,一说到政治上的改革,便以为要争自由。殊不知到中国人民,老早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需要去争的英译本内容与孙中山原文有些许出入。此处多引录相关原文。——译者注。
347当孙中山将民主视为他的三民主义中主要的元素,并相信他能够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到这种元素时,他已经决然地排除了所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对无政府主义和佛道思想既非完全正确,又非完全错误的认知,表明他认为这种思想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希望而已。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对于此则有不同,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初期,曾经很深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清晰且明确地试图协调三民主义中最后一条“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将所有的分歧归为方法上的不同。同时,民生主义还表现得与所有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而且,民生主义在所有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在他1924年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中,他对此问题有如下阐述:
348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现在国外是一样并称的;其中办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称的名词,都是社会主义。……今天我所讲的民生主义,究竟和社会主义有没有分别呢?……社会主义到底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呢?……但是从前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乌托邦派,只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至于怎样去消灭的具体方法,他们毫没有想到……到了马克思出世之后,使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透彻的研究,……从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里头便分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科学派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注物质的,要讲到物质,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产,没有过量的生产,自然不至有实业革命……近世的生产情形是怎样的呢?生产的东西,都是用工人和机器,由资本家与机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产。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斗争。照马克思的观察,阶级斗争,不是实业革命之后才有的,凡是过去的历史都是阶级战争史。古时有主人和奴隶的战争,有地主和农奴的战争,有贵族和平民的战争;简而言之,有种种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战争。到了社会革命完全成功,这两个互相战争的阶级才可以被一齐消灭。由此便可知马克思认定要有阶级战争,社会才有进化;阶级战争,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是以阶级战争为因,社会进化为果……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上社会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不能生存;因为人类不能生存,所以这种病症的结果,便起战争。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所有心得,只见得社会进化的毛病,没有见到社会进化的原理……我对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做了如此区分,是要说明,共产主义是民生的理想,而民生是共产主义的实践,它们之间没有区别——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它们的区别,在于实现的方法不同画线部分的英文,在孙中山《国父全书》中并没有找到直接对应。此处直接翻译自英文。关于“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孙中山的原文中有如下表述:“我们提倡民生主义二十多年,当初详细研究,反复思维,总是觉得用‘民生’这两个字来包括社会问题,较之用共产主义等名词更为适当,而且又切实明了,故采用这个名词。”(以上文字,见《国父全书》第256…264页)——译者注。
349尽管经过上述表述,共产主义和民生主义具有根本上的相同性,但这也不能掩盖孙中山自己发现的两者之间主要的不同,即是否承认阶级斗争。可以肯定的是,孙中山的气质已经先在地使他倾向于一种通过社会关系间渐进发展,逐渐达到理想目标的道路,借此废止阶级之间的所有暴力冲突。事实表明,只有到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他才逐渐认识到这种温和的革命思想,最终是虚弱的,并相信精神(民心)的改变是革命所不可缺少的。在192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这样讲道: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9)
向来本党势力多在海外,故吾党在海外有地盘,有同志,而在中国内地势力,甚为薄弱。……所以吾党想立于不败之地,今后奋斗的途径,必先要得民心,要国内人民与吾党同一个志愿,要使国内人民皆与吾党合作,同为革命而奋斗。……吾党所欠缺者,就是人民心力。革命行动,缺乏人民心力,无异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即以兵力打胜仗非真成功,以党员打胜仗,以主义征服,方是真成功。
只有到了几乎绝望的状态,孙中山才相信只有阶级斗争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革命。此时,他已经转向了共产主义一边。在他最后的一次宣言中,他将他的民生主义,定义为与共产党有着“共同的目标”。但同时,好像是为了对此做一平衡,他同时承认儒家的改革者如康有为等,也曾对这种思想进行鼓吹:
我们要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外国是有相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全中国人民都可以得安乐,都不致受财产分配不均的痛苦,要不受这种痛苦的意思,就是要共产。所以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不同。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照这样的说法,人民对于国家,不止是共产,甚么都是可以共的。人民对于国家要什么事都是可以共,才是真正达到民生主义的目的,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350孙中山在他生命最后一刻所作的,将中国20世纪20年代思想政治发展中产生的两种思潮——改革过的儒家思想与共产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尝试,通过简单地忽视两者的对抗性因素),无疑是有良好的初衷的。或许,这也是他作为“中国国父”,所应当采取的适合的政治主张:它应具有某种公平性,而非仅仅代表某一种政治力量。但是,他并不能修补中国年轻知识分子间存在的深刻不和。国民党(孙中山是它的创建者)的发展,是这种情形的象征。在1924…1926年之间,它试图与成立于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但在这个过程中,它的权力逐渐滑向朝共产主义方向发展的一些人手中。最终,在1927年春天,时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势力发起了暴力攻击,导致了数千国民党内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会主义者的死亡。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的控制权,国民党也逐渐向保守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并非源自20世纪初在中国发生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之争,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根据逻辑推演,随后的现象应当是其中的一部分人走向激进的右派,而另一部分人则走向激进的左派。更为中国化的追随者多在本土接受教育,他们所持观点相对分散,因为他们同样也不反对含有西方元素的现代化;而更为西化的追随者,其绝大多数都有在国外求学的经历,他们所持的激进主义,更显出一种内聚力。他们求学之地距中国越远,他们所持的观点就越有激进的色彩。那些相对温和的人物,曾经留学日本(至1906年,大约有1万人),而那些最为激进的人多为留欧,尤其是留学法国的学生(至1906年,约有600人)。他们对传统中国的批判观点,仿佛与他们在国外的环境并无完全的联系。满清政府幼稚地认为,将这些最为激进的学生送去欧洲留学,是摆脱他们的最好方法。
351
新无政府主义,与“机器达致大同”
当我们追溯中国20世纪关于人与社会的思想观念(这些观念已经部分地在孙中山的著作中得到表达)时,知识的线索将我们带到了“激进主义”,并且令人惊讶地将我们带回了欧洲,带回了巴黎。从1902年开始,一些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在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建立起了小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并随着一本名叫《新世纪》的杂志,于1907年浮出水面。直至1910年,这本杂志共出版了一百一十期。这些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包括一些经典和中国传统教育的思想,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基础的自由主义。吴稚晖(1864…1954年),现代中国思想史上颇具个人魅力色彩的学者,成为了这个组织的领袖。他曾在日本接受教育,并于1903年,因为在上海作记者时写的一篇具有煽动性的文章而被迫逃离中国。1904年,他在英国结识了孙中山。当时,孙中山正在几乎世界各地寻找反满和进行反满革命同道的支持。更多地基于友谊而非相同的理念,吴稚晖1905年成了同盟会(国民党前身)会员,并于1906年到达巴黎。在巴黎时期写作的一篇文章中,他仍然在歌颂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中文原文未能找到。此处文字从英文本翻译。——译者注: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10)
无政府之名在世界上是最有前途的……(携无政府之名)每个国家都能够超越自身的疆界……每个国家都可以放弃自己许多不同的语言,并接受一种普遍的语言;非政府的国家用其百分之七八十的力量,向大众传授无政府主义的新伦理。其结果是无政府主义成为一种必然。无政府主义将有它的伦理,而非法律。人们可以“各尽其能”,但那并非“义务”;可以“各取所需”,但那也并非“权利”。当每个人都能“自愿地进入真实与平等之地”,并再也不进入“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国家”时,那就是真正的无政府主义。
如果是孙中山,或许会说道家与佛家,以及一些人如鲍敬言、阮籍等,都曾经欣喜若狂地相信无政府主义会带来拯救。但与孙中山不同的是,吴稚晖所无限羡慕的一切,都来自欧洲。与他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同道们一样,他深深地爱上了法国这个国家,爱上了这个曾经有过大革命和巴黎公社,并仍然通过带贝雷帽等方式在几十年之后表达着对这段历史的热爱的国家(这种对法国钟情的传统,直至今日仍然在中国左派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