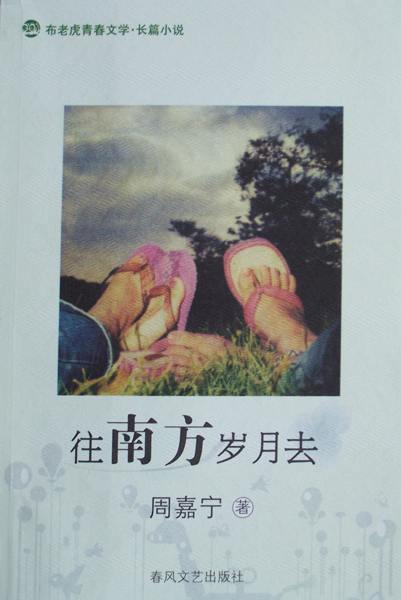岁月感怀:境由心造-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转学前,小小的我们就已经懂得友谊,并且意识到别时容易见时难,特意和另一位同学到城里的照相馆拍了张合影。可笑的是,想送班主任老师一张,居然让他自己拿了底片去洗。当年只有二十岁、刚从师范毕业的宋道韧老师将放大的照片给我们看时,大家都很高兴。
依依惜别,我和三明约定互相写信。小学五年级,自认为已有相当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信一通就是十几年,直到三明从部队转业。
1966年11月初,正值文革时期,三明到北京串联,住在通县的一所学校。人生地不熟,三明辗转找到我家,分别四年惊喜相见。我留三明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接着一同去学校看大字报,然后匆匆分手。那是革命年代,不能沉湎于小布尔乔雅的缠绵友情。
两年后,上山下乡浪潮席卷,三明去了安徽滁县,我去了陕西延安,都成了插队知青。1969年冬,我专程到滁县看望三明,一起去南京游览新建的长江大桥,相聚一天一夜,再叙友情。
又过两年,三明当兵入伍,我进入司法部门,在当时,这几乎是最好的归宿,我们由衷地为自己、也为对方庆幸。
转眼到了七十年代末,三明从部队转业,花样年华、美丽善良,被一位插队时认识的男生追了个死去活来。为了忠贞的爱情,三明放弃了回合肥的机会,来到小城滁州。
几乎同年,我和三明相继成家,过起了为人妻、为人母的琐碎日子。后来地址几经变更,从此更互无音讯。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除了工作,还要相夫教子。忙碌之间,也常想起儿时的伙伴。合肥那座城市我一直没有再回去过,也不知道三明和其他同学生活得怎样。
我保存的那张照片,虽被严加看管,但它从北京到延安,又从延安到西安,终于在一次搬家后不翼而飞,在我心中留下一份失落。
今年3月,突然接到一个会议通知,会址居然是合肥!立即给主办单位回执,那还有什么说的,去啊!就这样,在阔别45年之后,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古城合肥,回到我的梦中乐园安徽大学。
寻旧心情迫切。会议间隙,我从驻地皖能大厦赶到安大老校区,短短一段路,乘出租车只需9元,却让我盼得心焦。进入南门,一眼望见我们小时候常去玩的教学大楼,虽然落满沧桑,却是依旧巍然,“安徽大学”四个毛体大字潇洒遒劲。
三明的父亲也是安大建校初期的干部。我向一位老人打听(只有老人才知道老人),他遥指一片楼群,当年的老屋,已翻盖成新居。问了第二位老人,得知大概方位,第三位告诉我具体楼层,问到第四位时,只见她用手一指:那不是?你找的人来了。抬眼望去,一巍巍老者买菜归来,果真是老伯,当年形象依稀可辨。我忙自报家门,上前问好。老伯闻之,十分激动,拉我上楼,大呼阿姨倒茶。翻出三明的电话,终于听到久违的声音。得知是我,三明大喜过望。依旧是快人快语:“你住在哪里?等我安排一下,马上来看你。”
我和三明(2)
坐两个小时的汽车赶到合肥,当三明站在我面前时,好像时光倒流。觉得三明一点儿也没变,就像我们从来没有分开过!
眼前的三明,不施脂粉,职业套装;谈吐温和,举止优雅。目光还像小时候一样清澈,声音还像小时候一样亲切。岁月在我们脸上留下重重的痕迹,却没有在我们心中划开一丝裂纹。
轻轻拥抱一下,心中好暖。三明说:“我调了5天休假,加上周末,天天陪你!”“好啊,正好让我多看看这里。”
朋友就是朋友,不管分别多久!谈谈工作,叙叙家常,女人和女人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三明拿出当年那张合影,看到旧时模样,给我一个意外惊喜。如今的三明沉稳干练,在市科技局负责农业科技项目管理,工作卓有成效。我们从照片说到现实,从过去说到现在,会也不想去开了,考察也不参加了,我们要拥有自己的时间。
会议结束,代表们奔了黄山。我和三明整装出发,就像当年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一段一段地乘火车,换汽车。先到蚌埠,我在安徽生活过的另一个城市。
外祖父工作过的安徽商学院,现已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据说在当地招生十分火爆。学校建了新校区,旧址变为成人教育学院和宿舍区。当年住过的小楼已被拆成废墟,问及一位老人,居然记得当年任院长的外祖父,说那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离学校不及1公里,便是我国南北之界淮河,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地方。2006年建成的淮河大堤延展宽阔,堤内是花红柳绿的滨河公园,堤外是种了小麦的河滩。当年只有两条大马路的小城如今热闹繁华。
为了让我多看几个地方,三明把自助游安排得像80天环游地球一样紧凑。观赏了巢湖风光,领略了银屏山美景,逛龙川,游婺源,从江淮之间到长江以南;从山清水秀的皖南到郁郁葱葱的赣北,江南春色尽收眼底。一路上,三明车票、门票全包,对我更是照顾有加。
最让我高兴的是,三明还联系到七、八位小学同学和一位班主任老师。还有从深圳赶回来的“同桌的你”,当年的小淘气俨然变为成功的企业家。虽然四十多年未见,但同学都是安大子弟,父母多为同事,诸多人、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很快热聊起来,相约待到老师七十大寿时再聚会!
一周匆匆,分手时,三明把那张合影送给了我。她说:“我已经把它保存了四十五年,现在送给你,由你来继续保存。”
友谊是人类文明的需要。一个朋友代表着一段经历的见证。一生中能结交三明这样的朋友,我真的好幸运。
我为什么下乡(1)
前些日子,为了响应某个知青网站的征文,我开始反思当年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
然而,三十八年前经历的事情,已经和逝去的时光黏连在了一起,如果一定要回忆,就得像外科医生一样,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将它一点一点、小心地从无痕的岁月中剥离出来。
以当代人的眼光审视发生在上个世纪后半叶的上山下乡事件,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一场灾难,一次浩劫;它使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生活屋顶突然坍塌,使一代人的一部分神圣权利永远被剥夺,生命轨迹被无情改变。
但是,细想起来,当年我竟是自愿下乡的。那年冬天,西去列车启动的瞬间,我甚至感到一种如愿以偿的心悸。后来我不止一次地回忆,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使我毫不犹豫地一次次地报名,急于把自己从北京发送出去呢?
答案有点犯傻——我想离开家。
在我年满十四岁以后,度过了独立意识渐渐凸显的青春断乳期,虽然没有学到什么文化,却有了某些“想法”,具体地说,就是滋生出一种对自由意志的最简单的追求。这种追求随着年龄的增长日益膨胀,它的终极目标被我锁定为离家出走。
我渴望离开的那个家,其实是个很好的家。这个普通的、多子女的知识家庭,对一个当时正在成长的少年来说,该有的似乎都有:可以吃饱的一日三餐,补丁不太多的四季衣衫,不必发愁的学杂费,甚至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它温暖得像夏日午后令人昏昏欲睡的沉闷气息,没有任何的新鲜与刺激。也许是出于爱护,父母为我们制定了许多不成文的纪律,诸如放学按时回家、天冷要穿棉袄、不能躺着看书、吃饭不说话、别睡懒觉等好孩子天经地义应遵守的规矩。而我却与我亲爱的父母的意志背道而驰。这些纪律,在一个不安分的少年看来,无疑是一种束缚,它使我精心孕育的某些美妙计划——周六通宵达旦地读一本小说,周日昏天黑地地睡一天觉,偶尔到好朋友那里“刷”一天夜等等,不断地遭遇流产。
也曾经尝试过逃走,通常是在我和父母发生冲突之后。但身无分文、走投无路的窘况,使我不得不以无比沮丧的心情重归暖巢,继续实践那些亲切而坚固的家庭纪律。
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离开家庭、独立生活的契机。这个契机终于在公元1968年12月以政治面目出现在我面前。上山下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与一个城市少年的想入非非相吻合,这恐怕是它的企划者们决不曾料到的。而在当年,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以我短浅的目光看来,它几乎是一个完美的机会!在我最想脱离家庭约束的时候,这个机会汹涌而至,令我眼前一亮。
由于性格所致,我从小具有多动倾向,运动状态——行走或者晃动,可以使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快感;我对以行走为载体的故事,如唐三藏西天取经、八十天环游地球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等充满热情,并由此而热爱旅行,乃至热爱从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到飞机等一切交通工具,渴望经常处于一种运动状态中。这种渴望深至骨髓,以至于在我几十年的梦境里,反复出现飞来飞去的景象。
下乡使我获得了一个合法的长途旅行的机会,并实现独立生活的梦想,这对于我来说简直是求之不得。在等待出发的日子里,我怀着带有悬念的、新奇的、甚至有点迫不及待的兴奋,在母亲忧郁的目光中心安理得地为自己打点行装,一种长大成人、即将远走天涯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尽管我后来才知道,这次旅行充满艰险且代价惨重。虽然和那些对家庭充满依恋、死活不想下乡的同学相比,我的适应能力在农村迅速得到开发,但我还是遭到了报应——这种与亲人长期的“生离”,一直延续到我终于无法忍受的地步。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和我相类似的情况。“离家出走”在当时还是一个生僻的词,几十年以后我才感悟到,尽管生活背景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不同时代的人类在相同年龄阶段有着惊人相似的个体觉醒,现在的孩子更加渴望独立和自由,更善于制造一个又一个不同凡响的出走事件。
我为什么下乡(2)
当然,下乡的动机其实是多元的,在我那个年龄,不可能不被打上时代的印痕。但我相信它的核心是对挣脱父母羽翼、争取独立自由的渴望,因此,我对“出门”的方式不加选择——本来我就是那种顾前不顾后、只看眼前不计后果的人。还有一个在当时不便示人的原因:由于父亲“出了问题”,本已被部队接兵干部看中的我惨遭淘汰,出于少年人的虚荣,我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不得不把对绿色军营的向往,转向了更加广阔的绿色原野。
我从小胸无大志,成年以后,给自己定的最高标准是做一个有品味的散淡闲人。而在现实生活中,则既无品位,也不得闲,只剩下一个“散”字。确切地说,它是一种经历过泥土尘染的散漫。
三十八年前的上山下乡,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剧烈的一次突变,少年时代追求的那种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尽管乡下的生活远非我所想象,我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真正的自由。它带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绝不是一篇文章所能说清的,但乡下的日子打磨了我的筋骨,乡下的生活激活了我的思维,乡下的事开阔了我的眼界,乡下的人教会了我如何面对逆境。乡下使我了解到都市以外人群的生存状态,也敦促我多少改掉了一些娇气与矫情,虚伪与做作,怨气与浮躁,使自己更接近于一个纯粹的人。
这就是我所能够想得起来的我到底为什么下乡的主要原由。
西行的冬天(1)
我是在一个冬天踏上西去旅途的,从此开创了我独立的人生道路。
那一年的冬天非常冷。
当我提着简单的随身用品走出家门时,心情有些异样,因为这是一次和往常离家不一样的出门——尽管未满十七岁的我,由于从小喜欢旅行,从家里出发的事情已经经历过多次,包括和大人不打招呼大义凛然的离家出走。
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宗行李早已托运到车站,一只杂木箱子和一个行李卷——我下乡落户的全部家当。同行的是几千名年纪相仿的少年,启程仪式极为隆重地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广场冷峻而空旷。集合在可容纳上百万人的广场上,越发显得我们渺小。那天究竟在那里进行了什么仪式早就忘记了,记忆里只剩下刻骨铭心的寒冷。
仪式结束后出发,北京站人山人海,无数送行者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按规定,每名知青只能有一位亲属进站送行,送我的是母亲。当我在人流中看见医生出身、从不当人落泪的母亲竟然红肿了眼睛,就没敢再看她一眼。
车轮被蒸汽车头拉动的瞬间,车厢里、站台上原先还是沉闷的呜咽突然如同山洪爆发般响成一片,那惊天动地的哭喊声,盖过了火车的轰鸣。
那一刻我离开了窗口,怕看见站台上哭泣的人群,特别是怕看见母亲忧郁伤心的目光。
我居然没有落一滴眼泪。这是一个我记忆深刻的细节。一位送行的老师露出无比惊讶的表情,他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我这样一个看上去娇小柔弱的女孩,在被发配远乡的时候,怎会如此坚强?其实,沉默也是一种表达。在当兵不成、留北京无望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下乡,是我唯一的出路,因为我知道,父亲正在难中,如果我不走,母亲将会被造反派搅得无一宁日。
就这样带着对未来的一无所知上路了,迷惘中,竟然隐约着一种渴望和憧憬。
不知道要去的地方究竟有多远,只有地图上的概念——那里被称作革命圣地。
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上边的号召是“扎根农村一辈子”。
然而,毕竟是一群不知愁滋味的少年,随着车轮的飞转,车厢里热闹起来,笑容重新回到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上。
火车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疾驰了一个昼夜,当新的黎明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了黄土高原。路还在铁轨下延伸,窗外景致已是别有洞天。车到西安,站台上挤满敲锣打鼓但显然是例行公事的欢迎人群,大家也是一副公事公办的回应。
从西安出发继续西行,几小时后,我们到达西北煤城铜川。
按行程,似乎应该在铜川住一夜,但实在想不起来那一夜究竟歇在哪了,记忆的引擎可以搜索到这一路经历的无数细节,唯独在这里留下一个空洞。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坐蓬了帆布的大货车,奔赴延安。刚下过雪,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多度,厚厚的积雪被冻得硬邦邦的,为了防止打滑,车轮上绑着铁链。据说由于下雪,两次推迟了起程日期,但为了让我们到延安过一个“革命化春节”,不得不采取绑防滑链的办法能使我们及时出发,这就增添了这次西行的风险和悬念。
浩浩荡荡的车队逶迤千米,沿着盘山公路攀缘缓行,场面很是壮观。
我们几十个人挤在一辆车上,车一开动,冷风便从帆布蓬子的缝隙钻进来,过金锁关时,塞外的严寒更是令人难以忍受,风刮在脸上,刺骨般疼痛。冻得难忍,大家便在车厢里跺脚,凉气从脚趾向上蔓延,膝盖以下都是僵硬的,同伴们纷纷喊冷,我却又一次保持了沉默,我感觉我可能要被冻死了,是因怕喊冷而耗尽最后一点热量。渐渐地,脸被冻得麻木,寒风在早已没有知觉的皮肤上肆虐,终于不再感到疼痛。
经过一天的颠簸,我们到了延安县城,当晚宿在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