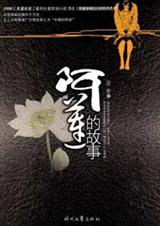潘金莲的发型-第18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受到了老百姓自发的尊重和爱戴,所以才能够从卖冰雪的商家那里一筐筐地白拿。这就说明,当时经营冰雪生意的商家完全是民间背景,另外,即使是官宦人家,在需要用冰的时候,也是直接到市场上买,在特殊情况下,甚至宫廷也会向民间买冰。
不过,从诗文记载来看,冰雪成为商品,成为商业买卖中的一个行当,主要是在长安、洛阳两京出现的特殊现象。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一诗中极力述说长安是生活昂贵奢侈之地(“长安玉桂国”),其中提到的一条证据就是:“开贯泻蚨母,买冰防夏蝇。”——人们在夏天可以大把花钱在买冰防暑上。这样的描写说明,民间经营冰雪买卖,似乎是京城生活的特色,在其他地方并不普遍。另外,即使在京城,民间冰窖的藏冰能力也是有限的,如《云仙杂记》的记载所说,“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璧”。也因此,唐代诗文中提到夏日用冰,多是说“赐冰”,冰雪终究还是“非常之物”。即使上层社会用冰的主要渠道,也还是来自皇家冰窖的赏赐,因此贵族高官们在夏天还能常靠“赐冰”来解决问题,而下层官员、老百姓赐冰得不到,买冰又太贵,对他们来说,冰仍然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所谓“实大王樽俎之常品,非小民造次之所致”(韦应物《冰赋》)。而杜甫在老病苦热之中,除了感叹“敢望宫恩玉井冰”之外,就没什么其他办法了。
这一情况到宋代有了惊人的变化。在两宋的京城中,民间的冰雪经营业极其发达普遍,夏天市面上卖冰雪,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东京梦华录》中记六月“巷陌杂卖”,说是:“是月时物,巷陌路口,桥门市井皆卖……冰雪凉水……”冰雪被放在水饭、水鹅梨、金杏、红菱等食物水果之列中,当作“时物”、“杂卖”之一种,街头巷尾随处都有出售,那么,当时民间窖藏的数量一定非常之大,以致冰雪成了很普通的东西,既不稀奇,也不珍贵。当时不仅有多家“藏冰之家”,而且其中更有靠专营冰雪而出了名发了财的,如《东京梦华录》同条接着便说:“冰雪惟旧宋门外两家最盛,悉用银器。”揣其语意,汴梁经营冰雪的显然不止这两家,但以旧宋门外这两家规模最大,他们的实力雄厚到了什么程度呢?——盛卖冰雪的家伙全是银器!
既然藏冰、卖冰的规模很大,宋代市民连同上层社会使用起冰雪来也就大手大脚,不必精打细算。夏天市面上的各种消暑食物、饮料往往是用冰雪冷镇的,或者干脆用冰雪制作。如六月“巷陌杂卖”中就有一种“冰雪细料餶饳儿”,此外还有“冰雪冷元子”,冷饮则有“绿豆、甘草冰雪凉水”(《东京梦华录》“州桥夜市”)、“雪泡豆儿水”(《梦粱录》“夜市”)、“雪泡缩皮饮”(《武林旧事》),茶肆“暑天添卖雪泡梅花酒”(《梦粱录》“茶肆”)。最有意思的是,有钱人家还要“散暑药冰水”(《西湖老人繁胜录》),作为一种慈善行为,无偿向路人提供解暑药和冰水。《东京梦华录》中记载顾客在食店中点饭菜的情形是:“都人侈纵,百端唤索,或热或冷,或温或整,或绝冷、精浇、膘浇之类,人人索唤不同。”《梦粱录》中有一段关于杭州“面食店”中“杭人侈甚”的文字,与《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述差不多,也是说顾客可以随时点“冷”或“绝冷”的面食和下饭之菜。如果没有大量的民间藏冰,“绝冷”的食物显然很难在民营饭店中做出来。这样的情况,与唐诗中表现出的情形,有着天壤之别,显然,冰雪在宋代早不是什么“非常之物”了。
近年来,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特别是一些国外的汉学家,往往强调在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经历了很大的变化,冰块由特权标志到普通商品的身份转换,或许可以作为这一说法的一个小小的注脚。不过,需要一提的是,在宋代,虽然民间藏冰已经随处皆有,而且价格便宜,但是,如在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皇帝颁冰的仪典还是被继续执行着,并且相关制度制定得更细,规模也更大了。那一时代的臣民们也还是以使用“赐冰”为殊荣,如宋词中一提到夏天用的冰,往往说是“赐冰”。这当然是人们的观念意识在顽强地起着作用。都是冰块,但是一说是“赐冰”,那冰块本身,以及使用冰块的人,身份地位似乎就陡然地升了一个档次。
不过,冰块的这一特殊身份并没有一直维持下来。在宋以后的年代里,民间冰雪经营业始终活跃,并持续发展,在明清时代,夏天使用冰雪,在大中城市都是很普遍的事情(王仁湘:《古代冰井与冰厨》)。这似乎造成了冰块的地位在政治生活中、在国家制度中无可挽回的衰落。关于明清皇帝赏赐臣下冰块的记录似乎很鲜见,《红楼梦》中,宫中不断往荣宁二府上送来各种象征多于实用意义的赏赐品,但不见有冰。这也难怪,像西门庆这样开生药铺的商人家里,一到夏天都可以“冰盆内浮瓜沉李”,享受“冰盘”里冷镇出来的酸梅汤,冰块也实在没有什么神秘感了,赐一块冰,又怎么能让臣民增加对“天家”的畏惧和景仰?所以,皇家就得另寻花样来作为操练君臣关系的手段,于是,一匣宫花、一碗蒸酥酪都显得比冰块更适合作为赏赐的物品,毕竟,这些东西是“内造”的,宫外没有,于是就更容易化身成“天恩”的雨露。
第36节 梅花络(1)
八年前,我从巴黎乘长途汽车跑到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看望在那里留学的一位旧日同窗。一个晚上,这位朋友出去打工,留下我一个人在她空旷的北欧老房子中独自发闷。无意中,我发现了一本台湾出版的教人打中国结的小书,鬼差神使地,竟然拿起绳子学习起来,折腾了一个晚上,才打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结,而且歪歪扭扭,极其难看。不过,朋友下工回来,看到我的成绩,却着实惊诧了一番,因为我一向是公认的手笨,她万想不到我居然也能把一根绳子绕来穿去,打成一个中国结,觉得我远比她想象的聪明,当下把我着实地夸了一顿。
这是我为数甚少的修习“女红”的经验之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动过学打中国结的念头。不过,这几年来,用中国结制成的各种小饰物渐渐风行,我每次看到柜台上琳琅满目的中国结饰物,就会不期然地想起自己在遥远的异国用学打中国结排遣乡愁的那一个晚上。这多少有点像《小王子》中的小狐狸,狐狸一看到麦浪就会想起小王子的金色头发,我一看到中国结,就会想到遥远安静的小城安特卫普。
这样对中国结留了意,我才渐渐注意到,在古代女性的生活中,中国结曾经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女红。《红楼梦》里就大约有四次提到打中国结,如第二十四回中提到,“袭人因被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第三十二回,却是袭人求湘云“打十根蝴蝶结子”——当然是为了宝玉;第六十四回,也是写袭人为了给宝玉做一个新扇套,“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呢”。第三十五回中“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更是用浓郁的笔墨描写莺儿利用打中国结的方法打“绦子”和“络子”。据莺儿讲,她打的花样有“一炷香,朝天镫,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其中,如方胜、连环、梅花等,至今也还是打中国结时常常要用到的基本样式。从《红楼梦》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物品要靠女性用打中国结的方法进行装饰,仅书中提到的就有“扇子、香坠儿、汗巾子”、扇套,还有装东西用的“络子”,即线结的小袋子。
其实,中国结在古代生活中的用途非常广泛,远不止《红楼梦》中提到的这些情况。既然上古曾经“结绳记事”,中国结的起源想必是可以追溯到极古远的年代的,这里且不去提它。根据我个人的印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中国结大概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细节形象之一。
比如,人物形象的服饰上就往往会出现中国结。这是因为,一直到明中叶以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才在服饰上普遍使用纽扣,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主要是靠长长的衣带来系束衣服。在把衣带两端连系到一起时,自然要打个结,于是在衣带上打中国结就成了每个人天天必修的功课。所以,在古代生活中,最离不开中国结的地方,首先就是古人的衣带。不过,衣带上打出的花结总以简便为主,要打得简单,能很容易地解开,从古代艺术中就可以看到,出现在人们服饰上的衣结的样式都是比较简单的。顺便说一句,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相似,日本传统服装至今也还是靠衣带来系束,不用纽扣,因此如何把和服的腰带打成结,仍然还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见武内元代《实用系结大全》“和服”篇,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至于中国,到了《金瓶梅》的时代,用纽扣来代替衣带的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而明清时代的纽扣,除了金属、玉、象牙等材料之外,大量都是布纽扣,这些布纽扣也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的,所使用的打结方法可谓花样百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活。
在艺术表现中,中国结被派在各种各样的用途上,范围非常宽泛,很难归类。例如,从春秋时代起,把一块块玉佩、一条条珠串用绦带穿起来,形成长长的佩饰,挂在腰带上,是贵族们炫耀自己身份、财富的重要手段。在信阳、江陵等地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上,就用彩绘表现了这种华丽的长佩,从彩绘上可以清楚看出,人们在用绦带穿系珠玉时,会用绦带打出一个个样式不同的中国结,作为装饰。又如,在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相传为阎立本作品的《步辇图》中,伞盖、旌旗等的装饰飘带上都系有中国结,以形成美观的效果。
比较特别的是,在传为唐人作品的几幅名画《挥扇仕女图》、《宫乐图》、《调琴啜茗图》中,都一致地表现了使用中国结的一种特殊方式。椅子、凳子是在唐代渐渐流行起来的坐具,出现在这几卷绘画中的椅凳上,都在座框上相隔有间地安有几个小环,每个小环中有一条长长的绳带穿过,绳带两端垂下,在中间打出一个中国结。这种打有中国结的垂带固然起着装饰的作用,不过,推测起来,这些椅子大多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些垂带大概还有类似提手的作用,当人们想要搬动椅子、凳子的时候,用手提起这些垂带就可以了,比直接去抬坐具本身会省力些。
在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的《货郎图》(沈从文先生考为元人作品,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页352)中,货郎担上挂满琳琅满目的各样玩意儿,很多都系有打着精巧中国结的飘带,反映出宋元时代商品的发达,工艺的发达,物质生活的发达。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砖刻上的宋代女性,在喇叭裤的外侧开衩上,缀了一连串的中国结做装饰。
从以上随便所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结在古代艺术中是频繁出现的角色,但是也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之一。因为它总是作为服饰、器物上的小小装饰,出现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很难引起人的注意,永远不可能唱主角。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中国结被艺术家在不经意间如此频繁地取入创作之中,即使在传世珍品如《洛神赋图》中,也活跃着它的身影,这正说明它作为古代生活中一项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重要技艺手段,让艺术家们根本无法回避。中国结在艺术表现中的命运,多少反映了女性的一切创造活动的命运,反映了女性生活,以及女性自身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重要,如此不可否认,却永远只能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第37节 梅花络(2)
因为中国结的用处大,所以,打中国结就成了古代妇女的一项重要女红。为了鼓励女性用心研习这一技艺,在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与打中国结密切相关的某些特定风俗,随着这些风俗的形成,这一技艺拥有了自己的专门节日,这就是端午节。
根据《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等书的记载,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端午节的风俗中就有了特定的一项内容,妇女们要在节前用五彩的丝线编结出许多“长命缕”,在节日那一天分赠家人亲友,让大家系在手臂上,据说是能辟邪、不生病。长命缕也叫续命缕、辟兵缯、五色丝、长索、朱索、百索、宛转绳等,名称很多。唐代无名氏所做的《五丝续宝命赋》中描写妇女亲手制作长命缕的情形,是“对回鸾之十字”、“盘续命之五丝”,这显然正是打中国结的基本动作;描写所盘成的花样的形状,则是“宛委虬盘”,这也正是中国结的形式特点。另外,唐人权德舆有《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诗,诗中有“千年彩缕同心丽”之句,而在诗题中把长命缕直呼为“彩结”,更在诗中提到这长命缕采用了古时最流行的一种结式——同心结。
从这些记载来看,古代端午节的长命缕正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成的。妇女们做长命缕时,不仅仅要打出一些基本的花结,如同心结,而且还要“结为人像”(《酉阳杂俎》)或“日月星辰鸟兽之状”(《荆楚岁时记》),总之,要在基本的结式基础上打出许多复杂的花样。宋人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三)引述同朝人姜廉《花月新闻》中的传说,讲一位女“剑仙”与普通男子结了亲,“值端午节,一夕制彩丝百副,尽饷党族”,这位来历神秘的女士一夜间就制作出了上百副彩丝,遍赠夫家亲戚,所制的彩丝“其人物、花草、字画点缀,历历可数”,这当然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反映出长命缕以能打出各种精巧花样为胜的特点。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妇女们在端午节前要打的长命缕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打许多条,家人、亲友都要送到。故事中,女剑仙在制彩丝一项上表现出的心灵手巧,立刻得到了夫族亲戚的交口赞誉,“自是皆以仙妇呼之”。可见,端午节做长命缕,实际上是妇女们赛巧、斗巧的一次机会,也让全社会共同来检验各位女性打中国结的水平。因此,这一特定的节日风俗,在表面上的迷信色彩之下,其实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一年一次地集中检验妇女打中国结的技艺以及创新的本领,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说,是“以示妇人计功也”。不过,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得很早,在唐代,市面上就已经有现成的长命缕作为商品出售了,女性可以到市场上买现成物回来,不一定非得自己亲手做(见《太平广记 》“神部”“赵州参军条”),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就更为普遍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端午节的长命缕主要是缠带在人们的手臂上,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中描写宫女在端午节带长命缕的情形是:“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正如今天青少年中流行带在手腕上的绳编幸运手链一样。如今,在用中国结做手链、项链时,常会穿些珠子之类的小饰品做点缀,古人制长命缕时也是这样。《西京杂记》就提到,汉宣帝幼时,他的母亲史良娣曾经制作五彩宛转绳,端午节时系在他的手臂上,绳上特意穿系了一枚小小的身毒国宝镜,用以辟邪。到了宋代,宫廷在端午节时有珍珠百索(《武林旧事》),显然是在百索上穿饰珍珠。另外,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