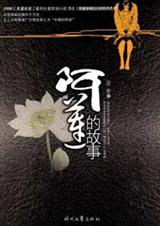潘金莲的发型-第2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似乎,从宋代以来,人们喜欢把玻璃制品中质量上乘者称“玻璃”,而水平比较一般的制品则呼作“琉璃”。无论如何,“琉璃”仍然是这一漫长时期内占主流的称呼,是玻璃类制品的通称。
唐宋以来的琉璃制品,始终存在着本土琉璃与外来琉璃的两大分野。外来琉璃的重要进口国,从昔日的东罗马、波斯,逐步变成为伊斯兰文化的阿拉伯“大食”帝国。本土琉璃虽然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得到某种普及,并且有一定的技术创新,但是,在质量上却始终无法与实力强大的西亚地区相抗衡。程大昌《演繁录》中对此说得十分清楚:“中国所铸琉璃,有与西域异者。铸之中国,则色甚光鲜,而质甚清脆,沃以热酒,随手破裂。至其来自海舶者,制差朴钝,而色亦微暗,可异者,虽百沸汤注之,与磁银无异,了不损动,是名蕃琉璃也。”本土生产的琉璃器,始终没有能够在质量上过关,坚牢程度不够,尤其是耐热性太差,因此无法与国外琉璃竞争。进口琉璃器,也就长期成为中国上流社会所宝爱的一种奢侈品。
中外玻璃交流史上的又一大变化始于明朝中叶。这一变化,是与世界历史的格局变革相联系的。欧洲人海上霸权的建立,及其对东方航线的开辟,使得中国有了新的贸易对象。从16世纪起,欧洲的产品,包括其所生产的玻璃器,就开始进入中国,并成为富贵人家的奢侈品。明人张燮所著《东西洋考》卷六“红毛番”,就明确记载了欧洲人挺进东方的急先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南洋的活动:“红毛番,自称和(荷)兰国……”文后罗列了荷兰人的主要贸易种类,其中就有“玻璃”、天鹅绒等。
荷兰人带来的“玻璃”,与中国人以前所见到的“蕃琉璃”,有着很大的不同。15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最终覆亡,促使西亚地区的一部分工匠逃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他们把古老的玻璃制造传统也一同携去,玻璃业首先在威尼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随后,又被威尼斯匠人推广到欧洲各地。明代人所看到的,正是经欧洲人发展、革新了的玻璃制品,这些质量优良的玻璃新品种,立刻引起了中国人很大的兴趣。很明显的是,新颖的欧洲玻璃,被冠以了“玻璃”这一称呼,而“琉璃”,则主要局限于指称传统工艺制作的土产玻璃制品。6这一现象在入清以后越来越明显,康熙三十四年设立由欧洲传教士负责的玻璃作坊,直接引进欧洲玻璃生产技术为宫廷服务,这一设置便被称为“玻璃厂”。从最近整理出版的《养心殿造办处史料辑览(第一辑)•;雍正朝》(下简称“辑览”)7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当时的宫廷,对于进口的或者由玻璃厂以欧洲技术生产的玻璃器,都一律称为“玻璃”。《故宫博物院刊》2003年第一期所刊《清朝的玻璃制造与耶稣会士在蚕池口的作坊》一文提到,乾隆时期负责玻璃厂的法国教士汤执中编写有《法汉词典》,今天译为“玻璃”的glass,在该词典中却被对译为“琉璃”;crystal一词,才被译为“玻璃”。而crystal一词在英、法文中都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天然水晶;其次,是指欧洲玻璃业所发明的一种高质量的透明玻璃,以其澄澈度、坚硬度都近似天然水晶,而被冠以crystal一名,在今天的汉语中译作“水晶玻璃”或“晶质玻璃”。crystal——“水晶玻璃”,是欧洲玻璃业非常重要的一项成就,是其代表性的品种。法国教士所编《法汉词典》显示,清代人是把高质量的欧洲水晶玻璃称为“玻璃”,而把本土常见的旧玻璃品种称为“琉璃”的。并且,在汤执中编写的《字母顺序常用词汇目录》中,保留了完全同样的信息。
《红楼梦》中对于“玻璃”的反映,正是在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方面,书中的描写,印证了史料文献中所记录的情况,说明在清代的上层贵族社会中,“玻璃”的称呼已经非常流行,而“玻璃”制品虽然尚属珍贵,但也不是极其罕见之物。另一方面,根据文献的记录,也可以判定,《红楼梦》中所说的“玻璃”,乃是从欧洲进口的玻璃,或是在中国本土根据欧洲技术仿制的玻璃。
在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膻》中,宝玉“一面忙起来揭起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一夜的雪,下的将有一尺厚,天上仍是搓绵扯絮一般”,说明怡红院宝玉住室安装有玻璃窗。“辑览”中同样收有皇家建筑安装玻璃窗的记录,如雍正元年“木作”记录雍正传旨在养心殿安窗玻璃,雍正五年“玉作”一节中也详细记载了圆明园万字房对瀑布仙楼内一面玻璃窗户的安装过程,正可与《红楼梦》的描写互相对照。按照汤执中《法汉词典》等资料所给的定义,这些用来安装在窗户上的玻璃,就是欧洲发明的“水晶玻璃”(crystal),其实,实际上也只能是这一类产品。水晶玻璃的特点是无色透明,毫无杂质,透光性能极好,反光性能也极佳,并且沉重坚实,不易破碎,这些优点,都是土产琉璃所远远不能比的。
更重要的是,欧洲可以生产出平整、光滑的大片平板水晶玻璃,这就更为国产琉璃技术所无法望其项背。也正是由于这种平板透明玻璃的发明,才使得在窗户上安装窗玻璃成为可能。“辑览”中,雍正九年“五月廿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奏事太监王常贵交……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系广东粤海监督督察御史祖秉圭进”,可见,皇家、大贵族家中所用的成片平板透明玻璃,要在广东等地从洋商那里进货。这样娇脆的东西千里迢迢运到北京,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之下,也真是不容易。越珍贵的东西越会成为时尚,这一种情形也毫无例外地发生在了欧洲透明玻璃片上。结合《红楼梦》与“辑览”,可以看出,用成片的平板玻璃衬摆锡玻璃而成的玻璃镜,在当时就是很显档次的陈设,雍正本人就很有兴致地一再吩咐如何在家具上、居室中安装玻璃镜。8另外,把外来物品与本土生活习俗相结合的一项新时髦,是用这些大玻璃片做成玻璃屏风9。玻璃灯,在圆明园和贾府中,也一样都是很华贵的陈设。除了透明无色的水晶玻璃之外,欧洲彩色玻璃制品也同样受到明清上层社会的欢迎。在清代,主要是通过传教士掌握的御用玻璃厂,在本土仿制欧洲彩色玻璃器获得了一定的成功。据汤执中编写的《字母顺序常用词汇目录》,至晚在乾隆时代,中国也生产出了相当有水平的水晶玻璃。10
随着中国社会逐步向西方世界开放,欧洲的玻璃制品以及相关的现代技术都被引入并得到普及,我们今天日常所用的各种玻璃器物,都是出于欧洲近代玻璃生产体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一过程中,“琉璃”一词又被国人逐渐遗忘,“玻璃”成为我们对于这样一类人工制品的日常、通行称呼。“随侯珠”、“五色玉”,与“琉璃”、“玻璃”的更迭、替代,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玻璃史上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而每一个阶段,都对应于外来文化和技术的一次冲击波,都像晴雨表一样,反映了世界文明景观中的变化、人类文明与技术的进步。
附:琉璃的奢侈
在魏晋士大夫中,王济(武子)是一个非常闪光的性格人物,至少他的同时代人是这么认为的。史料中记录他的事迹若干,件件都很有个性,给人深刻印象。他的特点之一是特别有钱,也特别奢侈。有一次,堂堂的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结果这位臣子家中生活作风之奢靡,让晋武帝有点受刺激,一顿饭没吃完就走人了。刺激之一是,“武子供馔,并用琉璃器”,这被收录在《世说新语》的“奢汰篇”里,作为挥霍无度的一例突出表现。此事也见于《晋书》“王济传”,说是“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
无独有偶,时代更晚的《洛阳伽蓝记》中,“开善寺”一节谈到河间王元琛的奢侈:“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自余酒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不仅说琉璃碗与水晶、玛瑙器皿一样属于“宝器”,而且还特别指明,是“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
在汉代通西域之后,各种异国产品经丝绸之路纷至而来,其中,就有东罗马、波斯生产的玻璃器,当时叫做“琉璃”。近年在考古发掘中,从北朝墓出土有那一时代的东罗马、波斯玻璃器实物,质地均为透明玻璃,当然,因为原料中含有杂质,这些透明玻璃器都微带青色,还远不能像今天的水晶玻璃那样毫无杂色、彻映无碍。但是,对汉晋人来说,这种像水一样清亮、像冰一样晶莹的制品,绝对是前所未见的神奇玩意儿。晋人潘尼的《琉璃碗赋》,就夸赞此等“济流沙之绝险,越葱岭之峻危”、万里远来的玻璃盛器是“凝霜不足方其洁,澄水不能喻其清”。另外,外来琉璃器还拥有着异域风格的造型,晋人傅咸在谈到自家的一件琉璃卮时,就提到是“逞异域之殊形”。1989年新疆出土一件隋代单足玻璃杯,杯身上采用萨珊玻璃器的典型装饰手法,无论从造型到纹饰都呈现出异域的特色,风貌与之非常接近的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一件配金属座的玻璃杯,可说是实际印证了傅咸所珍视的“琉璃卮”——玻璃酒杯的“异域之殊形”。现藏美国波士顿博物馆、相传为北齐杨子华作品的《北齐校书图》,非常准确地描绘了南北朝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散发裸身之饮”的士大夫们所用的酒杯,恰恰是无把手,下有单足,造型很接近新疆出土隋代单足玻璃杯及正仓院藏玻璃杯,也许,这里恰恰具体地、形象地表现了南北朝贵族在生活中使用进口酒杯(玻璃或金银质地)的情形。由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想象,王济家、元琛家开出的席面是什么排场——精美的肴馔都盛在异国造型的透明盘碗里,更显得色状诱人。
从文献记载和出土实物的状况都看得出,在当时的贵族阶层中,有一件两件琉璃器并不难,难的是场面上清一色的全部使用琉璃器。异国玻璃产品经过遥远漫长的贸易路线到达中国,价格会变得十分昂贵,所以,王济家一下摆出那么多琉璃器,就难怪晋武帝会觉得不舒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说一个人请客“并用琉璃器”,大概就像上个世纪80年代说谁家“家里都是日本电器”,或者像今天说谁家“一屋子都是意大利进口名牌家具”一样,是非常显示实力的一件事。
有一点也许值得注意的是,在形容王济的奢侈时,《世说》仅仅简单地说“并用琉璃器”,这固然是贯彻了其一向的明洁语风,但是,恐怕也与一个事实有关,即,在那个时代,琉璃器毫无例外地都是昂贵的进口货。所以,不用多说,只要这么点一下,大家就都能会意。但是,到了杨衒之的时代,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外国产品的仿制早已开始,包括一些异域的生产技术都通过各种途径传了进来。琉璃的生产技术就在南北朝早期首先传入北方地区,直接造成了在北朝琉璃制品的价格暴跌(见《北史•;西戎传》)。所以,杨衒之在形容元琛的奢侈时,就不得不多费点唇舌,说他的琉璃碗、水晶钵等等,是“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本地开发的仿制品,与这些原产高档货没法比。这正像今天国产家电、汽车成了寻常消费之后,要说明一个人有档次,就必须得指出,他用的是进家彩电、进口汽车,在这方面,古今的道理倒是一样的。
第四部分 鉴赏
第41节 想念梦幻的桂旗(1)
一
我是从《洛神赋图》知道《洛神赋》的。在我的印象中,《洛神赋图》在70、80年代的中国,正像《蒙娜丽莎》在西方一样的流行。打开杂志,翻开报纸,你会经常看到这一幅古老画卷的启首那一段;它甚至会出现在明信片上,火柴盒上,让你回避不得。于是,也正像《蒙娜丽莎》一样,《洛神赋图》是如此地被滥用,让人几乎从有记忆起就知道这一幅绘画的存在,以致最终变得对它熟视无睹,再没有独特、新鲜的感觉。
这正是《洛神赋图》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形,在耳薰目染之下,这一古老画卷以及关于它的一切都成为了一种知识,我知道这些知识,但并不真正明白这些知识的涵义。直到有一次,我再次偶然地从一本杂志的彩色插页上看到了那如此熟悉的画面,忽然被它奇异的美震慑了。同样的场景,同样的人物,但是,我从洛神回身顾盼、似来似去的身影上,从她临风飘飘的衣带上,从那高古游丝的线描上,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含情脉脉,什么叫惆怅,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即。直到今天,我面对《蒙娜丽莎》,也不会产生西方人那种异常的感动与激动,但是,我却能够理解西方人的这种感情了,因为我知道,这正是我每一次看到《洛神赋图》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情感。
也许正因为对《洛神赋图》太珍重了,我倒一直不急着去读《洛神赋》:在很长时间里,《洛神赋》对我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洛神赋图》的产生提供了一个缘由和依据,好像《洛神赋》存在的价值是因为《洛神赋图》而决定的,在我这里,二者的因果关系被完全颠倒过来了。更何况,我们好像不知从哪里早就知道了《洛神赋》中讲述的故事,以及围绕《洛神赋》所发生的那一场爱怨嗔痴。正像《蒙娜丽莎》一样,你总是听到人们那么郑重其事地提到它,以致会不可抑制地对它丧失好奇。
直到不久以前,为了研究《洛神赋图》中反映的一些服饰和风俗细节,我才找来《洛神赋》认真地读了一回。一读之下,才知道自己过去是多么的鄙陋无知。
二
曹植和甄氏之间的悲剧关系前后持续了若干年,而且过程极其曲折复杂,牵涉到残酷的宫廷政治。但是,作为对心上人的怀念,曹植不是像一般人那样,写一篇悼亡文,絮絮叨叨讲述他自己有多倒霉,他爱的人有多不幸——倘是换上现代人,那是要写上厚厚一本回忆录的,展示他和甄氏之间的每一个细节,所经历的每一场风波,周围人对他们的每一点不公。但是,曹植不是平庸的现代人,他对暴露个人隐私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他只是用短短的篇幅,虚构了一个奇特的神话故事,完全用隐喻的方式,表达了永失我爱的沉痛。正如《桃花扇》呈现出完整的长篇小说结构一样,《洛神赋》很像是一篇精彩的短篇小说。短篇小说所讲述的故事,一般来说,应该是“从现在开始,在现在结束”,《洛神赋》在取材上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
以我们今天人的眼光来看,《洛神赋》不仅是一篇标准的短篇小说,而且是一篇手法非常“现代”的小说。作者在文章的一开始,就对文中故事的真实性进行了一次消解,指出之所以写出这样一篇故事,完全是受了前人创作的启发:
黄初三年,我到京师朝谒,事毕之后,在归途中从洛河上渡过。古代的人有个传说,说是这条河的水神叫做宓妃。我想到宋玉曾经写过楚王和高唐神女的故事,于是也作了这样一篇赋。我的故事是这样的:
我从京师向藩国归去……
翻成白话,几乎让人误以为是博尔赫斯小说的开头。像很多现代小说一样,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