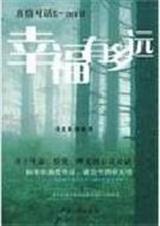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55这些几近于革命性的格言非常值得注意,因为它们显示出,在儒家那里仍清楚源于人及男人之间关系的那些道德,已渐次脱离,日趋自足。“道”和“义”变成了自身自足的价值,成为强加给人的一种行为方式,以便他能战胜自己自然产生的人类感情。从情感角度来说,无论事情错对,人总是倾向于站在自己的父母和家庭一边,正是在此点上,荀子建立起自己的学说,由此和孟子性本善的学说相背离。荀子深深地不相信本能的、天生的“善”,所以在此段文章里,他希望能表明,人有权反驳说:甚至家庭内部成员之爱也有可能是完全有害的,因此就不能形成自然道德的基础。那么,从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道”,特别是“礼”——之中推衍出的更抽象、更冷静、更清晰的概念就是这么一些理想:这些理想能让人从会把自己拉下水的本性中摆脱出来。
荀子的这种建议已经不再属于“儒家”,但有他自己思想的一贯性,即他的“不法先王而法后王”的思想。当然,这种要求不只是为了直接反对墨翟和道家的学说——他们的思想是趋向于回到一个更古老的过去,寻找到自己的这种或那种新理论的支持,而且还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将那些富有意义的轶闻归结到那些年代最遥远的古代人物身上,那些古人在荀子那个时代就已经仅仅只是些流传下来的名字而已——但是,“法后王”这种要求却破坏了儒家自身的“尚古”观念。荀子似乎还认识到,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许多方面,现实已有它自身的问题,因此如果过分依赖已或多或少有点面目模糊的先人典范,那么所有的智识和政治决策都将变得非常困难。所以,他这么写道:
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得,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56我们发现,在这种虽然尚未完全得到承认、但已被清楚地认识到的对现世拯救的强调中,虽然杨朱学说在所有方面都显得和荀子学说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但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密切关系。这并不是只有惟一一个相类点可以证明。上面所征引的句子就再次显示出,荀子对人性的不信任,其本身也表达出对“民”的同样巨大的不信任。“民”的含义既是大群人,也是政治意义上的整体民众。与之相比,荀子相信个体能给世界带来幸福。当然,这个个体不是沉湎于自身快乐、无比自我主义的人,而是一个良好的统治者。为了保证荀子所描绘的理想政体能够实现,需要某些古代圣人的努力;而为了让此政体能真正创立起来,则需要让某类杰出统治者的地位上升到民众之上,从己所欲地在民众的反对之上强施自己的政权,而这所谓政权是建立在“礼”的基础上。杨朱的学说极力避免有政治野心,他的言论鼓吹超越所有既存秩序,因此就和社会秩序无关。但荀子的学说(尽管他自己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却包含了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因为只需要在概念上有微小的转换,就能将一个看起来底基相当保守的意识形态,转变成更具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从而带有明显的极权主义特征。同样地,它最终反对所有传统学说,在一个虽然简洁但非常激烈非常重要的原则(法后王)中,给中国知识分子前景带来根本性的转变。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6)
法家和以法制序
似乎在荀子学说出现之前,这种想法已经广入人心:即认为时代已变,根据旧典范而行的统治只能增长混乱。这种想法相当典型,但并没有在当时所谓中国国土上的几个重要国家内成为主流思想——比如有着古老文化的晋国、齐国和鲁国,用一个大胆的比较,它们构成了古老中国的希腊和意大利——而是在有着更广阔国土的南部楚国和西部秦国中占据了主流地位。最开始,这些国家处于诸侯国地位,但是,就像在历史中永远会发生的那样,随着时间变迁,它们变得比古老的中原国家更为强大,因为它们可以任意扩展疆界。整个文化传统传到它们那里已经非常衰微,但这反而成了它们的优势。它们尝试树立新的必要道德,因为非常清楚,旧道德已经失效。
在这些“富裕”的国家里,由“原土耳其人”和“原藏人”人种成分混合而成的秦国,和远古断然决裂,它不仅和古代政体的典范脱离,也基本上和治国手段的古老理想之典范脱离。可能这种脱离影响了荀子的学说,使之成为将更有效的意识形态溶入儒教的最后尝试。但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即经过那么多“邪说淫辞”后,国家迫切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方法,甚至是场大灾难也在所不惜,这种尝试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57根据史书,商鞅(死于公元前338年)是第一个建立全新道德准则的哲学家和政治家。他是魏王(并不是很有权势)之妾所生的儿子,和贵族家系关系很近,从小受训将来要成为太傅。据他自己所言,他长久以来就对刑法就有着特殊的兴趣。据说他所依附的大臣在临死之时,曾上谏魏王,要么将这位异常聪颖的年轻人视作施政顾问,要么立即放逐他。因为魏王两种建议都没有听,所以那时商鞅就随着那些不可胜数的武士和文人之流一起——他们每个都有着特殊的才能——从一个朝廷奔波到另一个朝廷,希望获得金钱和财富。最后,他来到了秦国。流传下来的记载表明,他最初得到三次接见,于是时提了出习常的、儒家的建议。其结果是秦王昏昏欲睡。直到第四次接见,商鞅突然详细提出了一种完全崭新的思想,认为秦王不该遵循旧时典范,而应该旨在抛弃它们时,秦王被这种说法深深迷住了,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在兴奋之情中商鞅的双膝都碰到了自己的坐席。据说这次接见延续了几天,之后有人问商鞅怎么会这么幸运,商鞅说:“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故吾以强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商鞅的传记中记载,这次会见使商鞅成为重臣,同样也产生了以下言辞,靠它们商鞅为自己反对儒家做了辩护: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觽。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
以商鞅之名命名的《商君书》里,一次又一次地强调疑古主义。这本书当然不是商鞅所撰,但来自于他的学派的学说,这个学派称自己为法家。以下非常直截了当的论述就是个例子:“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这“世”毫无疑问地指向未来,虽然它不是明确说出,而仅仅是通过对过去和现在的忽略来暗示,58或用一些其他方式来下定义,如下所言:“圣人‘见于未萌’。”商鞅认为,如果要最公平正确地对付这些正在萌发的变化,所能运用的神奇手段就是“法”,也就是说,“刑法”,这就是“法”这个概念所意味的一切。对他来说,“法”有着绝对独立的价值,它似乎是自然法的延伸。虽然“法”完全是由单独一人所创,或说得更明白一点,为单独一人服务:即“法”由处于顶层的统治者所立,也为他服务;但就整体人类的幸福而言,“法”不可或缺。通过“法”这个新概念,所有的传统价值都被彻底推翻了。如果不适当地妨碍了国家和统治者无所不及的要求,那么孝、悌、智、信,甚至忠都变成了罪行。
一切事情所要服从的秩序就是军事秩序。在商鞅的理论体系里,士兵占据了最高的地位,或说得更精确一点,他们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范围一直延伸到皇储。这种平等并不在乎任何过去的功勋,因此也就直接消解了古老的、传统的贵族集团,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则之一。另一方面,乍看非常让人震惊的趋势是,法成了某种齐平原则:虽然施以惩罚的违法行为非常之多,惩罚本身却很少变化。几乎所有罪行都被判处死。只不过案情不同,处死的方法和连坐的范围有所变化而己。即便是最无关紧要的过失也会受到野蛮严厉的身体酷刑。而且,恰恰是在商鞅给这些惩罚手段以正当理由的过程中,他的观点来了个180度大转变,揭示出法家的一个中心思想。确然,照此,法家很快就要受到谴责,但它的思想仍继续发挥效力,成了长达几个世纪的中国统治阶级的统治法则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商君书》中,我们看到:“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故无刑也。”
59在《商君书》里一再出现对某种过渡手段进行自我去除(去)的主题。当然,手段本身并没有全部取消,仅仅转换成另一种集合,此集合并不是在现实中实际地改变世界,而只是对社会有潜在的长远影响。自我去除的主题不仅仅构成了严酷刑法的基础,也启发了所有其他暴力形式,正是这些暴力形式将秦国与其他国家区别开来:“故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7)
根据历史记载,就在法律被引进秦国之后没几年,这种惩戒性的秩序在秦国占据了统治地位。看到这种成功,商鞅以前的对手改变了他们的思想,对他表示了赞同,但商鞅仍将他们当作“叛乱者”予以驱逐流放,因为即便他们表示赞同,也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批评,在法律施行上,这种批评等同于违法。法律是以以下方式施行的: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在这种仅仅是其潜在影响超越了曾经得到彻底实现的“大治”的平和中,出现了道家的因素。统治者从自然中学到的“无为”,是道家有关理想世界之统治的最根本概念之一。虽然商鞅是法家一个最重要的代表,法家学派也是因为他对“法”的极度崇拜而被命名,但是法家的思想不完全来自于商鞅一人,而同样也得自另外两个哲学家慎到和申不害,他们明显倾向于纯粹的道家理论。不过,他们的著作只有少量残篇流传下来。从中最多可以得出,申不害的理论归结于“术”,而慎到的理论归结于“势”,这些理论给政体带来几乎神奇的自治效果。管仲(死于公元前645年)学派也发挥着相似的影响。在据说是管仲自己撰写的著作中(虽然可以证明这些作品直到管仲死后才产生),包含了一些章节谈论怎么通过“法”来统治国家。但是,只有那个受过儒家熏陶、而且并不只是靠机遇才成为荀子直系弟子的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才将以上不同成分糅合成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韩非子是法家的理论家;同为荀子弟子的李斯(死于公元前208年)、秦国后期最有权势的大臣,则是法家的实践者。韩非子的一生以悲剧结束,他被自己如此热诚地助以创造的体系之铁轮所吞噬。当韩非子出现在秦国宣扬他的学说时——直到那时,韩非子因据说口吃也只不过以书写的形式传播这些学说,李斯却出于嫉妒,将他投入监狱,迫令他自杀。一个多世纪之前,商鞅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当秦皇太子——商鞅第一个向之宣扬自己学说——死后,商鞅发现自己被牵连进一个阴谋之网中,他试图逃走,转入地下。但据历史记载,60随着秦国权势在整个帝国和它的体系中越来越强大,它的监视系统和举报系统也臻于完善,所以商鞅的这种努力白费了,最后他被抓获并被五马分尸。
在韩非子的著作中,仍然依稀可见荀子的影子。韩非子执著地发展了其师理论中潜含的部分,即关于人性恶的讨论。人们可以看到,韩非子的某些论述就像一阵遥远的回声,回荡着荀子对孟子所鼓吹的自然美德的批评,而这些所谓自然美德之最重要的温床就是家庭。然而,对韩非子来说,这些自然美德不过是国家的“寄生虱”:
夫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也。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何则?国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
对韩非子来说,自然形成的家庭中的家族秩序,不能被祭仪和朝廷仪礼的秩序原则所取代。而荀子认为后者才是社会的基础。和商鞅一样,韩非子考虑的是道德秩序。它将以一种理想的手段把平等和不平等结合在一起:即朝廷制服和官员勋章。韩非子公开宣称,他的目的是要通过完全是由人指定的法则秩序将所有人组织在一起,当然这种法则肯定不是“仁”。这样一种制度体系将不会允许有人能逃离到一个更高的既不服从于人、也不服从于国家制裁的秩序中去。因此他要求加强军事力量,但这不是主要目的,以下他描述的这个故事非常明显地显示出“仁治”与“军事”的对照:
61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
第二部分:确定边界(前1500—前200年)第四节 黄金现世和发现未来(8)
对军事的强调一代代地流传,有着影响深远的反人文主义的意味,但它并不仅仅来自以上态度,它同样是因为对所有纯理论的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年代久远,常常会有力地打断中国的传统,和无数只关心自己长长手指甲的知识分子之空谈道德形成一种对比。“今境内之民皆言治,”韩非子这么写道:
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
法家的混杂形式
韩非子的这些话,可以追溯到贴着激进儒家标签的荀子身上,但同时也非常贴近道家的思想。可以指出,这再次显示出后来在这两个世界观之间建立起来的壁障是多么武断。其中原因可能部分归之于想要让人民忘却法家曾有一段时间连接起了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