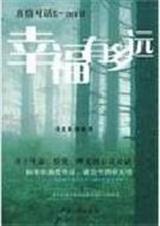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者不能理解的意义含糊的富有睿智色彩的短篇故事,而且还有很多难解的、令人迷惑的虚构引为,这些行为从某些方面看来几乎具有“偶发事件”的性质。这本书都是一些在历史中居从属地位的事件,但在每章内又是按编年来撰写的。这些记载使人深刻洞察承载自由精神的某些行为其繁荣与衰落的过程。《列子》中的孤独者由于社会的锁链没有紧束着他,则被认为是疯狂的,这个孤独者此时在《世说新语》中变得极端狂癫、语无伦次,奢侈糜烂。在《世说新语》中有一个非常具有表现力的故事,据故事所述,一个年青的亲戚表示自己要成为一个新的学生、决定成为天才时,竹林七贤之一故意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然而不是贤者阻止了这一新时尚的出现;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极度的贫穷,部分地对这一时尚的崩解负有一定的责任。而睿智时代产生的这些恶作剧不久便渐于停止,部分由于高洁的精神激发,部分由于虚无主义的绝望。在社会里自由观念的发展遭至失败,它仅限于保存在上层阶级的一小撮人中,已不能构成真正的问题,不久便走向消亡之路。一方面,所能遗留的是陈旧的令人沮丧的人们熟晓的自然,野性,自由的对立面,另一方面则是文明、秩序,以及自由的缺乏。因而在和谐中发现幸福似乎继续是不可能的。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1)
佛教带来幸福处所的变化
刚才讨论的天才的愤世嫉俗者们力图在政治上远离老百姓,生活在对老百姓的嘲笑、蔑视中。在他们的所谓清谈中,其思想背后吸收的虚无主义与悲观主义的因素日益为人所识,而且他们将之变成某种确定性的东西,那就是佛教。绝望与怀疑,失望与愤世,始于孔子的指向现世时代的终极取向,很自然地在一个时代转化成了完全扎根于宗教的终极目的,而这将尽可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不经意之中,结束成为新的开始,精彩篇章的开始展开了一个新的序幕。
154中国最初的佛教迹象要回溯到公元一世纪。然而很奇怪的是,很多年以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佛教不是道教的变种,而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佛教产生的原因有种种,很长时间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一直是模糊的。但有件发生于西方的事情不能认为是外来的。据传说,老子把《道德经》交给关隘的哨兵后就消失于西方的山中。完成《道德经》是他最后的心愿,是他对信仰的证明。西方是最为古老的道教的天堂,是“西王母”所在之地。后来有许多道士坚持说佛就是老子,他离开中国,在印度宣教。除此而外,还涉及佛家的社会态度。文人们倾向于把世界与社会看成纯属一体的一样东西,所以在佛教对人的悲观的放弃与信任大自然的道家对社会的基本乐观的放弃之间,没有什么必要的清晰的差别。因而表面上看来,佛家的消极反应与道家反对国家对人民的要求、反对社会几乎是一样的。最初,佛教的许多概念并没有直译成汉语,已成为特殊的事实,这就意味着外来词被冷落一边。因为是概念,汉语书写系统确实已不能胜任这一任务。取而代之的是作出确切翻译每一术语的努力。然而严格说来所有能符合这一目的汉语词也都是传统中国哲学中的相当简单的语汇,与相当丰富与复杂的佛家术语尚不能相比,因而一开始就产生了严重的误解。但后来,误解得到了改正。然而也仅是在理论上而已。实际是,因为这些错误已很早就深深地进入了人的意识之中,所以它们永远也不会产生什么有益之处。极其显然的是,令人惊叹的汉语同化力确实是由于语言的无力而导致,实事求是地说,尤其是由于其取代外来思维系统的书写系统而致。所有从外部渗入中国的意识形态渐渐显出其悲哀,因为汉语书写的概念体系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来词溜进其词汇之中,除非它作为一个外来因素已得到同化。外来词必得经过“翻译”,这就意味着外来词必须被同化(通常是简单化了)。否则,这些词从其完全意义上而讲,将永远打上舶来品的烙印。在这一过程中,不论发生何种性质的国家范围的运动都导致了它们的厄运。
早期对佛教的接收过程也有严重的误解,导致误解的原因是人们把佛教与中国的灵魂观等同起来。在佛教看来,“灵”(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是对个人存在产生幻灭的一个至为关键的构成因素,也是产生生命再生轮回的原因。起先,它并不意味灵魂经过了各种各样的美化,因为它再度暗示了“自我”的存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是一种生命轮回运动,一种充满活力的推动自身发展的力量 ,堪与物理学中的波浪运动相媲美。这一佛教概念翻译为汉语词为“生灵”。据古老的中国人信仰看来,灵魂是人生命中不朽的部分,人死后,它将再度被世界上的鬼魂接纳(后来,也称之为“魂”,以区别于短暂的“魄”),正唯如此,导致人们对佛教的误解。因为哲学化的佛教不仅摒弃了灵魂的概念,而且打算摧毁生命轮回,于是使佛教成为异已的这个问题立即出现了,它就是在佛教中新发现的人们误解了的灵魂永生问题。这个问题使佛教与道教早已提出的重大主旨直接地紧密相连,并且是多层次、多方面地相连,即怎样保存生命。
155儒家与道家在争论关于死后的生命与人的永生问题前,就曾改变过他们的立场。起先,儒家将他们的整体信仰建立在对古人教条的崇拜基础上。古代人所谓生命延续的观点因而是天经地义的。但渐渐地,它开始离开早期幼稚的观点,日益倾向于看到各种具体宗教性事物,包括作为隐喻的从灵魂中获取永生的信仰。相反道家则开始宣称,个人还在活着时,就得放弃其个性,因为人必得一死,事实是个人不可能从死亡中获救。但后来,道家越来越致力于发现保存个人生命的方法,致力于使人获得永生、成仙得道进入天堂的手段。
尽管道家与儒家一直受人尊重的地位已发生了变化,它们仍坚持对立。又同样对于佛家而言,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颇为矛盾的是,佛教并未十分致力于在时空上摒弃这个世界,而是致力于戳穿所有传统观念,当知识分子们将这一观点与儒家(也与道家)相比时,这一观点就使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之着迷了,因为它看到一个不可理解的巨大多维世界,在那里,穿越同样巨大的短暂而广阔的距离,所有的生灵在各个方向上被因果之索连接在一起。确切地说,由于“灵魂穿越存在”的错误信仰,于是人们认为万物的个体生命处于芸芸众生中,创世时代种种生命形式就已注定了芸芸众生,万古如斯。在佛教中所谓占据中心地位的部分,在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时空观念前,显得黯然失色,这要追溯到婆罗门的影响,但它已深植于中国人思想之中,并将之看作习以为常的“人的历史维度”。通过无尽的再生链条,人能获得完全的因果报应,这将得到应验。作为宗教而言,这一观点使佛教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它在中国能得到接受则就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了,因为在中国伦理道德注定比冥想更为重要。下列两段文字则深刻洞察了这一新动向。其中之一是僧人慧琳于431年写的。他摒弃了灵魂不灭观,而赞同其对手陈述的观点,这将在下面征引。第二段则是佛教徒宗炳(375…443年)在433年所写,因为他攻击慧琳的文章,但多少也与后者的反对观点相一致: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2)
156周孔为教,正及一世,不见来生无穷之缘,积善不过子孙之庆,累恶不过余殃之罚,报效止于荣禄,诛责止于穷贱,视听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释迦关无穷之业,拔重关之险,陶方寸之虑,宇宙不足盈其明,设一慈之救,众生不足其化,叙地狱则民惧其罪,敷天堂则物欢其福,措泥洹以长归,乘法身以遐览,神变无不周,灵泽靡不覃,先觉翻翔于上世,后悟腾翥而不绍,坎井之局,何以识大方之家乎?
生不独造,必传所资。仰追所传,则无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则亦无竟也。是身也,既日用无垠之实,亲由无始而来,又将传于无竟而去矣。然则无量无边之旷,无始无终之久,人固相与凌之以自敷者也。是以居赤县,于八极曾不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罗万二千天下,恒沙阅国界,飞尘纪积劫。普冥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独安我而疑彼哉。夫秋毫处沧海,其悬犹有极也。今缀彝伦于太虚,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迩。所谓轩辕之前,遐哉邈矣者,体天道以高览,盖昨日之事耳。书称知远,不出唐虞;春秋属辞,尽于王业;礼乐之良敬,诗易之温洁。今于无穷之中,焕三千日月以列照,丽万二千天下以贞观,乃知周孔所述,盖于蛮触之域,应求治之粗感,且宁乏于一生之内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论也。若不然也。何其笃于为始形。而略于为终神哉。登蒙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际矣。
157通过生活空间的爆炸性扩展,此时此地的现实区域缩小了。它对社会与个人的各种各样的对理想境界的构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这个新宇宙巨大的时空背景的出现,古时候的黄金时代与世界之尽头的天堂一样令人怀疑,二者都从现实中被一寸一寸地分离出来。由于期待着从黄金时代与天堂中获取真正的、永恒的救赎,二者似乎越发靠近了。最具决定性的是,佛教中幸福的意义,实际上与机智的中国人之思维系统中的幸福观完全不同。佛教不否定大量短暂、有限的快乐的存在。但其教义的中心意旨是确信生命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永恒的幸福,这一信仰也并未被后来教义中出现的新成分所丢弃。这一铁的法则不仅用于人与动物,甚至也用于至高秩序中的神人。并且佛教认为,从一开始,不管哪一层面的所有存在都被不幸所染指;不久,不幸就统治了存在。只有涅槃才能从存在的毒咒中解救人们的不幸。对这一境况的任何观点,描述或定义原则上都是不可能的。而这一形势不是“虚无”,它必然地缺乏倾向性,分界面及区别性。这种信仰不仅起源于对这个世界的背弃,而且源于幸福自身,因为在它看来,每一种幸福的形式都包含着忍受痛苦的真面目,把人们从救赎的道路上拉出来,而且也暗示了人们很少能获得好报。它代表了一种生命形式,这种生命是由前世修业决定的,因而对其信徒来说,天国与天堂里也染上了佛教徒的色彩,无法摆脱佛教色彩的浸染。它们是暂时的有限的天堂,而它们令人质疑的价值也在宗教范围之内为人们所认识,为人们所讨论。例如,在慧琳431年写就的一篇文章中,则对他的反对者作出了回答,其中有人们期待出现在佛教徒天堂里的幸福赞歌:
“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义而蹈道,惧地狱以敕身,孰与从理以端心。礼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肃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无吝之情。美泥洹之乐,生耽逸之虑,赞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远利又兴,虽言菩萨无欲,群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开利竞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来生之欲,何以权其当生之滞。物情不能顿至,故积渐以诱之。夺此俄倾,要彼无穷,若弗勤春稼,秋穑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遮虑者,长沦于九泉之下矣。”
158因而知识界出现与现世世界的分离以及对现世幸福的认识产生了怀疑的现象,它给10、11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打上了印记。事实是,它不会放弃在寻求现世幸福的过程中彰显自身,更为正确地说,这一逆转已成事实。中国的佛教时代是一个持续的战斗年代,各民族国家间都处于充满活力的文化交流中。后来而不是最后,文化呈现了成熟的、世界性的辉煌,这在中国是前所未有而且永不会再现的盛况。在其繁荣程度与灵活性上来说,人们相信佛教自身表现出来的、将永远存在的生命之昙花一现的繁荣及其中的悲剧因素。这个世界不再像所有过去的中国哲人所看到的是牢不可破永恒存在的,在其他许多方面,哲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较大的偏差。不仅自我的湮灭,而且人类得以安身立命的整个世界的湮灭现在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显然已无法抗拒了。诚然,如此的湮灭确实代表了人类努力的终极目标。这种精神发展的必然是它扩展着,进而超出真正佛教徒的范围而在许多文人和百姓中传播,这比难以置信的渐而构成一个重要经济政治因素(然而仍不能确定)的寺院生活,更为具体地反映了新的消极悲观态度。
第四部分:对彼岸世界的迷恋(约300—1000年)第二节 在西方天堂里的救赎(3)
显然,知识界的氛围是对于理想社会秩序的新模式并没有好感。对于注定不得不遭受承受苦难的世界而言,不值得为此立刻努力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对于任何实现理想所必需的努力而言,这些解决办法不可能具有长久永效性,在遭逢厄运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僧侣放弃其义务,不思其荣辱,由其家庭供养因而使自身获得自由,如果这些人最易于得到救赎,那么这时一个模范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幸福的生命的用途是什么呢?这是固执的儒者们经常抱怨的世界,如果这将能得到救赎的话,那么对宗教的狂热不能阻止人们短期的自我残害。因而人们希望离开流泪谷而到达彼岸世界。严格说来,佛教中描述的天国、天堂在本质上与现世没有区别,然而这些地方向人们允诺说,幸福与长寿是短暂的,不必总是期盼着它们;另一方面则是关于菩萨的教义,对此很难在理想领域里反对它,于此人们发现了它被狂热接受的原因,尤其是其中的大乘佛教,在东亚地区起了决定性作用。其中的佛们放弃了涅槃来助人超渡,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观音,她眼观八方,耳听六路。这一形象产生于7世纪,在中国渐而形成女身。观音的形象多年来一直在绘画、雕塑中有所表现, 且给人印象极为深刻,它使人极易联想起基督教中的圣母形象。和许多其他菩萨一样,在人们的想像中,一直把观音看作受人崇拜的居住在类似天堂地区的天与地之间的使者。这些则又赋予其他那些天堂以更大的价值,证明了人们对它们的渴望,尤其当天堂中的某些被当作为涅槃的最初必经之地时。虽然并没有特别强调其价值以及从理论上来证实,然而通过佛教展示给人们华丽的描绘,佛教的天国与天堂占据了中国人心灵。纯粹从天堂数量上来看,就发生了从事实到事实的变化,并且激发了人们对日益完美幸福的想像力,具有某种使人沉醉的力量。当道家把儒家与法家对理想的描述搁置一边,涉及天堂时,总是单纯而质朴,从而具有社会指向性。159然而来自印度的这些观点则以其开阔的想像力来面对中国人。它们详细列举每一财宝的名称已足以证明是多么地迷惑人们,以致他们无条件地向这一奇迹屈服。更为甚者,有时在印度人那些浮夸的想像中,无情地降低了古老的、某种程度上已稳固建立在中国人心中的,然而也可能更是可感亲切而朴素的天堂的地位,将之看作是毫无意义、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然而印度人的天堂更为阴暗,在他们无止尽的反复描述中,体现的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