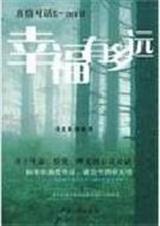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9)
然而,自宋以后,这些秘密团体也宣扬那些原本相当正统、但后来却和被“统一”这个概念搞得神魂颠倒的新儒家纲要不再一致的儒家教义。在新环境下,这些儒家思想经历了一种神秘化过程,有时甚至是粗俗化了,但其肇端却清晰可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在秘密社团里被讨论的一批预言性作品,比如说《推背图》,据说此书可以推溯到公元7世纪。题名中“图”这个词暗示着要接续汉代谶纬书籍的传统(汉疏),那早在公元460年后就被废除了。这些新的谶纬作品马上引致同样的命运是很自然的,因为在其中有着和《易经》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有关一定统治时期(代)会被轮回替代的汉代概念,以及将世界周期看成是连贯整体的西方学说。这些预言作品的形式让我们回想起我们的贞卜作品。它们经常包含着诗篇韵文(总是随着一个版本到下一个版本发生变化),也常常配有图画,比如就像《推背图》那样。有些甚至附有评论注释,试图要确定诗篇中描绘的事件哪些已然发生,哪些尚未发生。这提示了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将现时和紧接而来的未来正确地联系起来,当然未来是他们更为关心的所在。新儒家相信一个单一的、不变的原则(理)掌握着人类的所有历史(在这方面,他们和汉儒不同),所以,历史是以个别的、繁荣或衰退的阶段在进行这种观念必然要受到怀疑,特别是当有人想到那种谶纬作品是要取代以往的历史编纂时。以往的历史编纂是记录那在连续不断的朝代里不断演进的历史的。因此,它必须将诸如《推背图》这样的书看成非常之危险,因为其作品结构是一系列连续的图画,每个画面都代表了个别的、可以被替代的历史阶段。更有甚者,这些个别的历史阶段都步向一个“大结局”,虽然此终局不甚明了,不知是指一个新循环的开始呢,还是指一个会变成一个法官坐在那里审判整个历史过往的真正的“新开始”。似乎《推背图》的注释者,甚至可能是作者本人都倾向于后一个观点,因为在第一幅图中——这在所有版本中都一样——画的是日、月,这和附加的文字一起大都被解释成是世界的创始。没有任何一种单一解释试图通释所有的图画的文字(通常有60幅)以及它们和历史事件的关联。“大结局”总是存在于未来。另之,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它们对最后一幅图的再绘中,不同的版本都相当不同。
225虽然这些秘密团体总是遭到禁止,但他们散布的预言性著作却对民众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1945—1949年间,共产党军队和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正在打仗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再次变得非常明显。《推背图》中有一幅图,画的是水中间有一块长满青草的石头。这被解释成它代表了“人民的”的起义浪潮围绕着蒋介石(蒋这个姓有个草字头)。将预言性著作当作政治目标的直接宣传支持,使作品变得像打油诗,那是自汉以来所有革命运动都偏爱的手段。对“预兆”的处理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关注,特别是在公元前的最后两个世纪。在汉代,卜筮和谶纬著作是儒家反对法家倾向的统治者的武器,后来却倒过来变成了秘密社团反对儒家的武器,因为儒家早已和当权者沆瀣一气。在宋朝早期,这种发展趋势已经露出苗头,显示出在世纪变迁中儒家已在多大程度上偏向“右翼”。但是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即便是“君权神授”导致朝代更替这个观念——它无疑是儒家的口号,虽然不是他们发明的,但肯定是他们致力鼓吹的——也渐渐地、越来越多地为秘密团体所用,因为新儒家对朝代变化这个观念感到极不适意。从宋朝以后,这样的朝代更替再也没有发生,除了要么被异族征服,要么反过来又颠覆异族统治。这意味着“君权神授”变得无关紧要(在被异族征服的情形中)或者它不需要被讨论(当异族统治被推翻的时候)。但本土皇朝宁愿求助于“蛮族”,也不肯承认“君权神授”的失败。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0)
秘密团体和他们的社会政治诉求
秘密团体领导的起义借用了从前的儒家因素,这个事实显示出,企图拥有权力的那些力量将自身看作是潜在的统治组织,而且并没有仅仅把一个他世秩序作为自己的目标。至少,不同起义的首领显得能熟练利用民众的真正宗教信仰。这似乎显示出他们寻求的改变世界的替代方案常常不是要在彼界实现,而是对当世国家和社会进行重新建构。大部分起义教派常拥有占主导地位的军事力量,其结构之特色就体现出这一点。它们的领袖所拥有的名号也是如此。比如说,“上天大将军”就代表了宗教和军事思维的有趣混合体。又比如说,道家组织形式的复苏——它最初是在佛教渗透进来之前的两三个世纪中、在“黄巾教”和“五斗米道”中创建——也指出了同一个趋势。但就像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打坐一样,我们在此遇到的不是道教组织的原初形式,而是受外国宗教影响后的有非常典型的修正组织形式。不幸的是,对此民众起义的所有记录几乎都经过了儒家历史学家之手。由此,我们对这些不同运动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印象是不准确的,甚至常常是被扭曲的。但我们至少可以对它们的产生有一个粗略的概念。因为,即使一方面考虑到儒家带有偏见,另一方面又是起义者受教育不多,常常公开直言反知识分子的偏见,不愿过度细致地描写他们的纲要,以下情况仍是事实:记录中有些用词揭示了它们从属的传统。“黄巾教”和“五斗米道”精神的继承人创立了“事魔食菜”教,在这方面就相当典型。它被儒家学者庄季裕(13世纪)记载下来:
227事魔食菜,法禁甚严。……闻其法断荤酒,不事神佛祖先。……死则裸葬……小人无识,不知绝酒肉、燕祭、厚葬,自能积财也。又始投其党,有甚贫者,众率财以助,积微以至于小康矣。凡出入经过,虽不识,党人皆馆毂焉。人物用之无问,谓为一家。故有无碍被之说,以是诱惑其众。其魁谓之“魔王”,为之佐者,谓之“魔翁”、“魔母”,各诱化人。旦望人出四十九钱于魔翁处烧香,魔母则聚所得缗钱,以时纳于魔王。岁获不赀云。亦诵《金刚经》,取“以色见我为邪道”,故不事神佛,但拜日月,以为真佛。……其初授法,设誓甚重,然以张角为祖,虽死于汤镬,终不敢言“角”字。……而又谓人生为苦,若杀之,是救其苦也,谓之度人。度多者则可以成佛……甘嗜杀人,最为大患。尤憎恶释氏,盖以戒杀与之为戾耳。
此篇描绘,乍一看前后矛盾,但如果更仔细地研究一下那个奇怪的词“魔”,通篇就变得更能理解了。这个教派给自己起名为“魔”,这个字有着重要作用。它似乎是从儒家对“麻”这个词的细微转变中而来,反过来又指向摩尼,也就是说摩尼教(也许还有拜火教)。在这种情况下,对日月的崇拜就有了意义。不过,此中佛教的特点显得是独立的因素,并没有真正的影响,最后一句话肯定了这一点。但“杀人就是将之从万恶中解脱”,这个主题也许间接来自佛教,因为相比中国本土世界观,它的悲观和佛教更为一致。在公元5世纪早些年的一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这一点的说明,其中讨论了道士孙恩的起义,他肯定利用了一些佛教观点。另外,在佛教的禅宗公案里,我们也可以不时发现在一个奇怪语境中的“杀、杀”的表述。无论如何,从11世纪末起,即“事魔食菜”教形成的时候,杀人就是度人这个主题一再出现。第一次是在方腊起义(1120年)中,他被一些当时的学者看作是事魔者。在明朝最著名的一次起义中,这个主旨再次出现。张献忠(死于1649年)将自己看作是道家神仙玉皇大帝的特使,将他占领的主要地区杀了个遍。但在他这个例子中,似乎也体现出某种赎罪或牺牲的主题,因为在体现了他纲领的那个著名的“七杀碑”中,他这么写道:“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228但在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方腊起义中,其中的宗教因素事实上不再像在唐朝起义中那样扮演维续的角色。自宋朝建立以后,不管引发起义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大部分起义是因为社会政治状况让民众忧虑不安,导致他们揭竿而起。在方勺(12世纪)撰写的《清溪寇轨》中,对方腊起义那时的思想气氛作出了相当生动的说明。它带一点诗意,但大概传达了那些被称为“农民起义”的起义中大部分都有的循环出现的那一面,由此引起了西方人和东方人——主要是19世纪后20年的中国学者——的注意: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1)
腊怨而未敢发,会花石纲之扰,遂因民不忍,阴取贫乏游手之徒,赈恤接纳之。众心既归,乃椎牛酾酒,召恶少之尤者百余人会,饮酒数行,腊起曰:“天下国家,本同一理。今有子弟耕织,终岁劳苦,少有粟帛,父兄悉取而靡荡之,稍不如意,则鞭笞酷虐,至死弗恤。於汝甘乎?”皆曰:“不能。”腊曰:“靡荡之余,有悉举而奉之仇雠,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贵,反见侵侮,则使子弟应之,子弟力弗能支,则谴责无所不至。然岁奉仇雠之物,初不以侵侮废也。於汝甘乎?”皆曰:“岂有此理!”腊涕泣曰:“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夫天生蒸民,树之司牧,本以养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靡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废,宰相以为安边之长策也。独吾民终岁勤勤,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诸君以为何如?”皆愤愤曰:“惟命!”腊曰:“三十年来,元老旧臣贬死殆尽,当轴者皆龌龊邪佞之徒,但知以声色土木淫虫上心耳。……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我但画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四方孰不敛衽来朝,十年之间,终当一混矣。不然,徒死于贪吏耳。诸君其筹之。”皆曰:“善。”遂部署其众千余人,以诛朱为名,见官吏公使人皆杀之。民方苦于侵渔,果所在响应,数日,有众十万。
229如果仔细分析方腊的言辞,可以发现它已经包含了三个要素,这三个要素给自随后世纪一直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所有起义都以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和任何宗教因素无关,只是仅仅和宗教力量相伴而生而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三个要素都是从慈悲而来的消极理想。第一个,也是相当普遍的,是在被压迫的政体下争取自由,这主要是针对苛捐杂税和腐败官吏而言。第二个,是争取地方自治,用诸如这样的词语表现出来:“吾东南赤子”、“画江而守”等等。虽然这种情绪被小心翼翼地用一种统一的、强大的帝国观抹平了。第三,是争取民族的强势和伟大,那将终止由蛮族入侵带来的蒙耻和痛苦。同时,这三个理想对儒家构成了一个非直接的攻击,或至少对新儒家是如此,即便起义倡导者并没有总是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新儒家不仅完全支持政体,而且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儒家的绥靖主义值得引起特别关注,因为不仅是在宋朝,这种态度引起了令人震惊的军事上的薄弱,反过来,它也导致了向外族奉以岁贡以求安宁的政策,方腊提到了这一点是有理由的(当然,虽然这是事实,但这种方法的代价总要比战争小,即使它并不能长远地阻止战争爆发)。而且,继元朝以后的本土政权明朝,它的对外政策相对来说软弱无效,绥靖主义也要为之负责。如今中国的辽阔疆域就是由异族蒙古人在当政时拓展的。如果要考察中国在本土朝代时所拥有的可观版图,那就要追溯到7世纪的唐朝。然而在那时,佛教而不是儒教是中国的官方信条。儒教总是要削弱军政,自宋以后,也成功地在本土朝代中做到了这一点。基本上,这就意味着军事薄弱外交无力。由此,儒家总是尴尬地容易受到任何或每一种民族运动的攻击。在不同意见的巨大冲突中,并不可能总宣称更高的“文化”补偿了这种明显的国耻,特别是当这种意见对对手而言几乎毫无意义时(在起义民众那里即是如此),或当这种文化的优势开始被它的支持者质疑时,19世纪以来这种趋势愈来愈甚。
230但是,不管这些起义在特点上是宗教的、民族的、或具有地方色彩的,所有的“农民起义”都有他们基本的起因,他们永恒的主题,即反抗当权披着家长制的儒家外套一再对民众进行无耻的剥削。所有其他动机都可能被遗忘,这一点永远不会被忘记。以下事实最具有说服力地表达出这一点:当没有别的理想被宣称的时候,对所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状况进行根本彻底地颠覆就变成了一种理想。特别是在明朝,非常频繁出现的一个起义目的就是对财产的更公平分配(尤其是土地财产)。但应该如何实现这种变化,其管理形式是如何却根本没被提到过,或者仅仅是通过一些早已无用的陈词滥调(比如说“井田制”)来暗示。这方面933年发生的王小波起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来自社会底层,只有姓没有名,“小波”显然只是口语发音的记录,因为文献记载用了各种不同的汉字来注这两个音。宋代正史里对他的活动只有一些干巴巴的记录:“淳化中,青城县民王小波聚众为乱,谓其众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附者益众,遂攻陷青城县,掠彭山。”
第五部分:现实的灰尘(1000—1800年)第一节 忠诚和异端(12)
另一个起义领袖钟相,也用了同样的观点,不过是从更高的一个层面上。公元12世纪,当宋朝频繁发动灾难性的卫国战、抵抗北部的金兀朮时,钟相加入到那些半是爱国主义者、半是罗宾汉式的“绿林大盗”的非儒家行列中,发动了边境后和边境间的游击战。这些人后来大受赞扬,特别是在晚至19世纪的通俗小说中。接下来的这段文字是由儒家历史学家徐梦莘(1124——1205年)所撰写,听上去了无热情,虽然在那些爱国强盗身上,也有一些让那些儒家觉得有价值的东西:
231钟相,鼎州武陵县人……自号“老爷”,亦称弥天大圣,言有神通,与天通,能救人疾患。阴语其徒则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持此说以动小民,故环数百里间,小民无知,翕然从之。备糈谒相旁午于道,谓之“拜爷”。如是者凡二十余年……金人犯潭州,孔彦舟入澧州,相乘人情惊扰,以据彦舟为名,聚众于是日起兵。鼎澧荆南之民响应……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雠隙之人,谓贼兵为爷儿,谓国典为邪法,谓杀人为行法,为劫财为均平。病者不许服药,死者不许行丧,唯以拜爷为事,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凡十九县皆为盗区矣。
可以感觉到,民众精神力量的爆发非常强烈地震撼了像徐梦莘这样沉着冷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