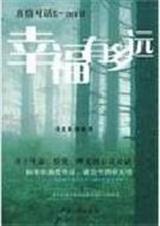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49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康有为此处宣布的对妇女的彻底解放,只有伴随着对中国传统、严格的父权家庭的彻底改革才能实现。由此,伴随着康有为对性别界废除的,自然是他对“第五界”——家庭,废除的坚持。在细致的导言中,他要求中国家庭所扮演的角色,应与西方的家庭有所对立(此处,他所了解的西方式家庭,仿佛只是盎格鲁…萨克逊式的,或者是美国式的西方家庭)。对这一章的细致论述,似乎表明他认为这一章所涉及的内容是他整体改革的关键。尽管,他自己对整个中国社会的破坏怀有歉疚,这对他而言仍然不能不说是一种隐秘的情感,但他似乎并不介意在此处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失落的感伤。他相信,只有通过建立在儒家家庭式宗教,中国才能成为世界上最为平民化的国家。他斥责西方儿童对他们父母的不敬,认为这种态度主要来自妇女地位的解放,使得下一代视妻子甚于自己的生身父母。然而他同时相信,西方式的小家庭要较中国式的大家族更为接近通向“大同”社会的家庭理念,因为个人利己主义的程度在家庭规模中有必不可少的功能。当然,家庭——这里包括西方式的家庭——在“大同”世界建立之前,必须已然消亡。康有为在导言结尾处所列出的针对家庭的十四条或有重叠的控诉,可被主要归为以下三条: 1) 家庭所生育、抚养的孩子因为缺乏控制与规范,在身体条件上并不能享受公平的机会,其中既有遗传因素,又有后天抚育、喂养过程中在不同家庭中不同的对待; 2) 同样的状况也会影响儿童在智力上的发育,大家族意味着他们比穷人家庭更有历史,家教更严格精细。学校教育结合家庭教育的阶段,不过是康有为在教育中由“家学”(family school,中国千年以来的传统)直至“公学”(total school,所有儿童从一岁到二十岁之间都必须参加)三个阶段中的过渡性阶段; 3) 家庭的自私性使得国家不可能自由地处理劳动量与个人财产的关系,由此也限制了财产在公共项目(如道路建设)中的使用,而这些社会工程之前都是由家庭完成的(如学校的建设、成年人组织家庭的所需)。但是,以家庭的方式来思考,不利于社会成员分担应有的责任,没有这一点,“大同社会”的秩序将不可能实现。有意识地,康有为使自己的理念与新儒家神圣的经典《大学》形成对照,在那里,世界的和平只有通过“家庭的秩序”(“齐家”)才能实现。以下,是他的一些反对家庭的论述:
316“以有家而欲至太平,是泛绝流断港而欲至于通津也。不宁唯是,欲至太平而有家,是犹负土而浚川,添藉以救火也,愈行而愈阻矣。故欲至太平独立性善之美,惟有去国而已,去家而已。”
因此,所有这些家庭曾经承担的功能,都将在康有为设计出的计划中被公共设施替代。从摇篮到坟墓,每个人都将在世界政府的力量下被塑造、帮助,以达到最终完全的平等。在为这个目标服务的十二个机构中,三个机构面向养育,四个面向教育,另有五个面向公民权:
一曰人本院,凡妇女怀妊之后皆入焉,以端人生之本;胎教之院,吾欲名之曰人本院也,不必其夫赡养。二曰公立育婴院,凡妇女生育之后,婴儿即拨入育婴院以育之,不必其母抚育。三曰公立怀幼院,凡婴儿三岁之后,移入此院以鞠之,不必其父母怀抱。四曰公立蒙学院,凡儿童六岁之后,入此院以教之。五曰公立小学院,凡儿童十岁至十四岁,入此院以教之。六曰公立中学院,凡人十五岁至十七岁,入此院以教之。七曰公立大学院,凡人十八岁至二十岁,入此院以教之。八曰公立医疾院,凡人之有疾者入焉。十曰公立恤贫院,凡人之贫而无依者入焉。十一曰公立养病院,凡人之废疾者入焉。十二曰公立化人院,凡人之死者入焉。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9)
317所有这些在结构概况中列出的公共机构,康有为都分别分章节深入细致地讨论。他的理念非常有趣,因为这样的对公共机构的设定,并非来自于任何东方或西方的模型,因此他也可以任自己的想像力信马由缰地展开下去。“人本院”设立可以作为例证。康有为根据古老的儒家经典《礼记》,部分地修正了胎教的过程,尽管《礼记》中所记载的内容,本来仅是对贵族王公之家行为的指导。绝大多数相关规定都有类似之处。如同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它们既含有科学优生学的成分,又不乏迷信色彩。在经常的药品监管以外,还要保证光线充足令人愉悦的房间、友善的护士、经过筛选的食物、精美的书籍与图片,以及具有启发性的音乐,这会使母亲的活动具有韵律感(这可以通过母亲的衣着以及腰带饰物控制),以上这些,都会有益于胎儿的发育。为了有助于这种融洽,康有为同样考虑到了有规律地控制母亲们的性生活。在胎儿出生之前,她应当只有一名固定的性伙伴。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她仍然应在孕期生活的房间进行哺乳,基于卫生学上的原因,甚至规定了呆板的替代品。尽管康有为并不相信通过这些提前措施,就足以去除生育的困难,他仍然希望能够将困难尽量减少。其他一些措施,还包括对堕胎(他认为会自行消失的犯罪中的一种)的严厉处罚,对母性的介绍,以及对生育超过一个子女的母亲的表彰。他认为“人本院”最重要的作用,是它对统一后的种族的影响与塑造。那些机构将主要建筑于山上,那里有宜人的气候和入胜的美景。它们将尤其向“下等人”敞开,帮助他们赶上“高等人”的发展步伐。康有为认为这些措施是极为可行的,因为出生的婴儿会告别它们的母亲和出生环境,进入育婴机构,享受同等宜人的自然条件。这种方法同时还能保证下等人的境遇不会传给他们的下一代。由于姓氏将会随着家族的消亡而消失,所有的小孩都将拥有他们各自的名字。通过这些名字,能够确定他们出生于哪个房间、哪个人本院、出生地的纬度以及生日,但是诸如他的出身以及父母的阶层这些数据的细节,将不会被体现出来。
318
教育、抚养以及惩罚
“大同世界”中对新人的教育,从幼儿园到大学教育,都受到康有为计划的塑造,不仅因为教育是非同一般的公共机构,更因为这种机构普世性的特征。在最低的两个年级,直至第十一年,老师将全部为女性,因为她们“更有耐心,更温柔,友好,令人愉快”。而到了更高的两个年级,在第十五至第二十年之间,男性教师地位将更加主导。这主要由教育过程本身决定。幼儿园教育主要以身体锻炼为主,随后逐渐集中到智力的训练,并在最后四五年中进入包含专业技能的培养。因为“大同之时,无一业不设专门,无一人不有专学。”但是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理论学习在现实社会中必须找到它的应用。一般而言,较高层次学校类似于训练各类官员的学校。居住一万至四五万的学生。在职能如军官或官员的教师训练下,他们将接受“如任何军队般严厉”的训练。
这种观念与加尔文教教徒的严酷颇有奇怪的相似,与基督教传教士的接触(在此之前,“穷”与“坏”在中国的社会哲学中从来不曾被等而视之)反映在建立旨在面向穷人的公共机构,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实施持续、循环的阶段性教育。根据康有为的描述,他们都是真正意义上的“无家可归者”。使学生感到羞耻(愧、耻),在教育过程中被当作有效的惩罚手段,那些“不能在他们特殊训练的领域找到工作,并且在更低层次也难以就业”的学生被恐吓“否则将入恤贫院而为苦工,名誉全削,终身不齿于人类矣”。那些不止一次被送往那些机构的人必须穿着特殊服饰,“不体面的”衣服——这一惩罚来自儒家的描述,上古黄金时代,“服饰上的区别是惟一的惩罚手段”。被派往为穷人服务的机构的时间越长、次数越频繁,则那个人的劳动强度也就越大。因为“大同”世界已经将人从存在的焦虑中解脱,康有为发现存在其他的一些威胁,如麻痹与懒惰,将会在更大面积的人群中散播。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10)
319其他社会机构,如医院、老人院和休养院,尽管它们的设备与维护花费昂贵,但都将对所有人免费开放。它们是整个社会医疗保障的中心地带。因为每日的检查是强制性的,并且由于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医生就显得极为关键。他们的重要任务,包括指派不治之症者进入岛屿上的休养院,执行优生的任务(这里,同样有为患有严重遗传疾病的人提供性方面服务的专业人士)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原文为:“其有人欲者,听其报官,结男子互交之约可也,然是时有机器人以代之。”。在无望的情况下,他们(医生)甚至能够决定是否为患者通过“电椅”实施安乐死。老年人之家尤其豪华。即使在最低的阶层,甚至是为那些不曾为公共福利有所贡献的老人,他们都能够享受到带有公共浴室的两室一套的住房,并且配有适当的服务。而处于中等阶层的老人(他并未特别提及高等阶层),则能够享受到六室一套的住房。在这些措施中,尚能够发现儒家思想的因素;而在涉及火葬时,却并不能看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传统中为了表明孝行,在墓葬之外建立的一系列复杂礼仪,到康有为的公共机构中便留存为一套认真执行的默哀程序。通常死者将被火化,因为——除了实际操作的考虑之外——这样的方式最美,尸体将以此方式升入天国“人之生也自无之有者,亦自有之无,是全归于天也。”墓地与墓碑,及其随个人特点而大小不一的铭牌,属于那些生前曾有杰出事业的人事。一般来讲,默哀与对死者的安葬的过程应当尽量简短,避免打扰“大同世界”中洋溢的欢乐气氛。以对死者一生的回忆代替悲伤。火葬还另有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只能由古老中国的历史编纂者以“传统”来解释。他们不仅仅是简单地处理死者,而且还要为死者树碑立传,借此向死者的后代记录他们祖先的足迹。
以康有为的观点,世界政府对家庭的替代作用,还在于假象的对于第六界——在人与快乐之间的障碍(生命力障碍)——的克服。根据这个概念,他经常提及社会的阶级结构和它的经济基础。尽管,他经常重复提到的中国作家梁启超——他的学生和追随者——向读者保证《大同书》讨论这一问题并非因为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然有部分章节可以清楚的表明,康有为的部分知识来自马克思,尽管它们或许显得粗略(惟有苏格拉底和马克思两位西方思想家,康有为直接提到他们的姓名)。320这一章节中包含了对工业社会中社会进步的描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并且对尚未成熟的共产主义萌芽提出了警告,认为它不应先于国家与家庭的消亡出现:“农人之得均养也。或亦能倡共产之法而有家有国,自私方甚……以此制度而欲行共产之说,犹往南而北其辙也,无论法国革命不能行之,即美国至今亦万不能行也。”
然而,他的计划与共产党宣言却有着相同的目标,尽管它们更为细节化,而且最大的区别在于它许诺大同世界的实现完全是出于自愿,而非共产主义需要依托世界性的革命。在“大同”世界中,所有土地、工厂、银行以及商业企业都将成为公共财产。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逐渐过渡,将相应地产生“改良”和“简朴”的退化。因为一些集团将再也享受不到经济特权,阶级差异将就此消隐。并且,随着私有财产概念的消失,剥削最终也将失去它的基础。
在详细阐述他的这些理念时,康有为必须再次面对他在讨论为穷人服务的公共机构时曾经涉及的难题:人类的惰性。的确,在他的书中有一段文字,他曾经激烈地与那些“唯恐天下不乱,趁竞争之机引发骚动”的人进行辩论。他谴责那些人,因为他们相信“以为竞争则进,不争则退”,并且说“然则主竞争之说者,知天而不知人”。但是,在此之外他并不能再进行有效的回应,用了超过五十页的长度,他问自己到了“大同社会”,如果“那里一切都来自公共政府,如果没有竞争,又怎么会有进步,怎么能有发展?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们坐视这种退化和堕落,我们面临的同样会是严峻的挑战”。康有为对这种潜在危险的补救,仍然是借助个体的荣誉感和羞耻心——儒家思想体系中重视的技巧——作为使人感到不快的惩罚。为此他设计了一系列复杂的荣誉名称、奖励和饰物,以维持社会对“智”与“仁”的追求。由于在选拔的官员当中仍然存在等级的不同,康有为并未忽视,所有的荣誉以及官员所能得到的物质利益,会再次造成一个阶级社会。尤其是因为医生的职业,使得他害怕这种进步。由于它充满了对人的爱,“大同”世界,用康有为的话说,还可以被称为“医世界”。他怀着某种不安地考虑了建立“医师宗教”或“医师党派”的可能性,以此疗治整个社会的混乱——这个看似荒谬的想法,在我们考虑到孙逸仙这位“中华民国之父”后变得可以理解。孙逸仙和他主持的“共和”事业,并未引起晚年的康有为的注意。但我们都了解,孙逸仙开始是一名医生,在随后的岁月中,他将他的治疗施于整个中国社会。在康有为看来,如果一个受到广泛尊敬的“智者”被尊为宗教领袖,将是十分危险的事。只有最为谨慎的、同时考虑到个人性格与个人经历的选拔,才能够避免那样的危险出现(在历史人物中,他将老子、路德和哥伦布当作探索者,而把俾斯麦视为强盗)。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11)
321第七层,行政界。他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保障机制。这里,便涉及了他当时所处时代法律上的不公平。在这一章节中,康有为首先告诉读者,所有法律,在“大同社会”实现之后,都将成为多余。在所有这些他认为通常不必要的法律之中,他提及了对性侵犯的所有惩罚。在颇具反讽地论证,经过长期坚守宗教中的无数性制裁之后,所有男人将就此绝种之后,他要求成人有包括同性恋在内的完全性自由。他反对鸡奸,认为这是极度压抑后的变态行为。至于自然界中不涉及性的犯罪行为,康有为相信这些犯罪在“大同世界”中会随着国家、家庭、阶级和私有财产一起消失。他同样考虑到一些不甚明显的轻的罪行,如工作中的疏忽、缺乏礼数和制造谣言,他相信这些行为在进行耐心教育后会逐渐消失:“故太平之世无讼,大同之世刑措,盖人人盾有士君子之行,不待理矣。故太平之世不立利,但有各职业之规则,有失职犯规而无干刑犯律也。”
然而“大同世界”并非完全没有它的秩序。正如汉高祖刘邦,汉代的开国之军,在公元209年战胜秦军后有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者抵罪)——这种做法被视为在乱世中重整纲纪之举——一样,康有为同样设立了四条基本禁令,作为所有律法停止运行后规范行为的惟一法典,其中主要内容在之前的章节中已有涉及:第一禁懒惰;第二禁独尊;第三禁竞争;第四禁堕胎。关于最后一点,他在“人本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