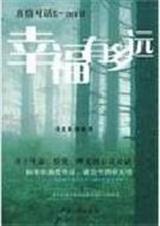中国人的幸福观-第6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人类历史中,存在着阶级的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无论在奴隶社会也好,封建社会也好,资本主义社会也好,互相矛盾着的两阶级,长期地并存于一个社会中,它们互相斗争着,但要待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认识这种情形,极为重要。它使我们懂得,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列宁说:“对抗和矛盾断然不同。在社会主义下,对抗消灭了,矛盾存在着。”这就是说,对抗只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处套用这个公式。
397如果想要了解理想的幸福社会在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中的位置,重要的是首先明确毛泽东关于实践与认识、普遍存在的矛盾与运动等等这些的基本概念。因为奇怪的是,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要求,能够导致它们自己被表述为矛盾辨证的两个方面。辩证结构的基本前提或者被排除,或者保持它们各自的性质。它们可以继续被当作目标,尽管意识完全先于实践,之前不流血的幻想,仍然能够与耻辱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毛泽东,恩格斯(如我们之前所讲,他的思想与毛泽东最为接近)也曾非常适当的描述过这种状态: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这里只限于考察康德以来的哲学运动中的这个结束阶段)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在于黑格尔哲学永远结束了那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一切看法。……现在,真理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科学从知识的低级阶段上升到较高的阶段,越升越高,但是科学永远不会达到这样一点,即它在发现了某种所谓绝对真理以后,就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以为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的状态就算是达到了尽善尽美;十全十美的“社会”,十全十美的“国家”,——这都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凡在历史上彼此更替的一切社会秩序,都不过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而已。……辩证法哲学认为一切和任何事务中都有着不可避免的灭亡的印迹;在它看来,除了不断发生和消灭的过程,除了无穷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上升过程以外,没有任何东西是永存的。……它的革命性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法哲学所承认的惟一绝对的东西。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他并没有在任何地方清晰地强调过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社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注释间接地了解他这方面的思想。1949年,他做了名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说。此时,抗日战争和与国民党的战争已经结束,他在全中国确立了实际的权力,而他的追随者则希望能够获得“千年帝国”的和平与平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在此处被两次提到,而每次提到时,都被相似的表述为“实现大同”。但其中的一次,它被提到是“人类发展的长期过程”,而第二次,并没有提及它在现时段实现的可能。
然而,更主要是因为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地点,永远处于变换的过程,以满足理想世界所需的特殊表现。正如同绝对真理只在“认识的过程中”得到表现一样,理想世界也只能在不断革命、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切实实现,这才是“惟一的真理”。但是,这是在所有现象(包括社会)的矛盾中持续不断的运动,并由此在这个过程中它能够被不断的认识。幸福在两个方面,变得难以企及。它只有在飞行的过程中(如革命运动)才能够被抓到。它经常逃跑,要得到它,就必须不断翻新。由无限的伟大生出的无限天空和天堂,被由无限的锁链、渺小以及狂喜组成的无限大地所替代。在这个大地中,矛盾、冲突和惊险将一次又一次的被经历。幸福与理想的尺度是“今”所代表的当下而非“某时”,无论这个“某时”指向遥远的过去还是遥远的将来。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6)
398“今”这个概念已经被李大钊发现并且详尽阐述。正是这个概念,在1927—1949年这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中,它曾经无数次安慰了几乎被广阔无垠的农村吞没的那些在寒冷、饥饿之中处于无家状态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员。而也正是这种无家状态,他们的战术中增强了更多的灵活、力量和自由。许多游击队所取得的无数小的胜利,甚至是他们的许多小失败,都能够被解释为走向新胜利的阶段性成果,并不断地带来新的快乐。部队被消灭,带来的并不是无边的阴沉的绝望,而相反是对战事发展结果和前途的好奇和期望。而且,游击队员们非正常状态的生存条件,也迫使他们不断切身进行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认识实践活动。他们所有人,包括许多领导者,都同时既是农民,又是战士,又是理论家,甚至有时还是科学家。一名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访问过延安的写过“从天空……到处都能够看到那些强盗的巢穴……”的美国记者这样写道:“他们散发着自信,言谈中总透着些假装神圣的味道。你有时会感觉这里像个宗教夏令营,人们互相拍着对方的脊背,表示友好。”这个总部设在盛开花朵、隐蔽群山中的苏维埃政权,使另一位来自国外的访问者感觉像是来到了诗人陶潜笔下的“桃花源”。当然,这种感觉应当归功于他们所在地界的原始自然状态和游击队力量的不断增强。生活在农村与自然之中,在洁净的空气与茫茫群山之中,这种居住在乡间的传统生存方式,倒更像是生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它的高级阶段,但无疑,它仍然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有相似之处。这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在1937年大胆宣称的那样:“这种根据科学认识而定下来的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到达了一个历史的时节——自有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重大时节,这就是整个儿地推翻世界和中国的黑暗面,把它们转变过来成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这同时也能够解释1949年胜利后,为什么当他的绝大多数追随者都认为那已经是决定性的胜利时,他仍然会告诫,尽管他们已经取得了成就,但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大跃进”与“大讨论”
胜利使得中国接近了城市和工业化。但是,它同样带来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曾经由于当时情况紧急而几乎被忘却:如产业工人和农民在革命年代的角色问题,在“机械主义”与“激进主义”之间道路的选择问题,这些问题随着胜利的取得再次浮出水面。尽管这看上去有些荒谬,但是,胜利危及到了胜利者的意识形态位置。因为在许多批评者眼中,毛泽东的思想或许足以控制农村,但是他的那一套在和平年代却未必适用;他的《矛盾论》,在和平年代不仅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甚至已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可能。是那些共产党员(尽管或许有些类似陈独秀的倾向),而不是那些虚伪的儒家思想者或者反革命分子,无意间表现得更像毛泽东的敌人,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在艰苦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农村,但在胜利已经取得的情况下,并不希望延长受到长期称赞的“持久战”。在20世纪50年代,一种来自儒家的,但对于这个广阔复杂的国家却也比较适用的古谚“可以马上打天下,却不可马上治天下”逐渐盛行开来,并在人们心中占据越来越大的分量。在许多明显的场合,它甚至改变了人们精神上的气氛,以至于昔日的主要英雄又重新受到人们的尊崇,而其他一些不合时宜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革命胜利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无数次出现——也遍布中国。几乎是完全放弃了自己曾经的安全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毛泽东准备开始一场“大跃进”,而从别的角度看,这场“大跃进”实在不啻为一场疯狂的“大倒退”。整个运动,不仅仅无谓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经历,甚至使得原来取得的一些成就遭到破坏。
然而,人们或许还会认为这个决定——它诚然是一种自我破坏——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无论毛泽东做出这样的决定主要是源于他自作主张的欲望,还是他忠于其他我们不得而知的理念,这些都已经并不重要。能够肯定的是,他既没有证明他在《矛盾论》中所阐述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正确,也没有能够将之付诸实践。在1957年2月,毛泽东做了关于建议“大跃进”开始的演讲。这个运动开始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结束于人民公社的建立。他的文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被理解作对早期更基本的文章更为准确的重申。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他对于意识形态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贡献,并且同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这篇文章的本质主题,同样引发了开始于1966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同的矛盾,通过相同的道路达到极点,经过“相对平和”的一段时期,将不会再消亡。直到这个时候,其整体经过了八九年的发展时间,而节奏又经常会被无数小的矛盾发展打断。毛泽东希望在他这篇演说中强调的,是一个被大家熟悉却又忽略掉了的主题: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也并不意味着矛盾的彻底消亡,无论这种矛盾存在于社会主义内部“人民群众”之间,还是其他一些地方。不仅如此,它们还会引发敌对势力的矛盾,在革命之后不断引发新的革命: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7)
400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的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有可能发生对抗。……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之间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不懂得在不断的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至少在表面上,“大跃进”在失败中落幕。毛泽东所希望的“在人民内部,遵循‘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民主地解决矛盾”遭到了来自知识界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很快就被结束了。而人民公社运动,这个曾经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并且使许多旧派人士感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他们所企盼的“大同”时代的到来)的运动,最终也不得不因为经济上的原因而宣告停止。声名狼藉的“大炼钢铁”运动最终也没有摆脱同样的命运。而这个以数百万记的小煤炉冶炼钢铁的运动,几乎可以被视为人第一次在没有灵魂的机器面前,对于自身伟大性的宣示。在意识形态方面同样也出现了问题,与莫斯科关系的破裂,造成了更多实际的压力。在1958—1959年之间,针对毛泽东为“大跃进”和“革命发展阶段”理论提供支持的“不断革命”理论,如何能够解决中国共产主义长久以来的困境,发表了无数文章。两种看似矛盾的发展成了这个时代的主题。其一,是毛明显地与人民大众产生了距离,与之相连的,是对他个人崇拜(尤其是在军队)的不断增强。401其二,是与此同时,享有声望的共产主义者对“不断革命”理论及其所造成的危害以及它顽固的领导,进行的有限的警告和批评。这些人是共产党内知识阶层的代表,他们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曾经在“大跃进”的第一阶段被要求广泛表达他们的观点。曾经被我们反复提及的哲学家侯外庐便是其中一员。经其一生,尤其是在1949年以后,他都致力于对传统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阐释,并且作为一名毫无争议的学者,他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传入工作方面,做了明显的贡献。他的著作《中国历代大同理想》出书于1959年,讨论了从儒家“大同”思想到他的那个当下时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乌托邦思想,并且包含了若干章节,可以被视为对实现这种乌托邦思想所做匆忙尝试进行评判的文字。当侯外庐在1966年底,文化大革命最高潮时期受到批判时,这些危险的言论并没有被特别提出,这或许是因为担心批判反而会产生相反的效果。但他却因为写过一本“恶意诋毁人民社会的黑书”而受到责难。认为他在书中引用了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如邓牧与鲍敬言)对古代暴君的批评,实际上是在诋毁毛泽东本人。
在这一点上攻击侯外庐,或多或少有些不公平。而对当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长期担任《北京日报》主编的邓拓(生于1911年),这个有着更为清晰的政治人格的人的批判,则显得更加似是而非。在1961…1962年之间,他在《北京晚报》以“燕山夜话”为标题,发表了系列连载散文。这些散文,多从古代掌故中寻找故事和事例,经过巧妙编排,指涉现实。因此,这些文章初看去好像是一些文学化的调侃,但仔细深究,往往又能发现含有确实的政治意见。其中最具战斗力的,是一篇名为《伟大的空话》(Great empty talk)的散文。这篇文章批评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式的文风。这种文风继承着明清科举取士“八股文”的形式外表,但却往往不能表现确实的思想内涵:
402有的人擅长于说话,可以在任何场合,嘴里说个不停,真好比悬河之口,滔滔不绝。但是,听完他说的话以后,稍一回想,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说了半天还不知所云,越解释越糊涂,或者等于没有解释。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不能否认,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到处搬弄,甚至于以此为专长,那就相当可怕了。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那就更糟糕了。因此,遇到这样的事情,就必须加以劝阻。……凑巧的很,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编写了许多“伟大的空话”,……不久以前,他写了一首《野草颂》,通篇都是空话。他写的是:老天是我们的父亲,/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太阳是我们的保姆,/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这首诗尽管也有天地、父母、太阳、保姆、东风、西风、恩人、敌人等等引人注目的字眼,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变成了陈词滥调。……因此,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多读,多想,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18)
邓拓担心,如果这种愚蠢的、机械的对概念重复的积习延续下去,其危险的趋势将导致整个国家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