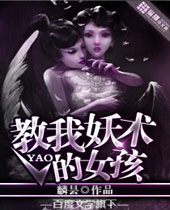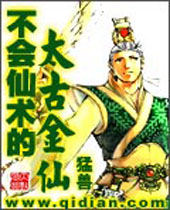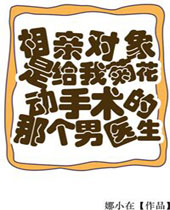深艳:艺术的张爱玲-第6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品了。我等不及地想看这个‘注定了要被遗忘的泪与笑’的idyll如何搬上银幕。张女士也是《不了情》影剧的编者;她还写有厚厚的一册小说集,即名《传奇》!但是我在忧虑,她将成为我们这个年代最优秀的highedy作家中的一人。”
本来张爱玲这朵“奇花”也许可以安静地绽放,可被剧坛前辈这么一喝彩,就招致是非了,应了“爱之足以害之”的话,竟至引起一场论争,而且站在反面的是多数。激愤的,把张爱玲连同洪深骂得狗血喷头:
“寂寞的文坛上,我们突然听到歇斯底里的绝叫,原来有人在敌伪时期的行尸走肉上闻到highedy的芳香!……难道我们有光荣历史的艺园竟荒芜到如此地步,只有这样的highedy才是值得剧坛前辈疯狂喝彩的奇花吗?”
这篇文章发表时,《太太万岁》尚未公映,文章当然不是影评,而是人评。一旦评人,张爱玲在敌伪时期的一节自然又成话柄,连累得说她两句作品好话的洪深都几乎变成坏人了,尽管洪深在“敌伪时期”是抗日救亡演剧活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
自日本投降后,张爱玲就一直处于挨骂的状态,她虽然识时务地不作回应,但并非真的毁誉由人、完全置身事外,所以她借1946年11月出版《传奇》增订本的机会,写了篇《有几句话同读者说》的序言以辩白。而辩白斤斤于枝叶,显得无力,并不足以澄清一切。也许就是因此吃堑长智,当她面对人们由《太太万岁》而生的批评甚至诟詈时,便彻底地一仍其贯,再不做任何回应。而《太太万岁》的热映,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也多少遮蔽甚至淹没了那些反面的声音,而她是最看重读者与观众的。
就像歌德由《少年维特之烦恼》得到了解脱,张爱玲也似乎从《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中寻求了解脱,张爱玲的心空有点放晴了。也是自尊心被伤透了,如同她4年前在《洋人看京戏及其他》一文中写到的:“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这时的她也似乎会想到要像她所理解的高更名画《永远不再》中的那位塔希提女子那样,在“永远不再”之后,心里只留下“没有一点渣滓的悲哀,因为明净,是心平气和的”。于是她将这两部电影剧本的稿酬共三十万块法币,附在信里寄给了胡兰成,与他断然分手。
1948年的张爱玲显然心情好起来了,桑弧、龚之方等人成了她公寓里的常客,与胡兰成分手时自称从此“将只是萎谢了”的她,这时在龚之方的印象里,竟变成了一个合群的、“喜欢与人聊天”、“对朋友的态度热情”的张爱玲,又恢复为那个听到好笑的故事会张口大笑的张爱玲了。在《太太万岁》大获成功之后,桑弧又与张爱玲商量,打算将她的长篇小说《金锁记》搬上银幕,张爱玲自然欣然从命。《金锁记》的故事与《倾城之恋》一样,在张爱玲也是“烂熟的”,何况她又有了编《不了情》与《太太万岁》的经验,故而也一蹴而就,但变成电影不顺利。物色主角曹七巧的扮演者颇费了一番周折,先是遍寻不着,后来看中了张瑞芳,可张瑞芳以肺结核并发结核性腹膜炎正卧床疗养而辞演。那时的社会正处于翻天覆地的前夜,该剧以不合时代洪流等原因,终告无果。
《金锁记》计划的搁浅,并没有影响张桑二人的继续合作。桑弧本来就是一个不仅能“拍”而且善“写”的导演。早在1935年,他就在周信芳与朱石麟两位艺术家的提携下尝试文艺写作,在拍《不了情》之前,就创作有《灵与肉》、《洞房花烛夜》、《人约黄昏后》、《教师万岁》、《人海双珠》等电影剧本;在《不了情》与《太太万岁》之间,他还编了剧本《假凤虚凰》(由黄佐临导演拍成电影后,也引发了一场社会风波)。所以张桑二人的合作能够成功,至少部分原因是桑弧懂得写作,彼此容易沟通与理解。
张桑的再次合作是电影《哀乐中年》,可是拍是桑弧拍的,写也是桑弧写的,张爱玲只是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其间,拿了些剧本费,但影片上不具名。“哀乐中年”的名字有可能是张爱玲起的,她在《〈太太万岁〉题记》中有言:“所谓‘哀乐中年’,大概那意思就是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丝辛酸,他们的悲哀也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而“太太万岁”的名字也可能是张爱玲受了桑弧“教师万岁”的启发,虽然后者是歌颂教师的正剧,前者则是调侃太太的喜剧,此“万岁”非彼“万岁”。
当时桑弧尚未娶妻,眼见他与张爱玲屡番默契的合作及合作的成功,上海小报开始制造新闻了,桑弧周围的朋友也在想:“张爱玲与桑弧不是天生的一对吗?”可是大家都知道桑弧是个内向、拘谨的人,虽然因了编剧本拍电影的事与张爱玲交往频繁,但在一起也只谈“正事”,不扯私情,所以他两人要好,必先取得张爱玲首肯。龚之方于是有天自告奋勇,抱着成人之美之心去见张爱玲,婉陈来意。张爱玲的回答如同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比《不了情》里的任何镜头都更催人泪下。龚之方在事过50年后回忆道:“她的回答不是语言,只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再说下去了。”
龚之方此番前去“提亲”,实在是莽撞有余,而了解情况不够。对张爱玲,他是连她与胡兰成的事都不大清楚,张爱玲此时是否心伤已愈,是否冷心复苏也不晓得。而桑弧那边也有障碍——桑弧十多岁时父母俱丧,是由大哥抚养大的,因此很听大哥的话。而大哥觉得写作不是一个稳当的职业,同时也可能听说了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以往,故而不同意。
《十八春》(1)
《哀乐中年》上映不久,上海就解放了,张爱玲在大陆的电影创作也就此告终,蜇伏了差不多10个月后,她才又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十八春》,总是与声名之累不无关系,连署名都改用了笔名“梁京”。
《十八春》共23万字,写的是一对要好的同学沈世钧和许叔惠。叔惠先毕业进了一家工厂,等世钧毕业时便介绍他到这家工厂来实习。春节假期他俩在一家饭铺与同事顾曼桢小姐邂逅,慢慢地,世钧与曼桢成为一对恋人。曼桢14岁丧父,一家大小生活的重担便落在她姐姐曼璐肩上,曼璐做了舞女,又“蜕变为一个二路交际花”,后来嫁给了一个乡下有老婆的客人祝鸿才。祝鸿才在交易所里做事,投机发了财后便不安于家。曼璐想用孩子拴住他,可她自己不能生,又看见祝鸿才对二妹曼桢有意,便佯称生病,叫曼桢到她家里来照顾她,使祝鸿才有机会在一天夜里强奸了曼桢,并且随即将曼桢囚禁起来,一边又借助曼桢与世钧的误会拆散了他俩。曼桢由受辱而怀孕,在医院分娩后,在邻床产妇的帮助下只身逃出了曼璐的控制,待她打听到世钧的消息,却得知他已经结婚了。后来曼璐得肠痨死了,之前半月她来找曼桢,希望她为了孩子嫁给祝鸿才,被曼桢拒绝。但曼桢却也在母性的作用下,心里总放不下那孩子。有回孩子得了腥红热,曼桢忍不住到鸿才的家里去照顾小孩,这样就又与鸿才见面了。鸿才在她面前表现得颇拘谨,曼璐曾经一再对她说过的话占了上风,曼璐说,鸿才始终是非常敬爱曼桢的,甚至那夜的犯罪也是在爱她爱得太厉害而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发生的。曼桢又想到孩子,于是嫁给了鸿才。婚后感情当然不会好,后来又离婚了。等到曼桢与世钧再次见面,已是在他们初次相识后的十八年了。他俩坐在一个广东小吃店里,倾诉遭遇,互诉衷肠,终于明白了彼此的心迹,虽然已经迟了,但两人还是得到了“一种凄凉的满足”。
在《十八春》开始连载的前一天,桑弧用笔名“叔红”(《十八春》里有个叔惠,桑弧却用叔红,像是兄弟俩或兄妹俩)在《亦报》上写了篇《推荐梁京的小说》,篇幅不长而内容不薄,不妨照录于此:
一向喜欢读梁京的小说和散文,但最近几年中,却没有看见他写东西。我知道他并没有放弃写作的意念,也许他觉得以前写得太多了,好像一个跋涉山路的人,他是需要在半山的凉亭里歇一歇脚,喝一口水,在石条凳上躺一会。一方面可以整顿疲惫的身心,一方面也给自己一个回顾和思索的机会。
梁京不但具有卓越的才华,他的写作态度的一丝不苟,也是不可多得的。在风格上,他的小说和散文都有他独特的面目。他即使描写人生最暗淡的场面,也仍使读者感觉他所用的是明艳的油彩。因此也有他的缺点,就是有时觉得他的文采过分秾丽了。这虽然和堆砌不同,但笔端太绚烂了,容易使读者沉溺在他所创造的光与色之中,而滋生疲倦的感觉。梁京自己也明白这一点,并且为此苦恼着。
就一个文学工作者说,某一时期的停顿写作是有益的,这会影响其作风的转变。我读梁京新近所写的《十八春》,仿佛觉得他是在变了。我觉得他仍保持原有的明艳的色调。同时,在思想感情上,他也显出比从前沉着而安稳,这是他的可喜进步。
我虔诚地向《亦报》的读者推荐《十八春》,并且为梁京庆贺他的创作生活的再出发。
“一向喜欢读梁京”,透露了作者与梁京即便不是多年的朋友至少也是长期“私淑”;“并且为此苦恼着”,既是可以诉苦的朋友,自然不在泛泛之列;张爱玲停笔未必是她自身的原因,而桑弧说她“并没有放弃……”,“也许……”云云,其中更多可见对她的爱护与安慰;《十八春》虽然是边写边载的,但也不至于每天只写一天刊载的量,尤其是最初,想必是写了相当部分,所以桑弧才能得以先读。当然也很可能桑弧的“读”用的是耳朵——听张爱玲谈《十八春》的构思,由此也可见两人的关系。
畅销书作家徐訏1943…1944年间,在《扫荡报》上连载中美日三方谍报斗争于上海孤岛题材的长篇小说《风萧萧》时,重庆渡江轮渡上,几乎人手一纸。相比之下,《十八春》的畅销情形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张爱玲深谙读者心理,早在抗战后期所写的一篇散文《论写作》中对此就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其中秘诀之一是“说人家要听的”,而读者要听的并非越秽亵越好,也非香艳热情的,“而是那温婉、感伤,小市民道德的爱情故事”。《十八春》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中国读者可能是因为普遍文化偏低的缘故而使得理性较差,往往分不清戏里戏外,一部《红楼梦》,就不知有多少人以林黛玉自怜,以贾宝玉自况;也有女读者哭着找上张爱玲的门去,说曼桢的故事写的就是她的经历。而“有文化”之如周作人虽然也把《十八春》读得入心入脑,在他的散文中屡屡提及,可是他却不入迷,他说:“我看《十八春》对于曼桢却不怎么关情,因为我知道那是假的。”
可是无数读者读《十八春》读得如醉如痴,对于小说人物也就真假不辨了。当读到曼桢被姐夫污辱之后,大家无不义愤填膺,一方面为曼桢一掬同情之泪,一方面狠命诅咒曼璐和鸿才。甚至有很多读者写信给张爱玲,认为非把这一对狗男女枪毙不可,同时也吁请作者不要让曼桢的悲剧再发展下去。
那时《十八春》已在报上连载了将近半年。有天桑弧去见张爱玲,张爱玲指着桌上的一些读者来信对他说,她没有想到读者竟这样关心她小说里人物的遭遇。这使她高兴,但也使她惶恐,因为她担心人们对她有一种误解,以为她故意把曼桢陷入最悲惨的境遇,用廉价的手法骗取好心肠的读者的眼泪。桑弧道:“一般读者似乎对曼璐更比对祝鸿才来得憎恨,因为鸿才的卑鄙无耻原在意中,然而人们对于曼璐的陷害同胞的曼桢,总觉得毒辣过分,不知你自己以为如何?”张爱玲道:如果读者读到曼桢被辱的一章而有一种突兀或不近人情的感觉,那是她写作技术上的失败。但是她仍要说,曼璐这一典型,并不是她凭空虚构的鬼怪。与其说曼璐居心可诛,毋宁说她也是一个旧社会的牺牲者。她自己不懂得劳动,她在风尘中拣上了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一旦色衰爱弛,求生的本能逼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了曼桢,希望藉此拴住鸿才的心。当然,曼璐为了慕瑾,对曼桢也有一些误会和负气的成分。但曼璐陷害曼桢,最主要的理由还是应该从社会的或经济的根源去探索的。这并不是说曼璐的行径是可以宽恕的,但旧社会既然蕴藏着产生曼璐这样人物的条件,因此最应该诅咒的还是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桑弧在《亦报》上将与张爱玲所谈的这些话发表出来,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我要泄漏一个‘天机’,就是曼桢最后的结局并不是很悲惨的。事实上,不但读者希望她坚强地活下去,作者也没有权利使一个纯良的女性在十八年后的今天的新社会里继续受难。”
《十八春》果然有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原因自然是读者有此愿望、作者无彼权利,而桑弧文中已经提到的“新社会”对曼桢“继续受难”的不允许,恐怕才是更重要的缘故。
《十八春》(2)
张爱玲写《十八春》时年龄已经三十出头,桑弧比她还大四岁,想必他家里早就劝他成婚了,尤其是在得知他有与张爱玲好的危险的情况下,催促得可能会更紧吧?张爱玲的作品向来不是近乎谶语就是折射她的现实生活,《十八春》说的其实就是一个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故事,尽管书中人物命运与她和桑弧的缘故不同。《十八春》连载完了,她与他的友情也定了格——就在这一年,桑弧与一位圈外女士戴琪结了婚。后来张爱玲又在《亦报》上连载长篇小说《小艾》,就再也不见桑弧的评介文章了。1952年7月,张爱玲离开上海,往香港去了。从此他俩再也没有见过面。
1995年3月,桑弧在《当代电影》杂志上连载回忆录《回顾我的从影道路》,其中写到他拍《不了情》、《太太万岁》及《哀乐中年》,前两部片子只提及影片是张爱玲编剧,后一部片子只字未提张爱玲曾参与剧本,对两人在几部片子编导过程中的合作与切磋情形也不着一字,倒是顾左右而言他,对如何选黄佐临女儿作小演员等津津乐道。
桑弧如此,也未必是对张爱玲一点不记前情,而以他的年龄、性格、经历、家庭及社会处境,倒很有可能是有意避嫌,也不愿再有任何风波,更对媒体或好事者炒作他与张爱玲有一种深深的防范。
在回忆录末尾,桑弧特地提出相濡以沫的夫人,向夫人40年来对他事业的支持及生活的鼓励表示深深地感激。可见他夫妻感情很好,也证明桑弧是个好丈夫。从张爱玲所选的两任丈夫来看,都不是桑弧型的,胡兰成不必说了,赖雅早年也是一位玩家,张爱玲择偶倒是符合“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模式,所以单由此来看,张爱玲未与桑弧恋爱也不奇怪。
就在桑弧的回忆录连载到第三期的时候,大洋彼岸传来张爱玲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曾否在桑弧心中荡起涟漪,他曾否午夜梦回,无人知晓;桑弧回忆录的第一期里就写到了张爱玲,尽管是一笔带过。张爱玲要是消息灵通,从时间上来讲,是可以读得到的,只是读到读不到,借用她在《十八春》里写曼桢与世钧重逢时的一句话:“也没有多大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