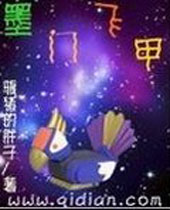[龙门飞甲]鬼雨惊飞-第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漫天大雪渐渐覆盖了整片京城,白茫茫一片看不清道路。
拾芳华
雨化田回到灵济宫后有整整一天没有出门,晨始盘坐在蒲团上闭眼念诵楞严经,素面单衣乌发披散,任谁都难以将这样一个人和平日霸道冷酷的西缉事厂掌印督主联系起来。
屋中暖炉烧得鼎盛,马进良在旁不时添熏香,屋外漫天飘雪,端的是两个世界。
他细听雨化田诵经,那人声音轻柔沉稳,潺潺似山间溪流,再加上眼前人天生一副仙人姿,不觉听得痴了,脱口一句:“督主冷雪之日诵经,无待外物卓尔不群好比魏晋名士。”
雨化田蓦地睁眼,挥手将案卷上的镇纸拍飞向马进良的兽面,稳稳打个正着,镇纸落地碎裂,马进良的脸也被震得生疼,就当掴过掌了。
“魏晋名士……我也想服那五石散逍遥放纵,你代我去平了梁春锦和薛檀?”
他现在心绪极为烦闷,赵通所说没错,雨化田的确有些着急了。
马进良被掴掌,倒觉得自己一时失言惹雨化田生气是好事,若督主还是像平时冷若冰霜毫无波澜,心里藏多少烦忧岂是一个万贵妃就能诉完的?
上位者都是凡人,雨化田也不例外。
他自小被俘净身入宫,多少人情世故看淡养成现在的冷傲脾气,万喻楼在他小时候用鞭子抽过他,现在见了面也要称一声“雨公”,他面上笑着回应,心里时不时就在盘算怎么把这老东西除掉自己才能前路光明。
现在连梁春锦都来阻他的路,即便早知官场险恶、自己也身在其中明争暗斗了许多年,但是雨化田的心仍旧免不了又冷下去几分。
十几岁还在宫里摸爬滚打天天被人使唤的时候,也是如现在这样的雪天,雨化田给宫里一位妃子熬药时觉得药炉旁十分温暖,便不觉打起瞌睡,等到睁眼,罐里的药汁早已烧干。他误了妃子吃药,被罚去雪地里跪,身上宫服单薄冻得毫无知觉,他一边怕是不是要被发去浣衣局老死、一边浑身打筛,恰好身旁一群散了宴席的世家子弟经过,少年们见到宫人被罚不是当笑话鄙薄几句就是笑闹着路过,唯有一人停下了脚步,将自己身上的披风解下给他披上。
雨化田从此记了梁春锦的好,日后跟了万贵妃也没忘梁春锦,每逢年节宫里宴请群臣时他都记得给梁春锦送些平时自己被赏的小玩意,世家子弟虽然看不上这些但每次都和颜悦色收好了,雨化田日渐冷去的心中因为这人总藏着些偏僻的温暖。
有一年宴席见到梁春锦,那人喝了点酒,宫灯映得他脸色微红,笑起来十分好看。雨化田给他斟酒突然被执住了手,梁春锦盯着他的眉眼轮廓忽然说:“我从前就觉得……你长得真像檀儿。”
他口中叫得肉麻的“檀儿”就是薛檀,彼时也不过是宫中的一名小太监,因为容貌秀丽被一些王孙公子私下尝过滋味,有些见不得人的名声传得挺盛。
雨化田手一抖酒撒了,马上跪地请饶,抬头再看梁春锦的眼神已经变得冰冷无比。
古有云:茕茕白兔,东奔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雨化田自此却不再想什么故人,依旧重新一个人在宫里过活。
再过了许多年,他已记不清梁春锦少年时映着宫灯的笑容是什么样子了。
雨化田被马进良扰了清静便不再诵经,站起身走到案卷旁提笔挥毫,宣纸上现出一字:胡。
马进良扫了一眼笔走狂狷的字迹,即刻明白了雨化田的心思。
“进良,我平日只见你双剑精湛还未曾见过你的字,写一个来瞧。”他递笔给马进良,踱到香炉旁闭眼深吸香气。
马进良提笔,在“胡”字后面写下一个“蓝”字,呈给雨化田看。
雨化田看过字后嘴角弯起道:“我没错看你,”说罢伸手揭开马进良的面具,靠近他的面孔接着低语,每个字似是极尽蛊惑能事:“平信侯如若还不念旧情,我也没必要顾念什么仁义……圣上面前参他一本勾结朝廷重臣结党营私,进良以为……如何?”
“如何”二字甫一出口,痒痒地钻进马进良的耳畔,雨化田抚着他脸上的疤痕,冰冷的指尖不断撩拨人的心绪。
“那把削金断玉的匕首怎么都没见你用过?……嗯?”说着用指甲轻拈疤痕上的新肉,指腹顺着皮肤按上马进良的嘴唇。
马进良的呼吸开始急促,强抑不住忽地抱紧了雨化田腰身,将唇舌压上那人苍白的颈间去噬咬对方冰冷的肌肤,慌乱间不小心把雨化田弄疼了,留下红通通一片吻痕。
他喉间忽然被雨化田扼住,雨化田从马进良腰间摸了那把匕首,刀尖正对着他的左眼,若不是马进良让得快怕是连这只义眼都不保。
“伺候人都不会,蠢货。今日再碰我就剜了你这只眼。”
“属下僭越了,请督主治罪。”马进良被捏着喉间只得沙哑回话。
门口忽然有番子来报:“禀督主,有消息。”
雨化田冷睨一眼松了他的喉,裹上貂裘打开门。番子递来一张寸许小纸,雨化田展开看后又挥退番子关上门。
马进良不敢再造次,静听雨化田的命令。
“都是废物,找到帐目又被人截走了。”雨化田五指紧捏椅子扶手,竟捏碎了上好的木料。
他望着地上的宣纸看到“胡蓝”二字,忽然又展露笑容,只不过带着十成的阴恻。
“备轿,我要去趟平信侯府。”
宣纸被丢进炉中,烧成一捧艳红的火焰。
纱笼烟
雨化田出门的衣服极其麻烦,里三层外三层包了个严实,让他看上去威严又禁欲。马进良帮雨化田换层层叠叠的衣服时还在想自己方才为什么会迷了心思。
一定是那熏香的过错——宫里的香总归有些不清不楚的功用。
转念一想,把自己的错误归结给无生息的熏香又实在不讲道理,六祖惠能说过什么来着?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他站在雨化田身后,手中拿衣物绕过对方肩头、一层层小心披上,目光触到雨化田苍白的后颈,一指勾了衣襟,指甲又压到雨化田的锁骨,硬硬的硌住手指骨节。
雨化田余光睹见那只在逾越边缘的手指,眼波流转,发语却强硬:
“马进良!”
和当初遴选时喊出对方姓名时一般语调。
他转身面对戴好兽面的马进良,还未系好的繁复衣物自半边肩头层叠落下,露出最里的中衣,像未完全绽放的馥郁花瓣。
然后雨化田面对马进良,自己把衣物一件件重新拉上肩头、系好。雨化田盯人的眼光并非直直朝向,而是松散得像铺开的网,马进良一瞬觉得雨化田不再瞧他了,可一抬眼,视线织成的网又把他的心神全部收拢了去。
这下是怎么都怪不了熏香了。
马进良也不再避雨化田的眼神,他用阴阳瞳去瞧那人穿衣:每一件扣上的姿势都十分优雅。渐渐的,他刚刚留下的吻痕被厚厚的衣物遮住,稳稳当当藏在了雨化田的脖子上。
上位者都是很奇怪的,明明自己能把衣服穿得很好看,为什么还要别人帮忙?
雨化田明明可以自己穿好繁复的衣服、一点都不用人伺候,为什么还一直把他带在身边?
马进良开始感觉离雨化田太近的日子十分煎熬,他从前不是这样的。他的定力很好,好到万通都在别人面前称赞过他:百户的双剑是高手的剑,人前轻易不出鞘,出鞘必取命。
『高手总是寂寞。』江湖百晓生旁观马进良换眼时磕着瓜子感叹。孙圣手摘了他眼窝的腐肉,他用右眼费力去瞧闻名未见面的百晓生,那人穿着白花花的书生袍,布料上脏污点点,实在不符百晓生的传说名号。
说起来百晓生的模糊轮廓和雨化田倒是有几分相似。
可世上没有谁的白衣能穿得比雨化田更好看。
尤其是现在这身珍珠白的曳撒,配上雨化田冷峻的面容,极妙。
“走。”雨化田推开门,一阵风雪掠过,吹开了他的黑色披风。
马进良受了冷,突然想明白一件事。
督主的兴致来了,想与他戏弄,虽然比宫里不具名的香还要来得勾人,但万万不能用“勾引”一词。
雨化田刚才跟他在屋里干了什么?
只能用另一词:调戏。
西厂大档头马进良被厂公雨化田调戏了。
平信侯府的大门没有关,朱漆映着金色门钉,不知有何居心。
雨化田下轿后站在门前未进,马进良要为他撑伞被挥开,便收了伞一起陪雨化田在门口站着。
前些日子马进良以为自己稍许摸清了雨化田的底,现在看来,不过是自作聪明。
“你说他究竟安的什么心?”雨化田一句问话飘来。
马进良这段日子听惯了一声声叫得亲密的“进良”,一下子没有回过神,等到要回答时梁春锦撑伞出来接雨化田了。
“平信侯安好。”雨化田撒开黑色的袍子抖落一身风雪,脸上又恢复了他平时高深莫测、似笑非笑的表情。
“雨公安好。”梁春锦上来扶雨化田的肩,雨化田也没避让给他扶了,两人俱面上含笑,各怀心思地进了侯府。
梁春锦待雨化田落坐,看了眼一旁的马进良道:“要事密谈,闲杂人等退开。”
雨化田哼笑:“你先把梁上那几位君子撤了,我的人可不会爬房梁。”
梁春锦被驳,不过并未撤影卫。马进良提了一口气准备随时拔剑,屋子里看似他们三个其实暗线密布,有侯府的人也有西厂的人。
“雨公说笑,今次来找我所为何事?”
“你府中账本被盗一事。”
“这等小事就不劳烦雨公了。”
“平信侯不赏下官几分薄面?”
梁春锦只瞧住雨化田笑:“雨公还是如当年,意气用事,一激就起。”
马进良听着他们云山雾罩的对话,心里也跟着思想:梁春锦是雨化田故人,想必清楚几分雨化田的脾性,该是设了什么套子让督主钻。
可雨化田偏顺了对方的意,他不可能不清楚梁春锦下套,那便真应了梁春锦的话:一激就起。
“你只需说出贼人模样,我自会替你办好。”雨化田步步紧逼,似乎自有想法。
梁春锦倒也爽快,让人取出两幅画像:“这是我凭记忆命府上画师所作,雨公过目。”
马进良望那两幅画,笔法流畅线条清楚,丝毫没有含糊之处,再接着听梁春锦讲:“贼人夜闯侯府惊扰家眷,又盗取帐目,实在该死。”
雨化田递给马进良画像吩咐收好,又对梁春锦道:“我近日必定给平信侯交代。”
马进良心下又明白几分:夜闯侯府画像却能如此清楚,贼人也未曾蒙面,天下哪有这样的事?“贼人”不是梁春锦事先设好就是杜撰用来扰雨化田的绊子。
雨化田得到了想要的东西便利落起身道别,头也不回出了平信侯府。
马进良揣了那两幅画,一时参不出奥妙,于是紧跟着雨化田的步伐走了,提的那口气还蕴着,双剑暗响。
雨化田品了品刚才与梁春锦的话,神情淡漠下去。
“进良,你今日旁观了一出好戏。”
锦上花
两幅画像,一肥一瘦,一丑一俊,如果不是侯府的画师画工了得,就是那两个盗贼长得太过神气,贼眉鼠眼獐头鼠目之类的形容完全用不上,神情间竟有几成倨傲。
马进良点灯,雨化田长坐灯前,案几上放着那两张画,他用指尖一寸寸滑过画上的线条,仿佛自己执笔又重新描了一遍。马进良在旁观望,不知怎的,觉得有点痒。
那指甲尖搔过画卷,又像在搔马进良的心尖。
他跟雨化田,现在似乎是十分模糊又危险的关系。
然而现下胡思乱想这些,不是被迷住心窍就是不想活了。所以他擅做主张开口说话,为的是藏起自己的局促:
“督主,若还不尽快动手的话,薛檀怕是要更近一步……”
“东窗事发他就会销那百引私盐?他不会蠢到自绝财路,”雨化田抚平纸上的折痕,话语锋机一转,“我现在虽不顺,他也不好过。”
“为何督主不亲带人马去南京直接查他?”
马进良预想中雨化田听到这一问,接下来定会骂他蠢了。
雨化田轻笑,扫了马进良一眼:“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双剑装傻充愣也是一绝?”他的笑容融在明灭的灯火中,如雾端月貌,看不真切。
“属下不……”
马进良话未说完,雨化田便接上:“你什么都敢,我虽不是什么好人,你也善不到哪去。”
画卷被灯火照得泛黄,有了些经年已久的旧书韵味。
雨化田终于把画像卷好再次交还给马进良,又虚晃过对方的手挑起了马进良的下巴:“所以我才选你。”
他瞧着那只恐怖的眼瞳,又缓缓一句:“才发现进良的眼睫是白色的。”
那卷纸慢慢朝下移去几分,挑开马进良领口,雨化田的动作和刚才用指尖描线条一样若即若离,沿着领口空隙将纸卷塞进了马进良怀中。
画卷仍有一丝冰冷,贴着马进良胸口的皮肤。
跟雨化田单独相处而产生的危险感又多了许多。
“刚放出去的线,怎能在船停靠岸的几天就断了。”雨化田靠回座椅,又绕回刚才的话头。
马进良朝后退了一步,他跟雨化田之间的那层窗户纸捅破了一个小孔,两人对面窥视,互相能看出五六成的念想。
但除了兴致起来,有些不可言说的事又确实十分微妙。
“我已命谭鲁子和赵通盯紧了陆路,只需等着,自有分晓。”
“私盐帐目被截的事该如何办理?”马进良问雨化田,微微躬身,十分恭谨的仆从姿势。
“要账本?呵,要多少账本我都能给他写出来。”雨化田双眼微阖,指节叩上桌面。
“梁春锦跟我故布疑阵,你道侯府那两个贼人有什么名堂?他们‘盗’的,并非侯府的账本——”
马进良忽然明白,又听雨化田接着道:“——正是被截走的私盐帐目。”
“他自是明白我不会上他的当被他扰,却想出这种法子逼我,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
平信侯府上并无账本被盗,想必两个贼人也是梁春锦派出的人手用来干扰雨化田,梁春锦知道雨化田颇有些心高气傲,所以即使知道这是下套子,被激到了还是会派出人手清扫障碍,多多少少会耽搁到查薛檀的事。
至于“贼人”身上的私盐帐目真假,雨化田也不能肯定,不能肯定就无法置之不理,梁春锦倒是摸通了他多疑的毛病。
他现在内心藏着十成怒气,面上还是要端住,不能自乱阵脚。
“这两人就交由你去处理,活捉回来,我倒要见识见识是什么高手。”
马进良应诺,怀里的画卷带着屋内的熏香,那熏香跟雨化田的心思一样时隐时现,无法琢磨。
夜晚,赵通藏在通往城郊一条偏僻小路旁的山垛子上,他守了一天一夜,身体有些冷了。
谭鲁子的手下报信岸头有了动静,薛檀按捺几天后终于开始卸几百引私盐,时不时就有各色装扮的人到岸边推运小车,行踪十分分散,但是雨化田估计得没错,薛檀船队运的盐不是小数目,一时要入市贩卖完不是易事。他们必定有一队人要将大头运至储藏私盐的盐场,而查出盐场之前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赵通打了个哈欠缩缩肩膀,想到二档头手下把私盐帐目弄丢一事不禁又打了个哆嗦。希望回去的时候督主不要全部治罪。
远处有火光渐渐亮起,点点萤萤慢慢飘向城郊小路,赵通紧盯着那线火光,耳边的车马人声越来越清楚。
![[机甲]1.2歌后 作者:湛空(晋江vip2014-09-08完结)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