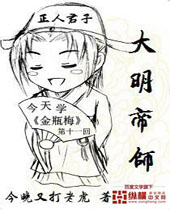帝师的掌心娇-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握住那竹签之后,她佯作不小心拨歪了签筒,翰林院的小侍从连忙上手搀扶。
“抱歉。”徐绮帮他一起接住签筒,顺势碰了碰他的手。
小侍从对上她的目光,摸到手中有了一张纸条。
徐绮眸光带着些厉色。
每年为了她能拿下翎朝宴的头名,祖父在翰林院上下打点关系,不知道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让所有翰林院试题的签子都在侧面做了微不可查的标记。
走到帝师面前的人必得是她,绝不能是旁人。
江念晚也迅速择了一签抽出来,瞧着签题倒不常见,是问刑赏之论的对策,不过她这段时日读的古今策论不少,也不至被难为住。
她不假思索,在纸上洋洋洒洒写起来。
徐绮见她并不犯难,微垂了眼眸下去,也在纸上写起来。
翎朝宴虽十分受朝野重视,但到底也不会真如科举那样严肃,策题一出也只做短论,以半个时辰为限,待考生写完之后各自宣读交流思想,而后由出题的众位官员评出最优。
今日天气不算好,风一直吹着,众人的宣纸都用砚石压着才不致被掀翻,眼见着就要到结束之时,徐绮佯装翻页,下面的草宣却被大风吹走。
“卷纸!”她惊呼一声。
翰林院的小侍从连忙去帮她拿回,可惜风吹得甚大,一路也不知打翻带过了什么,风沙四起,屏风这侧的女眷都纷纷拿帕子捂了脸。
待一切都安静下来之时,江念晚一睁眼,却瞧见满卷的墨水印渍。
不知是谁的毛笔被风吹落,在她的宣纸上滚过了一周,如今差不多毁了她满篇的对策。
“我的天,你这满篇都瞧不见字迹了!”江念珠看见了,一时愕然。
江念晚也怔怔抬头,瞧见六公主江念安正在寻笔,瞧见这边的情形,惊得捂了嘴不知怎么办。
也并不是故意的。
徐绮摩挲着纸面,唇角绽出极轻一丝笑。
最后一炷香燃到尽头,随着翰林院的小侍从一声“时间到——”,所有人都撂下了笔。
“呀,九公主,您这……”侍从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罢了,也不过就是一次翎朝宴,和父皇说明情况,父皇不会怪罪你的。”江念珠劝慰道。
可若是那样,岂不就等同于放弃?
那她这些时日的努力算什么,陆执为她所费的心力又算什么?
“我不放弃。”江念晚低声说。
徐绮听到了她这一句,有些惊异地转过头来。片刻之后须得轮流念出策题与自己写的对策,她写的这一面子的字都已经被墨水沾染了,要怎么念?
死撑罢了。
她的题目非常阔大,以论天下治乱为题。这篇策论她已经准备了许久,经过祖父打磨,文辞华丽烂若舒锦。她读的时候,自是得了一大片赞赏,在座的都频频点头。徐绮满意坐下,等着江念晚那侧开始。
正准备瞧笑话的时候,却忽然看见江念晚将那沾满了墨迹的卷纸捧起。
“你前些时日那般好学,朕倒要瞧瞧,你这些时日到底有多少长进。”皇帝瞧见江念晚,抬眼些许。
“是。”
江念晚捻着宣纸的角,乍一抬眼,视线就落在了那个人的方向。
他在看着。
也不知为何,他的目光,总能为她添上一二勇气。
江念珠在一旁着急不已,这策论不比平常,都是要引经据典的,能写出已经要绞尽脑汁,何论默念?
“你疯了吧你?你赶紧告诉父皇……”
江念珠话音还未落下,江念晚已经垂下眼,一字一句默来。
这些时日所读的书,请教过陆执的典经,早如刀刻斧凿一般地印在心中。
他曾说策论本在于心,立意才是灵魂。就算这篇策论已被墨迹沾染,根骨却不会变。
所以就算不用方才写的,她也能再言、再述。
“论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是以赏之以仁,罚而多义,乃君子之道。然传中有‘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际,何其爱民之深,忧民之切’,此皆赞有善从而赏,有过正以罚,是故赏罚皆应归之于仁,又拘之以义,是处天下事之大道。”
她言语流利毫无磕绊,娓娓道来。
徐绮怔怔,听出这一题并非翰林院所出,暗自攥紧了手。
在座的所有人也都噤声默然,一时间只听得江念晚声音从容。
她这一番策论很是出彩,不仅有从前《刑赏忠厚至论》的风采影子,还提出了刑赏不仅要有宽仁之心,也要以道义法度责令,是要赏罚分明又宽严相济。
良久之后,江念晚放下宣纸,做了结。
皇帝罕见地赞赏点头:“不错。”
在座的众人也纷纷鼓掌,不少人面露惊艳。其实江念晚两年前有几篇策论就足够引人注目,只是平日里似乎并不聪明,总是追在帝师身后问东问西,才让不少人忽略了她。如今这一篇,确实十分有分量,论道充分清晰,挑不出半分错来。
徐绮紧紧捻着手中的宣纸。
江念晚果真幸运,抽到的题恰好不是翰林院的,是陆执所出。若说她全然靠自己答成这样,她是万万不信的。
之后的几位她都没有心思再听,只等着翰林审判的结果。
翰林院的老学究们几番审论定夺,最后还是将头名定在徐绮和江念晚的对策之中。只是徐绮文采虽十分飘逸华美,却实在少了些根骨在,所提的仁而爱民也过于浮表,缺少见地。
“今年翎朝宴,九公主的《论刑赏》获头名!”
徐绮神色一顿,但很快压下,只撑着站起身来,随众人一同起身为江念晚道贺。
接下来便是自由问论,众人有不解疑惑都可相提。
“真是可惜徐家姐姐了,若不是因为九公主……”似是不敢再言,江岑宁安慰般朝徐绮笑着。
徐绮勉强笑笑,站起身朝江念晚道:“恭喜九公主获得头名,听闻九公主近日一直去镜玄司请教,今日一看确实得了帝师真传。”
江念晚看过来,淡笑道:“我天资不高,多亏有帝师相助,策论才能有所长进。”
徐绮低声笑,道:“是啊,若非这样去找帝师相助,公主今日又抽到了帝师的题目,我们怕也难这么轻易就得到帝师的教诲。”
她声音不高不低,却恰能让周围人听个清楚。
有人带着探寻的目光望过来,江念晚时常往镜玄司跑的事情,他们也是知晓的。徐绮此言……岂不在疑江念晚作弊,提前知晓了题目?
江念珠骤然拍桌子站起来,第一个不平:“你什么意思啊?”
“这是怎么了?”有人吓了一跳,连忙出声询问。
皇帝和一众翰林院官员也听到动静,纷纷转过来查看。
江念晚一愣,目光定在她身上。
徐绮瞧她神色微变,只以为自己说中了她心中要害,正暗自痛快时,忽然瞧得她轻笑。
九公主江念晚相貌生得并不明艳,可一双眼睛却实在明亮,笑起来那份温软干净,是全天下人都难有的坦荡。
“你方才说,我抽到了帝师的题目?”江念晚展颜,心中只觉讽刺。
前几年听闻徐绮夺得翎朝宴头名,她也是当真佩服的。这段时日她没日没夜的努力,也为着能与她相较,甚至研究了她从前的策论,想要写出她忽略的地方。
如今想明白一切,却觉得眼前这个人根本不配作为对手。
徐绮瞧她笑意盈盈,一时不解。
“翎朝宴所有策题都是保密的,并无谁人出题之分。你又如何知晓我今日所答的是帝师的题目?”江念晚抬眼看她,清隽眸子里带了点锐利,声音低得只有她二人能够听见,“难不成你知晓所有翰林院的题目,才知道我今日所答的是帝师所出?”
徐绮面色大变,方才只想着让她丢脸,却忘了这一样。
“听闻,徐姑娘的祖父在翰林院任职侍读,也算是位老学士了?”
徐绮怔怔不语,手指紧紧攥着衣裙,脸色苍白如纸。
“臣女只是……只是熟悉帝师出题的偏重,这也是臣女猜的罢了,和臣女祖父有什么关系。”
“既然如此,那大约是没有关系了。姑娘若是不服,大可将你我二人试题交换重比一次。”江念晚淡淡道。
徐绮咬着牙不说话,指尖几乎都在颤抖。
她所准备的都是翰林院的题目,就算此刻重答,怕也对不出什么。
可江念晚明明也是提前知晓了题目才能答得如此出彩,有何颜面如此说她?
“我哪里敢不服,公主就是公主,若是想赢,自是比臣女容易的。”
“你若再多说一句,我便立刻报与翰林院重出试题,令你我二人重新比试,反正我敢——”
江念晚声音平静如水,已经换了新的宣纸铺在砚石下,微侧过头朝她笑了笑。
急风将她的声音准确地送到徐绮耳朵里,短而清晰。
“你敢吗?”
作者有话说:
最近的新闻真的看得好心塞,宝们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呀。
第16章 香气
徐绮怔怔对上她这目光,一时间手心沁出薄汗,竟说不出任何话。
“在吵什么?”皇帝微皱眉看过来,“可是有何异议?”
瞧见惊动了皇帝,徐绮也不敢再造次,只紧声答道:“臣女不敢,只是策论上有一二不解在请教九公主。”
“翎朝宴本就意在交流思想,你有不解之处提出来就是,也让大家都学习学习。”
“瞧着徐家姑娘是不服气呢。”江念珠轻嗤一声道。
皇帝瞧见她脸色不甚好看,也开明道:“你连续三年夺得头名,今年有疑虑,也是应该。”
不等徐绮拒绝,江念晚先笑了:“父皇说得极是,儿臣也想着与徐家姐姐探讨一番呢。”
“你近日确实长进不少,你既也有想法,不如说说。”
“依儿臣拙见,徐家姑娘的对策确实文采斐然,此乃儿臣不可及之处。但对于天下治乱的策题,姑娘只以仁爱作论,待有过方施以严律,儿臣对此却有不同看法。使君主仁爱固然重要,教化百姓立德却也不可少。儿臣以为,道德乃君子自律之首,此律较严法之他律更为重要。广推道德论教化民风,在一切过错之前就使之醒悟,才是天下治乱的核心。”
江念晚说完这一番话,连江岑宁看她的目光都变了些许。
众所周知,女子不会像男子那样从小就接触策论,参与这样的比试也多是言前人所言,再加以自己的感悟。
可江念晚却真的有自己的见解,且像是丝毫不惧怕言错一般,光是这份从容与自信,就已十分难得。
翰林院的小侍从不停笔的记录,皇帝在座上点了点头,唇边现出欣慰笑意:“你很好。”
徐绮指尖撑着桌案,感受到周围若有似无的刺目注视,咬紧了牙关。
江念晚悄然抬眼,瞧见一身玄墨绛紫纹的官袍,那双一如既往的深邃墨眸,也注视着她的方向。
她抿唇眨眼,唇角微扬。
她要赢,就干干净净地赢。
像陆执那样的人,她不愿旁人玷污他一句。
徐绮面色红白交加,半晌按下一切情绪,勉强行了礼:“多谢九公主教诲,臣女心服口服。”
“好了,既已研讨完,接下来你们就自便吧。今日诸位都有所进益,朕很高兴。”皇帝做了总结,面色较往日柔和许多。
他一离席,席间的氛围骤然活泛不少,规矩也松弛下来,真正的翎朝宴这才开始。
宴上有不少珍馐美食,江念晚最喜欢冰果茶,当季的寒瓜被切成小块泡进加了冰镇的花茶,在夏日里喝来很是爽口,她一连灌了几杯都觉不够。
只是今日这冰茶却有些发辛,也不知是何缘故。
江念珠在一旁逗弄着惠妃养的纯黄狸奴,名叫金团的。它通身无一星杂色,灿金的皮毛映着烂阳金辉,偏偏又被惠妃宠惯着养大,体态圆润如珠,十分惹人爱。
江念晚瞧着有趣,也腆着脸上去逗弄:“好妹妹,借我抱抱。”
江念珠感念她带着自己学策论,难得没有嫌弃,道:“就一刻钟。”
徐绮见江岑宁瞧着这侧的热闹,走过去敬了盏茶,缓声问道:“臣女闻着九公主身上有很厚重的药草味道,我自幼就对草药十分感兴趣,也总愿枕着药草包入眠,可方才被九公主那般难为,自是不敢问了。不知郡主是否了解,这药草包是来自于何处?”
江岑宁原本对她也无甚好感,经这一遭,态度却更柔和了些:“你也别大往心里去,九公主就是那么个性子。我与她并不算熟稔,也不知晓她是从哪里配的药草。”
徐绮笑笑:“本也不是要紧的事,只是我觉得那药草热性,想也不是为了夏日配的。”
“说起来大约是端午后就见她用了,那时候接连下雨,天儿阴沉。”
江岑宁这句话说完,徐绮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也断掉了。
端午后,那不就是兄长进宫感谢帝师的时候吗?她也是求了好久才让兄长将这药草包带进镜玄司,只为了让帝师缓解头痛,如今却成了江念晚的手中物。
“怎么了?”瞧她神色不对,江岑宁关切开口。
徐绮咽不下委屈,缓声道:“那药草包,是徐家送帝师的。”
她虽说得隐晦,江岑宁却也不傻,转瞬就明白过来,惊道:“怎会如此?”
徐绮不语,江岑宁缓声安慰:“你也别难过,九公主看似娇弱实则内心强硬,我早先在重五宫宴就领教过了,是最能理解姑娘的。你也宽心些,若是她一介公主硬要一个药草包,帝师那般温和的人,哪里有不给的道理。想来她也是怕帝师在意姑娘,才这样介意这药草包,拿到自己跟前用不说,还非要叫你知道。”
她三言两语说过,徐绮已然收了委屈,蔻丹长甲嵌进掌心,美目中只剩憎恶与恨意。
江岑宁又劝慰几句,徐绮一一点头应了,状似无碍。
恰好此时有世家小姐相邀去邻近的澄湖赏荷,江岑宁便告了辞。
青珏台靠近澄湖,湖中荷花开到盛季,此刻有不少人都去到那边观赏了。徐绮瞧江念珠和江念晚抱着那猫也朝澄湖走去,目光忽而定格在那通体浑金的猫上。眼下瞧着是安稳,可这硕壮体格若是发起狂,想来也有意思。
“今日的香囊带了吗?”徐绮掀起眼看着侍女,淡淡问道。
*
澄湖旁的荷花嫩蕊凝珠亭亭玉立,被午后的光照来分外明艳。
江念珠抱着金团走到澄湖边的桥梯上,拍开了江念晚蠢蠢欲动的手。
“你今日都抱多久了……”江念珠忽而皱了皱眉,闻见她身上一股酒气,“你喝酒了?”
“没有啊,方才只用了果茶。”许是被烈阳照射得有些晕,江念晚答话之余也着实感到脑子不甚清醒。
“你脸也红红的,”江念珠狐疑地瞧了她半晌,道,“每人桌上有两壶冰饮,一是果茶饮,一是果酒饮,你可是拿错了?”
江念晚茫然抬头,并不记得什么区别,反正是都喝了。
江念珠毫不留情地嘲笑了她一番。
“连茶和酒都分不出,你是不是真的傻啊。”
正说笑着,忽然瞧见一人走过来,江念珠收了收笑容,怀中的金团也不安分地动了动。
她顺势将它放下,轻声对江念晚道:“瞧见没有,不讨喜的人连猫都不待见。”
江念晚头脑晕怔,没太明白她的话,只瞧着金珠,担忧道:“这么放它走怎么行?”
“无妨,母妃在宫中都是散养,这猫最是乖巧。”江念珠肯定道。
徐绮走过来请安,态度恭和:“二位公主安好。”
“你来干什么?”江念珠扬起下颌,颇为不耐地问。
徐绮并不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