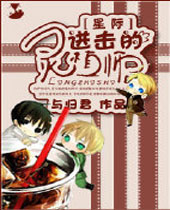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簟!�
但是我并没有忘掉它,因为大师们的难听音乐对我总是具有吸引力。而这是只有我和少数人相信存在的一种东西,因为正式的权威们想要否认它。他们坚信:如果是一位大师,他就只能作伟大的音乐作品,而当那作品并不漂亮时,那肯定至少也要拔高,或是一种天才表演,或是某种东西的一个综合,或是某种文明的一种象征,或是形式结构的一个奇迹,或是……真是累死人啊!就是为了不说〃难听的〃。然而,要是好好地想想,这事儿却是一件几乎令人激动的事情。例如,正如结果显而易见,简单地就是难听,如果一个人试着想像一下贝多芬(哎呀就是贝多芬),他决定为比所有人都伟大的歌德写点东西,实际上并没有人请他写,但是他决定要写,而结果他所能做到的,是做似乎是一个假贝多芬而又的的确确就是贝多芬的某种东西,是公司的正式说明书一类的东西。整个儿是井井有条,完全到位,整个儿丝毫没有天才的痕迹,仿佛歌德的幽灵将其阻挡住了。就像应试的一位学生那样,仿佛他要对那位大人物解释说他也是大人物;但是解释是一回事,是大人物又是另一回事,而他并未能成为大人物,这至少有点令人激动,是值得思考的漂亮的事。犹如新闻报道所证实的如下事实:贝多芬甚至没有能及时提交其作品,当时埃格蒙特的首场演出没有音乐,或者是用了谁知道是谁的音乐,贝多芬的音乐赶上了重新演出的一场,也是惟一的一场,最后的一场就像你看到巴雷西哭泣,或者你发现马丁·路德·金背叛了妻子。的确,那些事就是使他们真正成为大人物的事情。
然而无论如何,历史并不是傻瓜。事实上,那场音乐,只有一个版《前奏报》(Ouverture)头版挽救了它。其余都被忘却了。
/* 5 */
世界的起源
埃布拉
找了她几乎一百年,没有找到她。本来知道她曾经存在,但并不知道在哪里。再说也是可以理解的,两千五百年前消失了的一座城市,被恰恰是不能再看到她的一个征服者她极其愚蠢的奢望把她一扫而光的一座城市,怎么能找到她呢。挖着挖着,每每找到记载那座城市的可诅咒的描述,而每一次神话都扩大了,要找到她的愿望也更强烈了,没有能找到它的结果也更让人感到被愚弄了。她还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埃布拉。其意思似乎是〃白色〃。如同其发音,她具有某种隐形的东西。名字是正确的,看看那事态是如何发展的。
默默地,埃布拉永恒地躲藏在了叙利亚的地皮下。有一次,在1926年,名叫威廉姆·福克斯威尔·奥布赖特的一位美国考古学家曾与之擦肩而过。她该是屏住呼吸。他注视着那奇怪的山岭,但他当时所想的全部就是:多么奇怪的山岭。于是他径直地走开了。埃布拉又隐藏了三十年。后来有一天,当地农民们碰到了露在地面上的一个类似浴盆的东西,此物很漂亮,上有浮雕,整个儿并非一个随便的浴盆。这是投降的开始。考古学家们开始审问它,仿佛它是个悔过者。而那件东西讲述了至少具有四千年的一种文明。他们继续挖掘。那文明开始一米接着一米地出来了。明确知道底下埋着何物之前,用了五年时间:他们找到了一尊半身雕像,那上面写着一些东西,而那一些东西是由一个名叫伊卜比特…利姆签署的,而伊卜比特…利姆曾是一个城市的国王,而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叫埃布拉。你想想:他们找到她了。
由于找到埃布拉的是一些意大利考古学家(你看在这个国家里并非一切都叫人恶心),现在,埃布拉,你去罗马,到威尼斯宫,你就看到了她。在那里他们收集了三十年的发掘成果:故事、实物、图片、纪录片,全有。对文物你已习以为常,但是那里不同,整个儿具有昨日发现的魅力。可以这样说,一切都还是热的。而且我们可以努力让你相信:埃布拉并非是一个一般的城市,你正在看到的是伟大历史的一个片断,并非像其他一样的一种残余物。〃意大利人在埃布拉发现了一个新的历史、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文化〃,一位名叫伊纳切·丁·吉尔布的人如是说,而我明白了必须相信他。我就是这样带着作为第一个人看见了玫瑰宝石柱或金字塔、斗兽场的一个人的那种面孔,观看了那个展览。那是一种游戏,不过并不完全是个游戏,因为的确有些东西让你感到惊奇,例如那些字块。
事情是这样的:挖着挖着,他们在王宫里找到一个厅,这个厅原本是档案厅,这一发现使他们永远载入了史册。因为那里面收藏着多达一万七千块的字块残片,也就是在一种并不认识的语言中的一个无尽的旅行,也就是在数千年来已不存在的人们的心灵中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飞翔。这不让人发抖吗?你的鼻子碰着一个匣子,很明亮的,里面有个托盘那么大的片片儿,上面有个双语(埃布拉语…苏梅罗语)词汇表,全部漂亮地用楔形文字雕刻出来,就像是专为我们留在那里的一种信息,以便我们能学会阅读。这个时候,肯定会让你发抖。你看看那泥土上刻画出的所有那些道道,你看到在那里干活的人的手和眼睛,仿佛是昨天干的,然而却是三千年前的。你并不确切地知道为什么,但是显然,任何古陶罐、任何珠宝、任何雕像都没有那上面写有物件名称的泥饼子的那种吸引力。那物件的名称,一个挨着另一个,大约有一千五百个。物件名称,是比所有东西都简单的东西,但这是最伟大的东西,是一切的开始,是一切的最后真理。真的,你会被惊呆的!如果说你一点也看不懂,那也没关系,因为苏梅罗语对你来说是一点外来的东西。如果说在那一万七千块残片中没有一块是讲述历史的或写的诗歌类东西,而整个儿是商业的玩艺儿,或政治性条约,那也没关系,只要有某些对神的祈求就行了。没关系无论如何,似乎是在一块土砖上跳探戈舞的鸟儿留下的足迹的那些雕刻就是一幕奇观。
/* 6 */
世界的起源
复杂性(一)
如今绝对要读的这本书,是六百页的一本,用三万里拉买回家来,也就是五十里拉一页,也不算太贵。此书名为《复杂性》。一位名叫莫里斯·米歇尔·瓦德罗普的美国人写了这本书,名叫英斯塔尔书店的一家出版商将其翻译成意大利文。大概你们都不曾听说过上述两个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名字。总是有第一次。
《复杂性》不是一部小说,而是讲述一个故事:真实的故事。就是〃圣菲研究所〃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在八十年代,一批智者为了大家都有的一个模糊、不确定的共同想法而走到一起来工作,而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想法。他们中什么人都有: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生物学家,两位电脑专家,其中有两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些人多年来在研究昆虫如何繁殖,或者哪里产生风暴;有些人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世界怎么会在只有短短的数十亿年内就像蛋奶酥那样冒出来了。就是一些这样的人。那种脑子,只要你能让它超过平均水平,尔后你就无法再使之停止下来。
他们每个人本来可以呆在自己的家里去培养自己的狂热,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他们在无数的科学家中一点一点地相识了,仿佛是同一星球的火星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们的头脑中,除了谁知道有多少数不尽的心灵次货之外,他们却有一个想法,一种特别的想法,这种想法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当他们谈论它的时候都心领神会。谁也无法给这种想法一个准确的名字,而他们却都明白谈论的是同一样东西。这恰恰就像当你碰见一位小学同学的时候,你会想起另一位同学,那位第三个书桌的同学,用不着提他的名字,但你们都很明白,是那位知道萘的同学,是这样做手势的那位,一切都非常模糊,但是你明白,没有错,当然如果你明白的话。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想法,但不是一个一般的想法,而是一种无限巨大的想法。他们每个人以各自方式所想的东西就是世界在运转,因为世界是一种非常混乱的东西。但愿如是说似乎又并非如此,不过我发誓,这是一种天才的想法。
然而必须像开始时那样考虑:世界,等等,等等。我想说:世界。不是经济,也不是生物,也不是棒球,而是世界。那里的那些人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想法:解释干酪汉堡包的价格,第三世界人口曲线,蝴蝶翅膀的形状,罗马帝国的衰落。有点低调,不过也不是很低调,他们所解释的东西就是:他们正在使科学翻个身,就像翻袜子一样,他们仅差一步就要建立〃二十一世纪的科学〃。如同所见,这是一个小小的计划。
他们想,这场革命的钥匙就是非常混乱的那个想法。我尽量把它说得干净些:秩序是混乱的一种特权。世界并非生来就有秩序,也不是简单的,世界之所以变得有秩序,是因为它运转所根据的那些极为复杂的各种体系具有组织成有序模式的一种客观倾向。所以世界在运转并非因为它简单,而是因为它是那复杂的地方,非常复杂,乱糟糟的。
圣菲研究所的那些有头脑的人们用一个非常漂亮的术语破解了事情发生的焦点:发生在混乱的边缘。这就是实际上事件自行产生所在的那个地方,创造的地点和时间。原则上就是复杂性。
再作个努力来说明。当圣菲研究所的智者们谈到复杂性的时候,他们心里有一件特别的东西。他们并不是想着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那些复杂的东西,而是想着各部分互相关联的那些复杂的东西。一种各部分互不相关的复杂体系,是这样一种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各种变数,即使非常之多,也都以同样水平行事。例如象棋,是一种复杂的体系,走棋的招数非常多,但总是走棋,与那天天气如何无关,与谁是内政部长无关。而干酪汉堡包的价格则属于这样一种复杂制度:诚然其价格来自算术级的供求关系,但是也受制于其他各种变数那天天气如何,谁是内政部长。无论如何,在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那种复杂体系中,2加2总是等于4;而在各部分相互关联的那种复杂体系中,2加2就可能等于5或3或0,这要看情况。在这里,你处于混乱的边缘。在这里,你处于发生创造的地方。
在整个故事中,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种复杂性的想法,而且要把这种想法置于各种事态的中心。也许我也能解释为什么,但是只剩三行字本文就要结束了,因此我就此作罢。我是讨厌连载故事的,多年来我厌恶Tex,因为你要等一个月才能知道如何来挽救自己,但是这次我投降了,作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在《巴南姆》专栏中写作连载文章,把一切都推到下星期三去。
/* 7 */
世界的起源
复杂性(二)
上篇概述:一群包括各种智人的组织在新墨西哥圣菲研究所中,为了在表面上愚蠢而实际上天才的原则上重建科学世界的未来落在现实的一个准确地带,在那里混乱差一步就滑到纯粹的混乱之外,而停滞在一些极端复杂的体系之中。这些体系具有一种组织在秩序之中的可以验证的客观倾向:重建其行为就意味着找到未来的秘密。他们,那些智人,正在那里尝试。正如莫里斯·米歇尔·瓦德罗普所著名为《复杂性》的一本书所讲述,该书如今在意大利已由英斯塔尔书店翻译出版。
那么,我说到,使人感到惊奇的是把复杂性置于世界的中心。认为就是在那里现实找到活力来改变并整理成某种秩序,获得一种意义。似乎是显而易见,但并非如此。如果不在黑暗中就没有光明,如果不在混乱的边缘就没有秩序(不能相反地说,混乱可以存在,这就够了,它不应当从任何秩序中产生)。现在,一般地说,人们对复杂性抱有一种怀疑、防卫的态度。一个讲话复杂的人,你们大概不会从他那里购买一辆已经用过的汽车。如果是这样,复杂性就是作为一个令人不快的中间状态来度过的:要解决、要战胜、要克服的一种东西。瓦格纳的音乐作品刚写出来的时候曾复杂得令人讨厌,但是在那里练习了几个小时,渐渐地〃懂了〃它,它就变得美了。然而,该书所讲述的却是不同的事:是对复杂性的喜欢,对复杂性的需要,教育人们把复杂性作为居住的地方,而不是要逃避或超越的地方。必须泡在那里,〃感受〃它如何动作:如果你在那里,那你就是在世界机房之中。
那些人在那里研究基因图、经济增长率、人工智能这类东西。一般地说,这些东西你是一点都不知道的。但是你领会到一个原则,而这个原则同你在所有日子里能取得的经历有着最直接的关系:同你也认识的世界有关系。而这个原则就是:并不是你处在光明地带之中,而是当你能在黑暗地带之中行动的时候,你就接近明白了。如果那是黑暗,那么我们就明白了。
例如,当他们问你:为什么他以他那种方式、以描述那样一种故事来写了他那部小说呢?答曰:确切的东西我不知道。如果你回答,并给以一个清楚的回答,那么你就觉得你在撒谎。这并不是一种明白的方式。而如果你说〃我不知道〃,那么你和对你提出问题的那个人,你们就进入了真理地带,你后来加的所有临时的话都是真理。而实际上,你所知道的东西就是你写的那些东西,就在于那些混乱的边缘,而且大概就是一个混乱的边缘。只有那个混乱的边缘,换句话说,绝非其他,是用语言描绘出来的那里那个混乱的边缘的地图。你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不稳定地呆在那里,尽可能长的时间,全部所必要的时间,以便使那混乱几乎能自己组织成复杂性,因而成为某种秩序的开始。对此你真的不知道是怎么运转的,但你感到有,或者至少将来有当有人阅读的时候就会有。人们知道魔术,而实际上使你不敢公开说出那类事情的原因是他们知道魔术,因此使你感到一种羞耻,你就急忙寻找清楚而又合理的解释。然而如果你读一读《复杂性》,对你来说羞耻就消失了:人们所看到的并非魔术,而是科学,是事态的真相。你可以这样讲述那些事而并不给人神秘的印象。
在这一切之中,下面这样一个规律具有其真实性,否则就是有争议的。这个规律就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不能不做到高水平的复杂性,也就是使之成为〃困难的〃。在这种事情上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恐怖,在最黑暗的时期里甚至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一件作品,如果它是困难的,那么大概就是一件艺术品。这是精神错乱。不过某种感觉是有的。因为如果你真的是在混乱的边缘工作,那么那个混乱的某种东西就会延长至抓住你所做的东西,咬它,使之面目全非。你不能想在同混乱接壤的边界上贩卖东西而你不会被弄脏,不会被弄皱你的衬衣、心灵以及声音。
很难办的,但也许是真的:如果你从事的是创造性的某些事情,那你就在混乱的边缘工作了。而如果你在那里工作了,那么你所做的事情应该散发着混乱的臭气。没有圣人。而如果有人拧着鼻子,因此闻不到马鞭草的香味,那你就别在意。
/* 8 */
世界的起源
世界的起源
并不是一个人专门去巴黎就是为了看那幅画,但是他一旦已经在那里了,他就会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