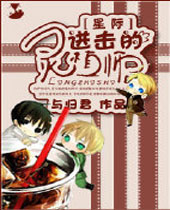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8 */
世界的起源
世界的起源
并不是一个人专门去巴黎就是为了看那幅画,但是他一旦已经在那里了,他就会产生好奇心。使他产生好奇心的是,在处理库尔贝①那幅画的整个故事中,我不知道这是受哪位这样的收藏家之委托而为之。那幅画的最后所有者当然是拉康,他把那幅画盖起来了,只给知道它的人看,直至他去世时,那幅画,而不是拉康,就落入奥赛博物馆内,与其他库尔贝的画放在一起,没有盖着,尽管其内容不可否认是下流的,但只有一块玻璃保护着。这是件怪事。一个人完全不会专门去巴黎就是为了看那幅画,然而一旦到了那个地方,他就会马上去奥赛博物馆,为了正式地看看那些画,而实际上是为了看那幅画,想说说事情究竟如何。那幅画。
①古斯塔夫·库尔贝(1819…1877),法国画家,被认为是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画派大师译注。就这样进入了都是大理石和办公室的庞大的老火车站,在那里一反任何逻辑,一群群移民者的眼睛和大脑被唤来一次性地忍受那数以担计的美,而眼里并没有太注意,便谨慎地走向库尔贝展厅,在半层里,走二十米远,然后向左转。前面就是了,他好像是偶然地到了库尔贝展厅,那幅画他没有看到,因为他按照某种逻辑,跟着人多的地方走,意外地来到一幅巨大的画前面,这幅画像一个电影银幕那么大,题为《埋葬》,这肯定不是那幅画。实际上似乎是电影院。这幅画整个儿有点黑,上面有那些伤心的女人们的花边和手帕穿破那黑色,好像是那充满悲伤的森林里的小动物在飞舞。男人们之中,只有一人在哭泣。远处有个神甫,表面上已厌烦,有个人向你转过身来注视着你。他在那里已经这样注视着一个多世纪了。而后就永远这样。行了。那幅画在哪个鬼地方呢?那幅画在靠那边一点儿,那里根本没有成堆的人,人们反而有点躲开。实际上,如果好好地想想,这样也是合乎逻辑的。在那堵大墙上,上面有另一幅像一块电影银幕那么大的画,画着斗鹿;在左边有画小溪的一幅小画;在右边是画着一个背向的裸体女人的画,那女人旁边有条小狗;在中间就是那幅画。年代:1866年。尺寸:46厘米×55厘米。标题:世界的起源。滑稽的标题,也可以说是恰如其分的,但肯定是滑稽的,因为人们看到的是女人的身体,裸露的,躺在一块床单上,两腿是张开的,近处是生殖器,非常清晰,也没有聪明地用个影子或者正好是那个床单的一动来减弱一下。没有这样,就像最内在的色情剧场的一瞬间,以它那个生殖器作为主角,有点半闭着,逼真的如果你们明白我想说什么的话漂亮而逼真。那画面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是窄小的,那模特的两条腿和头部均在画面之外,靠近上方边缘一点地方正好露出一个乳房,而作为在那下边30厘米处爆炸的轰隆声的一种回响该是对的。在那轰隆声的整个周围是只有在那些画中才有的一个女人的腹部和大腿的白色,现在已经不再这样画那些女人,母亲…情人女人,她们没有骨头,只有肉和曲线,以及像玻璃那样的皮肤。
人们无法真正在那幅画前面站着不动。走近那儿看看标题,冷笑一下,去叫朋友来。朋友来了,感觉到该评论点什么(真蠢,但是可以明白),然后他们就走开了,但还是向那幅画回过头去。因为显而易见,如果不是由于你感到有点害羞的话,就不会那样看一眼就完了,那幅画不是要你笑着看一下,而是要你认认真真地看几分钟。
我竭力地在那里呆着,并且坚持了两分钟。我盯着那幅画,仿佛那是《永恒的微笑》。而我所记得的是,在那两分钟内的每一瞬间,我都肯定那幅画是特别美的,我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但是绝对肯定。而且还有这点:那幅画要把你的目光掏空。这难以解释,然而确是如此:把你的目光掏空。我也可以试图用其他话来说它,但实际上简单地就是这个:把你的目光掏空。的的确确如此。如果你们能明白的话。
我转过身来准备走开了,在我前面看见了另一幅特别大的库尔贝的画,暴风雨后的一块礁石。大海,天空,土地,阳光。什么都有。然而,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放上一张电车票,那会是同样的效果零反应。正如我前面所说,目光已被掏空了。我们希望能像电池那样:我闭上眼睛两个小时,它就重新充电了。
/* 9 */
世界的起源
街头演出的《迪多内和埃内阿》
真实情况是,我到阿尔杰罗①去了,去看电影。确切地说,那是个电影展,其主题是只要开始说起来就说不完的那种主题如何把小说拍成电影。是否能做,怎么做,书更好,电影更好。来点带酒精的润滑剂,你也可以在那里消磨夜晚,在一个古堡类建筑内挂起的一块银幕上,其中放映了科波拉执导的《德拉库拉》一片,该影片是根据勃兰姆·斯托克的同名小说(很漂亮的书)改编的。一部大片,它能够控制观众的就是,一下子是色情场面,一下子又是血腥场面。看着那些场面,你会激动。也就是说,惟一除外的是《太阳下的决斗》。
①阿尔杰罗,意大利撒丁岛西北部海滨港口小城译注。
②亨利·普尔赛(1659…1695),英国音乐家,被誉为英国最伟大的音乐天才,系宫廷作曲家,作有许多歌剧,其代表作之一是1689年所作歌剧《迪多内和埃内阿》译注。好吧,我是去那里看电影的,但是后来我发现,正当在银幕上放映着另一部小说改编的影片(《群》,一个让你感到目瞪口呆的故事)的时候,离那儿三百米远处的阿尔杰罗的小广场上发生了一件简直令人无法相信的事,那就是在那里表演普尔赛②的歌剧《迪多内和埃内阿》。于是我走上了一条满街都是光彩夺目的珊瑚和软木拖鞋商店的小街道,来到了那个小广场。
什么玩意儿!
歌剧已经开演,你到了那里,在栅栏后面停下,自动地(免费)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泡影之中。一种魅力,一种虚拟现实的东西。那个音乐有些东西,什么时间的、数世纪的,都没关系。那音乐从数百年前来到你这儿,两分钟后已经在那里给你了,而你所听到的恰似一个怀抱,你曾经一直梦想的那个怀抱,为你消除任何疲劳的一个安乐窝。那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他抛弃了她,爱情结束了,死人的故事。然而你所听到的却完全不是悲伤,而是像珍藏在水晶盒里的一件珠宝那样的悲伤的踪迹。悲剧是出现了,但虽然悲剧的出现并不是在那里。这是一种更复杂而高深的东西:在同样的一个世界里,那些已经不存在的人出现在他们留下的东西里。已经不在了的爷爷的安乐椅,没有叫醒你就走了的她的睡衣。就是那些东西在那里,有的和不再有的,爷爷和她,轻率地同时出现了……你不用太长时间就会想到,就是那音乐该用来跳舞。总是这样,所有悲剧,小的和大的,所有都系如此,只是如果能够做到。
周围,那广场也真是一幕好戏。三层楼上百叶窗后面有些人在探出头来看,前面那家用绳子晾着衣服(有个海边用的帐篷,上面还有令人毛骨悚然的戴着眼镜的甲壳类动物,还有裤衩、袜子,最后是牛仔服),旁边的窗户关着,被无限悲惨的霓虹灯光所照耀。不时地有骑着小摩托车的那些人从旁边的街道上蹿出来,虽然他们没有料想到会突然地来到了那天堂泡泡之中。那时有个男孩嘟嘟囔囔地说着脏话:〃哎呀,天哪……他把油门放到了最小〃;而后面坐着女孩的那位男孩则要表现一下男子气概,因此他狂笑着,大模大样地让摩托车冒出许多废气;后面坐着的女孩也笑着,对他说:〃哎呀,你干嘛哪!〃而他们并不知道,在那个舞台上正好是在讲着他们的故事呢,不是诅咒他们,而是有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最后这样结束并没有任何不好,他或者她最后走了。有人走了,另一个人想死。诚然,无论如何在其内心将会很难有勇气和美德来说出迪多内最后说的那些话:当埃内阿离开了的时候,对迪多内来说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于是他对其知己女佣人说了一句非常漂亮的话,即使没有用像普尔赛所作的那样美妙的音乐来包装,也会是很漂亮的一句话,这句话的英文是〃Remembermebutforgetmyfate〃,在那里演出的歌剧中慢慢地唱出来,像一种非常高尚的哀怨。如果翻译成意大利文,那句话就是:〃请你记着我,但是要忘掉我的命运。〃
作为附言,我说,那个小广场是在剧院前面的小广场,那剧院虽然小,却也雅致,已经关闭了多年,如今他们终于把它修缮了,那些包厢和那马蹄形剧场,一切都正规了,但是《迪多内和埃内阿》这场歌剧,他们在外面,就在剧院前面演出。他们走出了剧院,创造了广场天堂。于是我想到,我真愿意把穆蒂①叫到这个广场上来。他肯定会觉得那演出很可笑,但问题不在这点上。我会想让他明白要走出剧院,到一般生活中去。我不会想要他在斯卡拉歌剧院前面演出音乐会,我们该明白,那会是一件蠢事。我头脑中想的是,必须走出剧院。躲在那无法进入的殿堂里,活活地关在对那种无法挽回的过去的迷信之中,并不是在这个国家里保护文化和音乐的最佳方式。你想想那电视,在那里等待、躲避,是愚蠢的。有人也能来救你这位在海洋中的愚蠢逃生者,然而如果你却拒绝从你的漂流残骸上下来,还该做别的什么呢?
①里卡多·穆蒂(1941…),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时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乐队指挥译注。
/* 10 */
世界的起源
饼干厂里的一个破碎城市
我要对那些不是都灵市①的人说,科莱尼奥不仅是被人们遗忘的精神病院(现在是原精神病院)所在的地方,而且也是被叫做法国大道的一条道路所穿过的许多地方之一。这条道路穿过一系列地方,这些地方一个连一个,只是由写着名字的牌子分开,就像罗马涅海滨②那样,只是这里没有海,但是有其他许多东西作为补偿。例如,现在有一个名叫马吉奥拉的工厂,做饼干,但是如果你在这些天里进这个工厂里去,你会看不到饼干,而是看到萨拉热窝③。这并不是一个隐喻。
①都灵市,意大利西北部工业重镇译注。
②罗马涅海滨,意大利东海岸埃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所在海滨译注。
③萨拉热窝,前南斯拉夫的波黑共和国首都译注。
④米兰市,意大利北方工业重镇译注。这是一种展览(但是展览这个词在这里是很不确切的),题为〃萨拉热窝的生活,封锁的再现〃。一个女孩儿向我讲述了这个展览是如何诞生的,这位女孩儿有个漂亮的名字(克雅拉,带K和Y)和一个无法叫的姓(范埃林库伊曾,是荷兰姓)。她说,有一天她去了萨拉热窝,因为她不相信报纸上所写的那些东西,她要亲自去看看。她作为我不知道是哪个广播电台还是杂志的人报了到,她钻进了穿过塞尔维亚路线下面的隧道,在城里钻出来,她就这样去看了。后来她又回去几次,她每次去所做的事情就是带走那个城市的一些东西,因为那些东西、物件比言语更能说明问题。如果需要让我们明白有关那种荒唐的围困的什么事情,那么这就是一种方式:我看看东西。于是她把从那里带回来的东西放在一起,办了一个展览(你们明白,这个名字根本不对),先是在米兰市④办了,现在在科莱尼奥办,将来还要在意大利其他地方举办。
举个例子来说。她在萨拉热窝住在一所房子里。落下一颗炮弹,炸中了邻居的住宅,夺去了全家人的生命。现在你到那个制造饼干的地方去,会看到那个家庭的照片,以及那个家留下的东西:炉子,一把椅子,上面用塑料布代替玻璃的窗户,一些修修补补的物件。瓦砾和灰沙。你往前走,绕过一些木箱子和破烂汽车,便到了一个市场,所有货摊子都是空的,香烟盒是用随便的那种纸做的,真正的香烟盒早就没有了,但抽烟的欲望并没有完,因为抽烟可以解饿,于是他们还凑合着做烟,而包装就有什么用什么了,只要像个盒子就行。似乎微不足道,好好地想想,其实是以小见大。又如儿童们的那些画。克雅拉是从一个幼儿园那里带回来的,看着那些画,就像窥视着实际上从未看到过和平的那些小孩子们的心灵。有人画北约的飞机,有人画鲜花、树木和天空中的飞鸟。有个人只画东西,没有画任何人,只有东西,他该是坚决地认为那些人真叫他恶心。
我不知道你们从那场战争懂得些什么。每天在电视新闻上都有,但我不知道你们真正懂得什么东西。我本人懂的很少。这样说会叫人恶心,但是我几乎一点都不知道。我原先几乎什么都不知道。现在我在这个饼干厂里,我知道得多一些了。它帮助你认清那种荒唐:一种封锁,就像在中世纪,只是我们处在2000年;多年来在家门下面就有那些敌人想进而又进不去的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已不再有任何一个角落能躲过狙击手或炮弹。你探出头去,你在路上走的每一平方米上,你都可以成为一支准确的枪的瞄准目标。你呆在家里,在洗裤衩,一颗炮弹就可以把你送去永远洗裤衩。在2000年。晚上青年人出去,尽管实行宵禁,尽管像发疯了,但他们还是出去,因为这可能是最后的夜晚,他们点亮打火机,好看清楚脚往哪里踩。克雅拉说,真好像许多萤火虫一样,他们去玩。只要说说这些事,你就会感到极为悲伤,我不知道确切地是为什么,但真是极为悲伤。
为一场始自十九世纪的战争而实行中世纪式的一种封锁:那些人为民族身份、为独立而互相残杀:我们在历史书上学习的那些东西,1848年的加里波的①,斯皮埃尔伯格②。2000年见鬼去了?究竟怎么回事会这样停止历史,把文明降低为零,把整个人民的智慧随风吹散呢?也许,要想明白,必须从那个饼干厂里正好在入口处的那张照片说起。一张铁托将军的照片,黑白的。是一张四分之三的半身照片,他已六十多岁,明亮的鬈发,浅色上衣,上衣小口袋里装着一块小手帕,眼睛注视着未来。他没有皱纹,但是身上有了弹洞,极为准确地击中照片的画面:其中两个在眼睛里,第三个在嘴巴里。
①朱塞佩·加里波的(1807…1882),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英雄译注。
②斯皮埃尔伯格,捷克布尔诺附近的一个城堡,十九世纪时曾有四十八名意大利爱国者被囚禁在那里译注。
/* 11 */
世界的起源
孤独的公牛
杰克·拉莫塔有着似乎是生造出来、而却又的的确确是真的那种名字之一。他就这样叫:四十年代的拳击手,重量级世界冠军。他击败了那位同爱迪思·皮阿夫一起的马塞尔·塞丹,因此而夺得腰带。他不是那位叫时装设计师的拉莫塔。第一声锣响他就低着头开始,不停地打,直至结束。有胜也有负。他不时地出售比赛,而在那个年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被他赢过多次的蒂贝里奥·米特里讲述:那人最喜欢的招数之一就是用头(而不是脸)迎击对方的打击,而不是躲避打击,他没有多大感觉(石头脑袋),而你却把手都打破了。这说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