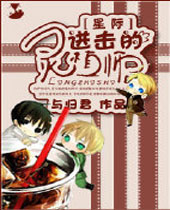用吉他射击的人-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张照片,也是一动不动。数米远处有一个男孩:他穿着短裤衩,光着脚丫,在一个球后面跑着。(那个球属于先掉进了水里,然后又沾满了沙子的那种球,像那沾着面包屑的米兰式牛排一样,你踢那球,那皮子就遭殃了。)他跑着。即使那是一张照片,他也在跑着。你看着那张照片,会使你确信那不只是一张照片,而是一条定理。要么你站在贝克特一边,要么站在那男孩子一边,无法摆脱。要么你看着沙子,要么你在上面跑着追那个球。近在眼前,又是世界的两个极端。这是世界的两个极端。无法调和的两个极端,很遗憾。而人们说本来可以是很简单的事:贝克特可以抬起头来。冲向一翼并要球。这就会失去魅力,一切都会是更加轻而易举。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我明白了,在布赫梅塞翻阅书本不好。要么你是一个出版商,你卖书;要么最好你别摸那书。我合上那本书,然后等着展台那位笨蛋女人转过身去的那一会儿,我再打开书,但就仅仅一会儿,因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总是要抱有希望。
很遗憾,贝克特总是在那里,手里拿着鞋,眼睛看着沙子,一动不动。好吧,我打算明天再回来。
/* 20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布赫梅塞(二)
①萨尔曼·拉什迪(1947…),印度英文作家,1998年出版《邪恶》一书引起伊朗伊斯兰领袖霍梅尼的愤怒,以渎神罪被判死刑,因此被迫逃亡译注。布赫梅塞书展那样的一类东西。塔斯利马·纳斯林现年三十二岁,生于孟加拉,如今逃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她还要继续逃跑。一本书和一篇文章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她恼羞成怒:她被判处死刑。她大概仍然属于这样一些作家之列:这些作家无论在哪里都从事其职业,而又不让世界觉察到。如今她成了一种象征,一个小拉什迪①,某种需要加以保护也可以加以利用的东西。在她的记者招待会的大厅里,他们翻了你的包,并用探测器从头到脚检查过了之后,才进来了。在讲台上,一大堆麦克风等待着她,这些麦克风将要使她的声音流到大批愤怒的好人的血管里。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排了一大队,像一堵墙,对准了她的位置,她的面孔将传遍全世界,从照片上看那是一张温柔而悲伤的面孔。西方对像她那样被宣告的牺牲者抱有其贪婪的好奇心,这样一种想法是难以消除的:这是再一次感到自己优越的一种方式我们不杀那些作家,顶多我们不读他们的书就是了。大家都像大事降临到身上似的焦急地等待着。而她则做了最正确不过的事:不来。她没有到来。问题在于没有给她发放签证,住处难以安排,在像很少得到保护的世界博览会这样一个地方不可能保护她。在场者当然气愤之极。摄影师开始转过身来,拍下摄像机的旗号。有人对准空着的那个座位按下快门。这是正确的照片。这是一种被震惊所包围的空缺:如果有一种方式来讲述塔斯利马的故事所讲述的事,那么那种形象就是最正确而干脆的方式。
我第一天就看见了汤姆·莫里,是在有美国出版商的桌子那里看见他的。那桌子周围有好几位小个儿日本女子,她们像机器一样做着笔记。我看见了他,因为像他那样一个人,你是不能不看见的:上百公斤的男人包装成一个完全的黑人,宽大的双肩扛着一个小小的娃娃头,娃娃脸上安着两只东方人的眼睛。然后,而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数以公斤计的手镯、戒指、手表、镶在金子上的绿松石,简直就是瓦伦察①的一位代表的样品集成。我待在那里看着他,自问那些书是否能够出售或购买。后来,到晚上,我到埃科②那里吃晚饭,大家围坐在桌旁,庆祝他的新书。他的所有出版商都到了,其中也有他。他配戴着他的那些手镯,他的那些绿松石,他的一百公斤。我简直不敢相信。于是我就问了。他叫塔凯石·莫里,人们叫他汤姆·莫里,生于日本,在美国学习过,年近五十岁,肚皮有两层肥肉,西方最好的销售商的权利几乎都落入了他的手中,从他的手中再出去征服东方:世界出版业的某种丝绸之路。他们说,他是在一位叔叔那里做职员工作开始的,当时管画册。如今他是亿万富翁。当他同西方人在一起时,像一位那不勒斯人那样笑着做手势。当他转过身来同东方人谈买卖时,又重新钻进只有他们才能做到的那种超凡的恰到好处的硬壳里。他是一条变色龙:大把大把地捞钱。
①瓦伦察,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区阿莱桑德里亚省盛产金饰的小城市译注。
②翁伯托·埃科(1932…),意大利符号学家和美学研究者译注。罗卜·范德尔·普拉斯,对于钱,他该见得比较少。他有一个四平方米的展台。他的出版社名字叫〃自行车书籍出版社〃:只出版有关自行车的书,而其中一半是他自己写的。他是保养自行车的一位魔术师:如果需要,他可以教你如何使一辆自行车永远可用,只要有人对此感兴趣。他有着一张悲伤乐师的脸孔,那些演奏击弦古钢琴的乐师们,全部时间都在调弦,当然,这是因为那是一件古老的乐器。他生于荷兰,生活在加利福尼亚。我问他来法兰克福做什么,他平静地回答说:卖书呀。卖关于自行车的书?是卖关于自行车的书。他打开记事小本,让我看:一些法国人,一些德国人,一个巴西人,一个日本人。我想,那些在世界上转悠的自行车,将由于他的智慧而变得神奇。他以其自己的方式成了一位英雄。
安诺尔·尼马科也有着某种英雄的东西:他像一座雕像似的在那里主持着博览会里最令人悲伤的展台。灯也一直关着,以便使效果完美。书架上摆着的似乎是一些教堂公报,封面上连一张照片也没有,只有素描画。书名诸如《鹰和鸡》、《大象跑哪里去了》、《喜爱柑橘的利齐尔》。是加纳的出版社,由八家国家出版商组织在一起,由政府出钱送到法兰克福这里来的。尼马科是一位政府官员。他为自己在那里关着灯同书在一起而感到骄傲。我不信任地问他,那些书是否卖掉了一些。他大笑起来,回答说:没有。为什么?他说几乎都是儿童书籍。他对我解释说,如果你想要一棵高大的植物,你就应当在它还是幼小的时候特别注意浇灌它。我想,第三世界也各有其作为的方式。当我告别尼马科而走到邻近的展台的时候,我确信这点。孟加拉出版商展台灯光极为明亮,在墙上挂着耀眼的大挂历,挂历上的女孩子们有着杏仁眼和高高的乳房。那不是画的,而是照片,似乎是立体的。的确,各有各的方式。
/* 21 */
星星,条条,蘑菇番茄酱
钢琴科学家
世界当然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去想,但是,波利尼①把贝多芬的奏鸣曲集中在一起,这可是非同一般。不管那会使人觉得是多么愚蠢的事,但那是发生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认为是一段次要的、外围的历史,但那是历史。就是发生这样的事。
①毛里奇奥·波利尼(1942…),意大利钢琴家兼乐队指挥。1960年获华沙肖邦音乐比赛奖译注。过去,听波利尼的演奏曾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奇妙经历,绝对的。这是说七十年代。那时有人像上帝那样在外面演奏,但是如果你碰到一场他的音乐会,那么你听到的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从那黑色大动物里弹出来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如果想要给那一切找个名字,你就会想到:科学家。他是科学家。他在发出音符中的完美和干净,是其他地方所听不到的。即使是乐谱写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密密麻麻,你也能听清所有音符,而其他人则会用没有区别的、诗一般的声浪来对付过去:他却让你听到所有音符,仿佛在读出一种化合物的成分。如果有把一个符号变成字面上的音响的一种方式,而又没有感情用事或者侥幸处理,那就是他的演奏方式。像任何一种科学那样,它也似乎是不人道的。其他人延长和缩短时间,用踏板来走私艺术,添加油彩,弄脏这里和那里,故意这样做或者出于需要;他却是绝对忠实于原作,着迷地尊重节拍,彻底拒绝任何模仿做法、感情用事的转调、表情方面的混乱波动。进入他手里的东西,出来已经过消毒了。他演奏肖邦的作品,似乎是在少有的一个晚上因稍有一点感情波动而被喝倒彩的一部巴赫作品。他演奏舒伯特这位怀旧天才的作品,就像是在听一位从不认识死者的优秀演说家所致的悼词那样。如此说来,似乎是令人不愉快的。但是,如果说,他演奏的比那写着的东西一点也不多,这是真的话,那么,他演奏的一点也不少,这也是真的:而在这方面,他是最伟大的人。那音乐原来的东西一点也不丢掉。其全部给人深刻印象的力量都还给了你,这是由于他善于把完全清洗干净的东西奉献给你,没有任何个人主观的改变,你的激情是一种盲目而无限的真实性的激情:并不认识的激情。已经沉醉在梦幻之中和淹没在内在迷宫的欲望之中,最后到了波利尼的面前,发现了能够产生纯粹现实的那种潜力,只要你让它原汁原味。我发誓,那是一种激情。
后来发生了一件似是无关却有关的事情:他们发明了光盘和数字录音。无论是听还是演奏的效果完美,便突然变成更为容易和几乎必须做到的事情。对于一位年轻的钢琴家来说,像鲁宾逊整个一生所做的那样乱七八糟的事情来使世界着迷,今天是不可思议的事。而对于今天的听众来说,则已习惯于在音乐厅里期待受光盘教育而习惯的那种干净和准确。在波利尼身上作为独一无二的奇迹的东西,今天已变成演奏实践的必要前提。好像被集团所吸引的一位自行车赛车手那样,波利尼多年来一直处于一种宝贵的半明半暗的地位之中,继续走他的路,科学家的苦行僧之路,很少去迎合正在他周围形成的新的娱乐思想。我对他的最后的见面记忆是在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演奏的一场《帝王》,我记得好像是阿巴多①在指挥台上。作为几百年都是波利尼的忠实崇拜者,我要说,我的记忆是:极为厌烦。
①克劳迪奥·阿巴多(1933…),意大利著名指挥家,曾先后担任米兰斯卡拉歌剧院、伦敦交响乐团、芝加哥乐团、柏林爱乐乐团的指挥译注。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想到会是那样的结果。观众有其路数,他也继续走他自己的路。你可以打赌:他们迟早会再相见。带着这种想法,上星期天我去了斯卡拉歌剧院,去听首场马拉松式的贝多芬音乐会。我想发现多年前曾教我懂得想干净意味着什么的那位惊人的科学家情况如何。
当我进去时,跟过去是一样的,他不上台去,而是向我们跑来。这是我一直喜爱的他身上的一件事:因为当他最后再出来时,他以缓慢而疲劳的脚步这样做。但是当他进来时,他跑着来,似乎是不愿让任何人等待,或者是因为他感到急躁,我不知道。不过我喜欢原先和后来不一样的那些钢琴家,因为在他们身上写着:中间发生了某种事情。面孔也总是那一张面孔:仿佛是一分钟之前他们把他叫醒的,像被大灯照着的一个人,模模糊糊地毫无防卫,感到十分尴尬。他们一般来说都有那样一张面孔,而他们却是些天才。他坐在凳子上,开始忙碌着,把凳子升高,又把它降低,最后又把它放到原先的位置上。当他开始演奏时,突然一下子就开始:好像是解放了一样。
①格伦·古尔德(1932…1982),加拿大钢琴家译注。使你吃惊的第一件东西是你听不到的那东西:过去的那种明显的完美。也许有,但事实是,再没有过去那样突如其来地让你感觉到。只过一会儿你还感觉到,那是一种基本的钢琴演奏方法:基本音调色彩少,采用一些基本强弱法,而毫无细腻的东西,毫无小游戏、点缀、魅力,仿佛是选择了一种几乎是原始的坚硬材料来加工:石头。一种石头贝多芬。然后你逐渐地感觉到,所有那没有的东西,不只是不存在,而且以某种方式被吸入了你所不曾期待的一个漩涡之中,你从开始忍受着,而后渐渐地对准了焦距:最终你看见了这个漩涡。这是一种力量的突然爆炸,它在音乐里面燃爆,并以其冲击波打击每一个音符。一个人并不习惯于想到,开头的那些奏鸣曲里面会写着这样的强度。并不是克莱曼蒂式的一些小玩意儿,而是、并且永远是十八世纪的东西。而就是波利尼,他没有动原来所写的东西的一个标点符号,只是在可能的地方加进了你无法想像的整个强度。你们看,这并不是弹奏得强点或者快点的这类平庸问题:他能使人觉得那慢速的极轻的弹奏法有一种惊人的强度。不仅是觉得这样,而且就是这样。而当他无限地加强那些音符的时候,你听到的音乐在冲击波作用下跳动一会儿,而后又立即严密组合,监管着爆炸,给它装上铁甲。真是天才。的确这是一种杂技。古尔德①(比方说)让地雷爆炸了,就在那中间,在圣母那里,而最后的结果,就是废墟。漂亮,但是废墟。而波利尼,用左手点燃导火线,用右手把铁甲大门锁上,整个儿爆炸了,但什么都没炸碎。你想想就会明白,贝多芬就是那里的那个东西。人们发现,人类本身具有十八世纪不想认识的巨大强度:当时是试验这种巨大强度,去找到它并使之爆发,但是一切都好像在一个试验室里,也就是在一种能控制的局面中,不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就像是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是感情科学。
我自问,当波利尼演奏到最后的那些奏鸣曲时,也就是在那些奏鸣曲中爆炸已经不那么地下的时候,将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般的听众也将能看到它。我自问,怎么样才能做到与那下面的进程同步。将于二月份发生,我将要去听。我也带着好奇心去看看是否将重新出现在听他演奏前面一些奏鸣曲时使我吃惊的第二个东西:从那黑色大动物中向我跳出来另一段贝多芬作品,我从来就没有非常清楚地看到它。这是贝多芬的呼喊。
原先已经直觉到了,而当星期四波利尼演奏了《悲怆》的时候,我就有了清楚的概念。如人们所知,以慢板序曲开始,以美妙的技巧加强。我总是觉得那是一种庄严的东西,一个设计精明的大门。我要重复说,这是一种美妙的诡计。而现在我听到了波利尼演奏打开那扇大门的那几组和弦。然后同样的那几组和弦又回到了接着演奏的刺耳的快板,这快板就像是对一个记忆的突然袭击。我以为简单地只是一些记忆。波利尼演奏它,那是恐慌,绝对的害怕:悲痛欲绝。那根本不是什么诡计:他在呼喊,被关在他的什么笼子里,监狱里,疯人院里,谁知道呢。那是优美而善良的呼喊。你再想想,你就会明白,贝多芬正是在那里的那种东西:把一种痛苦呼喊的初步经历包装在试验炸弹的一座宏伟建筑里的一个人。在那座建筑周围修建了一些主教堂,以便隐蔽它,使之合理化,以便战胜它,使之新陈代谢。但是,如果你下到教堂地下室墓穴里,你所感到的则是:一种痛苦的呼喊。我喜欢看见那位表面上不人道的、惊惶失措的科学家一直下到那下面来,让我听到那痛苦的呼喊。
今晚有另一场音乐会。还有作品二十七第二乐章,人们所熟知的《月光》:其开头便是轻而易举的激情的撞击,对浪漫垃圾的一种预言,在废糖蜜中旅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