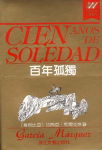孤独行走-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把我带到这里的主人名叫斯格勒玛,六十多岁,养育了三个儿女。两个儿子已成家立业,只有最小的女儿巴娜玛还未出嫁。她从高中毕业起就去了海拉尔闯世界,曾教过书,打过工,开过饭馆,如今饭馆也开不下去了,就带着一位城里汉族小伙子(她的对象)回到草原的老家,帮助父母打草。
秋季,是牧民一年中最繁忙,劳动强度最大、最辛苦的季节,要打到足够的草料以备牲畜过冬。他们吃住在草甸上,夜晚还要忍受蚊虫的叮咬。这可难为了巴娜玛的汉族对象,他整个是一个废人,什么活儿也不会做,斯格勒玛老两口儿打心里不满意,但不满意也只能放在心里,现在女儿家可不比以前好管了。巴娜玛与她的母亲是两个时代完全不同的女人,巴娜玛思想前卫,紧跟时代,但浮躁,急功近利,因此,她的青春路走得很不平坦。
早年的斯格勒玛是苏木(乡里)的妇女主任,从二十多岁的青春年华起,一直干到五十多岁才退下来。她耿直、待人热忱、性情温和、坚毅,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和人缘,是出了名的女强人。用她的话说:这全是用真诚干出来的。斯格勒玛家住的是三间砖房,房顶上盖着石棉瓦,东房住着老两口儿,中间是仓库,西屋则住着新婚不久的小儿子夫妇。屋内家什简单,都睡铁床,一切打理得整整齐齐,这对游牧民来说,算是上乘的条件。斯格勒玛家养的牲畜数百头,羊三百只、奶牛四十二头、马八十九匹,这些,都是她家的命根子。之所以养这许多羊,是因为羊的产出周期短,经济效益来得快,但羊对草原生态系统的破坏相当严重,甚至是自杀性的破坏,它们吃草的习性是连根拔的,从不留后路。近些年来,牧民们受到利益的驱使,羊的只数只增不减,斯格勒玛谈到这里时,也只能是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养奶牛经济周期相对较长,需要足够的耐心,好在每日挤的鲜奶可以换来现钱。而养马主要是为了解决交通和食肉。
自打我来到的那天起,草原上的天,就像漏斗一样阴雨不止,无法走动和拍摄。这却挡不住牧民们的日常劳作。斯格勒玛一家人,每日早晨四点左右就起床去牛栏里挤牛奶,近两个小时才能完成这一工作,然后把整桶的带着母牛体温的鲜奶,一桶桶搬到牛栏外,等着收奶车拉到城里去加工,通常每斤鲜奶能卖上一角多钱,每天能挤上几十斤,刚好贴补日常生活。
他们家的早餐多是馒头和油饼,再配上香喷可口的奶茶,直喝得周身冒汗,五内通畅。而用羊肉、羊下水和草原上野韭菜做馅的“布力亚特包子”,更是吃了令人难忘,它皮薄,肉多,香味扑鼻,是布力亚特人款待贵客必不可少的传统食物。只要吃上两三个,足够饱上一天。
到了傍晚天色擦黑时,她们还要去牛栏挤一次鲜奶,这样,一天的活计才算忙完。
平日里,男人们都去了自家的草甸上割草,女人们管理着家庭和照料牲畜,还有制作不完的针线活,布力亚特人至今仍保留着穿戴自己手工缝制的衣裙衫裤的习惯。所以,布力亚特妇女个个都是女红能手,难怪她们从城里买来那么多布匹。虽然布力亚特妇女不会像苗族女人们织布刺绣,但她们却有苗族妇女不会的制皮手艺和赶羊毛毡毯的技术。你说这是智慧也好,勤劳也罢,她们就是这么一辈一辈传下的习惯,她们认为没啥好夸奖的。
在布力亚特人中间,妇女是家庭中的支柱和灵魂,也就是说,每个家庭的兴衰,全是由妇女的能干与否决定的。斯格勒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她的男人,自打和她结婚之后,就养成了好酒的习性,且嗜酒如命,每酒必醉,不难想像那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可斯格勒玛却能一手撑天,家中的私事和苏木的公事,从没落下任何事,样样都做得无可挑剔。她是位优秀的草原母亲,她脸上所表露出的慈母般的神情和聪慧精干,让人感到她始终生活在一种自信中。即便如此,你没听到一句豪言壮语;她的心境如呼伦湖一样的沉静与博大,像草原一样的辽阔与宽广。
二十五年前冬天的一个深夜,她为了寻找放牧未归的丈夫,冒着越下越大的暴雪行走了二十多里路。终于在凌晨时分,在茫茫雪野中,找到了醉倒的丈夫和羊群,他(它)们已冻得奄奄一息。无奈之中,斯格勒玛放弃了羊群,硬是把丈夫从死亡线上救了出来。之后,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她是如何连拖带背地把丈夫从齐大腿深的暴雪中,冒着随时被冻死的可能,忍着刺骨的严寒和饥饿,又走了一天零半夜才回到家中。那时的小巴娜玛,哭嚎得只剩下一丝声音,眼巴巴地盼着斯格勒玛回来喂奶吃。那次生死经历后,斯格勒玛在草原上的威望更高了。她对我说:“当时有几次我都坚持不下去了,心想着只有一岁的巴娜玛不知是冻死还是饿死,两个大孩子去了十多里以外的姨妈家,根本就不知家中的事。那心里真不是滋味……后来,就那样忍着,坚持着,坚持着……也就回来了,我家那口子差点冻成残废人。”这就是草原妇女的刚毅性格。
又是一天的早晨,一阵西北风吹来,把天上的乌云全带走了,湛蓝的天空还飘着几片鱼鳞云,一轮红日在雨后的草原上升起,它显得那样温暖和亲切,我心中不觉充满对大自然的感恩之情。
昨天,斯格勒玛从其他几个牧民点上邀来了乌日金、斯布勒、斯里格玛和达丽格玛四位妇女,她们个个都是当地有名的制衣能手。这是斯格勒玛出的主意,她们要亲手为我这远道来的贵客,做一身只有新郎官才穿的布力亚特男人盛装送给我。没有电熨斗,就用铁制的土熨斗在炉火上烧热来熨衣;没有尺,就用木板替代,惟一一件现代用品,那就是上海“飞人牌”手摇台式缝纫机。看着她们认真、投入、专注的神情,你会感到她们的真诚。眼看着一套崭新的服装就要制成了,她们脸上充满创造的幸福感,竟情不自禁地齐声唱起了本族民歌,那歌声充满自信、坚毅和奔放,有着极富内涵的游牧气质。歌中内容大多是歌唱母亲的,可见女性在布力亚特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血红的夕阳终于掉进了草原的尽头,又一个黑夜来临,仰望满天繁星,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博大和布力亚特人火一样的热忱。斯格勒玛老妈妈帮我穿上她们精心制作好的新装,人们一下掉进了欢欣的氛围中。主人点起烛火,人们合唱古老的歌谣,跳起了只有布力亚特人才会跳的民族舞蹈。
直到深夜,欢乐的歌声仍然回荡在草原的星空中。
几天后,我带着布力亚特蒙古人的深情厚意,带着草原母亲的慈祥与博爱,带着斯格勒玛和她的姐妹们为我制作的新衣,又回到了车水马龙、喧嚣浮躁的都市,但我的心却留在了那片溢满母性光辉的草原上。
第五部分黄土塬上的巧婆娘
在陕西省中部洛川县的黄土塬上,有位远近闻名的巧婆娘——杨梅英。
2000年,我选择在春暖花开的季节,按照当地人的指点,在县城南的一个用青砖修造的窑洞里,找到了我要拜访的主人家。这种自打北宋末年就有的“穴居”,在黄土塬上一直沿袭至今,它经济实用,冬暖夏凉,很舒服。杨梅英家的庭院,足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里面种满各种蔬菜和花草果木,房里屋外打理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一看便知这家的主妇是个“撒利”(勤快)的人。
六十一岁的杨梅英,比我想像中的要年轻得多,身材高大,面和心善,是那种很易接近的人。她之所以远近闻名,是因她擅长做面花(面塑),前些年又改做了捏泥人。不仅如此,民间剪纸、刺绣、农民画等与当地民俗有关联的活儿,她样样精通。可别小看不识多少字的杨梅英,她创作的这些土里土气的玩意儿,被选送到省、市,甚至国外去展出,她还被邀请到日本、中国香港去访问和进行才艺表演,所受到的广泛赞誉自不用说,乡亲们都很羡慕,可她自己却从没把这当回事儿。
“我这人心胸宽得很,财和名算个啥?人活着,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才是宝!你看,我六十多岁的人了,头发黑亮亮地,眼不花,耳不聋,你说,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我们刚刚见面,杨梅英就扯开大嗓门,干脆利落地打开了话匣子。可见,她是一个开朗而又健谈的巧婆娘。
“那你啥时开始喜欢上了这些民间艺术?”我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们黄土地的农民,男人劳动一辈子,就是为了能修上几孔窑洞,有了窑洞,娶了婆娘才算是成家立业哩。男人刨挖黄土地,种庄稼,而女人就在土窑里操持家务、生儿育女,还要寻思把自己的日子搞得美美地,让劳累的男人看了心情愉快哩嘛,这也显示着咱们农家人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地,让人看了喜庆,不‘坷碜’。我们不知道啥叫‘民间艺术’,那是你们公家人说地。我们不识字,只知道这么个弄好看,能把我们心里地喜怒哀乐表达出来,把想说的话变个样样子说出来,这样看着就是美,心里头就是舒坦。人是见笑就喜,见哭就悲,好事、喜事想得多了,看得多了,你的心情也就快乐了。人是感情动物,人心做梦都是想着好事哩。你说,你为啥到我这儿来?不就是想看美的东西。我们过去捏面花、剪窗花并不是为了卖钱养家口,也不是上贡给谁,我们就拿这铰衣服的大剪子,自由自在地,想剪啥就剪啥,想损坏个啥模样就是个啥模样。你问它们有啥子意思?那可多着呢!都是咱们生活中的事儿,心中的盼望,精神的寄托……”
如今,她每天创作不止,而且经常接待慕名前来访问的中外客人。她过去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随便弄起的玩意儿,如今能换钱,贴补生活。用她的话说:“我弄啥像个啥,每件东西里面都是有说头地,全是我们当地老百姓日子的事,反映美好的心愿,祈福地希望,纳祥地兆头。谁知道,耶们城里人和外国人也信这个,耶们来看了(作品)欢喜地了不得,像是见了宝贝。那年来了两个意大利的客人,见了我的作品之后,又是唱,又是跳,那个高兴的劲儿就像是疯了似的,他们说我的作品像什么‘斯’,对了!像外国的艺术大师‘马蒂斯’!我才不管什么是‘马蒂斯’、‘羊蒂斯’呢,我就是怎么想就怎么做。最后耶们走时硬要买我地‘艺术品’,说是带回去收藏、宣传哩。我说:这些土里土气地,有啥好收藏地,想要就送你,人家毕竟是远道来地客人嘛。可耶们硬是把钱给留下了,说是尊重艺术,尊重劳动。既然这么个,那我为啥不收钱,这就好像把喜事、美事卖给了人家。是好事,是善事,是积德的事,你说对呀不?”说着,她就从炕席下边拿出一叠剪纸,当她展开在宽大的炕上时,我一下看呆了,这并不是我平日里在陕北看到的巴掌大小的窗花花,而是用整张整张的大红纸、黑色纸剪成的剪纸作品。那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使我禁不住地往后退了两步,这才看清作品的全貌,像这么大幅的剪纸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你看这幅是《双凤献子》,左为凰,右为凤,双双捧着石榴子(民间寓意:多子)献给人间,石榴体内的童男童女正在玩耍呢,旋纹地是男,舒长袖地是女。”“你再看这幅,看,外面一圈是条蛇,中间坐个乖乖兔,这叫‘蛇盘兔’,你家里人如果有一个属蛇和一个属兔地结姻缘,那你家地好事数不完,每年必定富。兔的性情善良地很,人见人爱,跑起来欢腾腾地。蛇把它这么一盘,这意思是说:好东西就跑不出去了,财富都能留在屋里头。我们农民叫这是‘蛇盘兔,年年富’。”
好一个出神入化的想像力!我们知道,蛇在古代部分氏族中,被视为力量的象征,万能的“神”物,在人类早期的生活中,作为图腾加以顶礼膜拜。又因它与龙图腾特别相近,因而,蛇的形象在陕西的民间备受推崇,代代相传。至今,它的图腾概念通过妇女们的巧手,逐渐演变成了祥善和财富的保护神。
说起陕北地区的民间剪纸,那是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积淀的,它与黄土地上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与人们的生存习俗密不可分。同时它又是女人专属的手艺。每逢节庆年关,那塬上川下的星罗棋布的土窑洞的窗户上都会贴满各种各样的窗花,把那单调的黄土地装扮得分外红火,生气勃发,可以说家家户户都是个剪纸展览会。除了窗花,还有炕围花、窑顶花、家什贴花,甚至在筷子篓上也要贴上吉庆的花样。这是长久流传下的当地的浓厚的民俗、民风,因此,陕北的妇女几乎人们都会剪纸。但绝大多数妇女都是“替样”(依照传统的纹样)剪纸,这样省时省力,是传承者,而非创造者。据了解,大概有千分之一的妇女,具有“冒铰”(创造性剪纸)的天赋,成为佼佼的巧人儿。乡间的婚曲中就有这样的唱句:“生女子要巧的,石里挑一的“巧女子”的典型代表。
“你是啥时开始捏了泥塑?”我问到。
“我原来是做‘面花’地,但是面会发霉,会开裂,留不住。人家客人带了去,无法收藏。直到前些年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着很多黑鬼、白鬼到我屋来讨债,说是我一辈子做面花,浪费无数粮食,是犯罪,要拉我到阴间问罪示众,吓得我浑身大汗,当我就要被这些鬼拖往阴间时,忽然,一位身穿大红袍地白头翁,急忙上前来搭救我。他说,黄土高原上有取之不尽的黄土,你只要保证从今以后改用黄土捏泥人,就可免你一死。打那梦以后,我真乖乖地用了泥巴来做泥人。这下,比用面粉做出来地东西还有灵性,我捏起来更顺心顺手,样数也变多了,摸索地经验也丰富了,还能用低温烧制(不易破损),外人也更喜欢了。把面粉省下之后,那些黑鬼、白鬼再没有来梦里过。一个梦把我给救下了,我要好好地捏泥人报答,你说是呀不!”
说话间,杨梅英带我来到东窑前。打开门一看,嗬!窑里到处堆满了黄红色的泥塑作品,大的有二三十厘米,小的有十厘米左右。
“这都是美国人来订下地货。”
杨接着说:“这材料全是用咱们当地的泥芯土,拿箩过后,和水捶,再捏成形,烧完就变红了。你看这件,叫‘抱鸡女娃’,女娃长大时就必须嫁人呀,她抱只鸡,就是吉利,做啥事都顺。咱们这儿的人结婚时,都要叫童子抱个大红公鸡,女婿来时,丈母娘还要给杀个鸡……都是这么个意思。你再看,这个‘饱奶媳妇’地奶被我捏地特别大!她是在地里做完活,往回走哩,奶局(涨)了,一跑动,就乱甩,她就用手扶着舒服。我们这里娶下媳妇后,她生了娃,首先要看她地奶美不美,她地奶下来没下来,奶大,奶水就足,这家的娃身体保险好,就健康哩!就没有小毛病。女人一结了婚就不知害羞了,走到哪里都敢把奶扶出来奶娃。这就是生活地规律,一点都不是啥怪事。”
艺术理论认为,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给人以美的享受,给人以灵魂的净化……也许杨梅英并不懂得这些艺术的
![[人文]行走中的玫瑰 作者:闾丘露薇封面](http://www.iixs.net/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