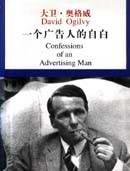狗小的自行车-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物发生了兴趣。那位青年作家开始收集素材时,他父母向他推荐了郑土根。他们说了解林隐火的人差不多都去世了,只有土根公到现在还活着,他是亲眼目睹过林隐火的,你去向他打听准不会有错,他的讲叙应该是最具权威的。
那位青年作家找到郑土根时,郑土根正在村口食品店前晒太阳。那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新春。跟郑土根一道晒太阳的有好些人,包括林隐火的儿子郑木宝。那些人正兴味盎然地聊着邻村一桩公媳风流韵事,年迈的郑土根没有参与他们的话题,孤单地坐在一旁打着自己的瞌睡。他认为那是年轻人的话题,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青年作家喊醒他,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坐正了一下身子,开始让自己进入回忆。他讲叙了林隐火进村时的情景,讲叙了林隐火英俊的长相,讲叙了林隐火收租时的凶狠,讲叙了林隐火要毙了郑阿保的动机,以及林隐火被打死时的细节。整个过程中,他只字未提郑秀红,好像郑秀红压根儿没在那事中存在过。
在郑土根细细讲叙的当儿,郑木宝插话进来回忆了踢骷骼头的情节。他富有激情的插叙,使郑土根感到莫大的欣慰,他在心里暗暗地笑了:木宝呀,木宝,你当初踢的可是你爹呀!不过,那个隐私不会再有人知道了。这时,以往的一切对郑土根看来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林隐火的儿子将永远成为自己的儿子,林隐火的后代将永远成为自己的后代!
青年作家采访后的第二天,郑土根就无疾而终了。
后来,那位青年作家根据收集到的素材,创作了一篇题为《隐私》的短篇小说。为了使更多读者对那篇小说发生兴趣,他虚构了一段郑秀红跟林隐火私通,并生下了一个野种的故事。这样的虚构无意之中恢复了事实的真相,使这篇小说几乎成了对那个隐私的真实记录。这也许是郑土根说什么也预料不到的。
第二部分:寻找“把柄”寻找“把柄”(1)
厚忠走进镇政府时,想里面住着的都是些比村支书大的“官”,心头便涌上了一份农民固有的根深蒂固的胆怯。
厚忠虽说五十多岁的人了,但进每次上街都要路过的镇政府,还是头一遭。
厚忠是个安份守己的农民,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是不大会来这住满着“官”的镇政府的。厚忠来,是来找分管土管的秦镇长的,他有事求他解决。
厚忠循着别人的指点,来到一间半关着门的办公室前时,心跳着很厉害,犹似一匹脱缰的野马。但厚忠想自己不能便宜了土根家,便状状胆,抖索着手,敲响了门。
门敲响的时候,秦镇长正瘫坐在豪派的皮转椅上,撕咧着阔嘴,用牙签剔着牙缝里的肉屑。见进来了一个土里土气的农民,就正襟危坐好,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官”的模样,直视着厚忠,打着官腔问:“你是哪个村的?找我有什么事?”
厚忠还是第一次见秦镇长这么大的“官”(电影电视上的不算数),便手足无措地愣在那里,涨红着脸,说话一下子结巴了。可他还是很不容易地讲明了来意。
秦镇长从厚忠的话里“删其糟粕,取其精华”,弄清了厚忠来的目的——厚忠邻居土根家在他家的道地里造了一间猪舍,厚忠希望镇里能出面调解。于是,皱了皱眉头,不悦地说:“这样的小事也找镇里?”
厚忠听了,苦着脸说:“这事我向村里反映过,村里不管。因为土根是村支书的舅舅,他们有亲。”
秦镇长就“噢”了一声,停了会儿,打发厚忠说:“这事我知道了,你先回去。”
厚忠回家后就盼月亮盼星星地等,可五六天过去了,仍不见有人来调解,而且连一点风声都没有,于是再也按捺不住,又一次去了镇政府。
这次,厚忠内心的慌乱比上次锐减了许多。之所以锐减,是因为厚忠有些生气,想秦镇长身为镇长,怎么说话这样不作数!
秦镇长见了厚忠,觉得有些面熟,但一时记不起在哪见过,再看他那土里土气的样,也就懒得去想,打着官腔问:“你是哪个村的?找我有什么事?”
厚忠听了不由一怔,暗里寻思:我来过还不到一礼拜,他怎么就忘了?真是贵人眼高!于是又将土根家霸占自家道地造猪舍那事,一五一十地复述了一遍。
秦镇长恍然大悟,但明知故问道:“噢,是那事。现在还没解决?”
厚忠就一脸苦相地说:“还没有呢!”
秦镇长又装出惊讶的样子,说:“村里不管?”
厚忠无奈地回答道:“他们才不肯来管呢!”
秦镇长就错开目光,口气淡漠地说:“村里不来,总有村里的道理吧!”
厚忠一听,心一下子冷了,愤然地说:“村里不管是因为土根是村支书的舅舅!”继而,软着口气央求秦镇长,希望镇里能出面调解一下。
秦镇长听罢,禁不住讥笑了一声,说:“像这样的小事,全镇不知有多少呢!如果都要镇里去调解,镇里的人不累得吐血才怪呢!”
厚忠还想说,秦镇长就不再搭理,顾自打私人电话。
厚忠知道再说也没用,只好闭上嘴,怏怏地离开,心里一个劲地骂:官官相护着呢!
第二部分:寻找“把柄”寻找“把柄”(2)
就在厚忠对道地被霸占一事失去信心时,厚忠家的一个亲戚得知了此事,给厚忠出主意。
那个亲戚说:“人家霸占了你家的道地,村里镇里都不管,你将那家的猪舍钯了不就行了!”
厚忠听了,连连摇摇头说:“这怎么行?!他家有三个牛高马大的儿子,我只秀英、秀凤两个女儿,我去钯,他们不把我打熟才怪呢!”
那个亲戚就又想了想,说:“既然这样,那只得靠村里出面解决了。”说完,问厚忠能不能抓到一些村里的“把柄”。
说起“把柄”,厚忠的眼睛蓦地亮了亮,脑海里浮现起了一堵墙。
那堵墙是一堵围墙,筑在村委对面河那边的田里,有二百多米长,里面围着好几十亩良田。五年前围起来的时候,村里是准备用来挖塘养鱼的,结果镇里不同意,要村里拆掉还耕。可村里觉得那样有失面子,便既不挖塘养鱼,也不拆墙还耕,一直荒芜着。
厚忠问,那堵围墙算不算“把柄”?
亲戚说:“你最好先打个电话去县土管局问问,他们认为村里这样做不合理,那就是‘把柄’了。是‘把柄’,你可以用它来要求村里为你家解决道地被霸占那事。他们如果不管,你就说要将筑墙抛荒的事反映上去。我想村里不会傻到‘丢掉西瓜,捡芝麻’的。那事捅到县里去,影响大着呢!”
厚忠听亲戚这么一说,心里舒坦了很多。
第二天上午,厚忠就打电话给县土管局,问村里筑墙抛荒的做法是否合理?
接电话的人问厚忠:“你是哪个村的?”
厚忠本想不说,又怕不说那人不肯告诉他,就如实说了。
那人就答复厚忠说:“从你的反映看,你们村里那样做是不合理的。但我们没有实地查看过,不好下结论,你是不是先去问一声你们镇分管土管的镇长,他如果认为不合理,你再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采取措施的。”
厚忠放下电话,欣喜地去镇政府。
厚忠走进秦镇长办公室,秦镇长刚打着官腔又要问:“你是哪个村的?找我有什么事?”见是厚忠,顿时打住了话头,厌恶地说:“你又来了!为那事?”
厚忠笑笑,镇静地说:“不为那事?”
秦镇长瞅厚忠的眼神便有些异样,他不解地问:“那又为了哪事?”
厚忠就一字一顿地说:“我是来问您事的。”紧接着讲了村里筑墙抛荒的事。末了,强调说:“这事我已向县土管局反映过,他们要我先到您这里问一下,再让我打电话过去……”
话未说完,秦镇长紧张起来,不再纹丝不动地瘫坐着,赶紧站起身,替厚忠让座、沏茶,并讨好地说:“如果你有什么难题,我一定会帮忙解决的。”
秦镇长明白:厚忠若将筑墙抛荒的事反映上去,对自己非常不利!虽说厚忠所在村筑墙那年,自己还未调到这个镇,当时分管土管的是王镇长,要厚忠所在村拆墙的也是王镇长。问题是那事发生不久,王镇长就调走了,是自己接替了王镇长的位置。而更让秦镇长担心的是,他准备着手处理厚忠所在村筑墙一事时,厚忠所在村支书送了他一份厚礼。为此,他彻底放弃了处理那事。现在,万一厚忠真将那事捅上去,上面怪罪下来,他这个分管土管的镇长无疑要承担责任,搞不好还会“东窗事发”——受贿被揭露,那样自己的前途可就完了!
厚忠瞧着秦镇长的紧张样,明白自己一旦将那事捅上去,他这个分管土管的镇长也逃不了干系。于是,说话的口气粗起来:“我这样做,不是成心要跟村里过不去,只是村里也真他娘的不识相!明明是土根家霸占了我家的道地,可他们就是不管……”
秦镇长听着,连连点头,表示认同。
等厚忠发泄完,秦镇长信誓旦旦地说:“土根家霸占你家道地的事,我现在就给你村里打电话,叫他们尽快解决。至于你们村筑墙抛荒那事……”
厚忠知道秦镇长要说什么,立马抢过话头,拍了拍自己的胸脯,保证道:“那事解决了,筑墙抛荒那事,我屁也不再放一个!”
第二部分:寻找“把柄”寻找“把柄”(3)
厚忠初战告捷,踌躇满志地回家去。
刚跨进门,油桶般肥胖的村长就跟脚进来了。
厚忠见是村长,冷着脸不搭理,那情形恍如跟进来的是一条狗。
厚忠很瞧不起村长。而且也不只厚忠一个人瞧不起村长,全村人都瞧不起村长。如果说村长在当村长之前,是一个好人。那他当上村长之后,就彻彻底底地变了,成了村支书的一条走狗。他在村里没有一点权力,村支书要他往东,他不敢向西,村支书叫他朝前,他就不敢退后,完全傀儡一个。厚忠家的道地被霸占后,厚忠曾向他反映过,可他惟恐惹怒了村支书,丢掉“村长”的宝座,一直不理不睬,这很让厚忠憋了一肚子火。
村长尴尬地站了会儿,开口说:“厚忠,我已来过两趟了,你都不在。刚才秦镇长来了电话,要我们为你家解决道地被霸占的事。我已经去土根家说过,要他家在三天内拆掉猪舍,否则后果自负。”
说完,偷眼瞟了厚忠一眼,见厚忠依旧阴着脸,又解释说:“当初你向我反映那事,不是我不想帮,只是你也知道我在村委没啥权力,村里的事全由村支书说了算。村支书那人,你不是不清楚,狠着呢!筑墙抛荒那事,就是他出的主意。当时,虽说我也在场,可我屁也不放一个。那事万一闹起来了,你可别将我牵连进去呵!看我这块头,要有一天当不成村长了,真不知还能干什么呢!”见厚忠还是不作声,只好心怀忐忑,灰溜溜地走了。
厚忠原以为大功告成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土根家的猪舍欲拆前的一天,县土管局突然派员来查看村对面河那边的那堵围墙了。
他们查看后,确定厚忠反映的属实,当下就指令村里限两天内拆除,并要求村里下季还耕。
厚忠搞不清自己没有再次打电话去,县土管局怎么就来采取行动了呢!他望着那堵被越拆越短的围墙,心头袭上了一阵又一阵的绝望,暗想随着那堵围墙的拆除,拆土根家猪舍的事可要泡汤了,便后悔当初不该说出自己是哪个村的。
果真如厚忠所料,第二天,土根家说定拆除的猪舍没有拆。
厚忠想,村里筑墙抛荒的事自己并没有再次去反映,是县土管局自己来的,不能怪自己;而拆猪舍那事,说定了的,也不能因此就算了。于是,在路上碰见村长时,生气地问:“土根家说定要拆的猪舍怎么没拆?”
村长见问,白了他一眼,鄙夷地撇撇嘴不作声,兀自摆动着肥胖的身躯,走自己的路。
厚忠还是不甘心,又动身去镇政府找秦镇长。
秦镇长见厚忠又来找自己,就趁厚忠还未跨进办公室之际,起身过去,狠狠地踢上了门。
秦镇长几乎是恨透了厚忠这个出尔反尔的“刁民”。为了那事,他不仅挨了县里领导的训,年初想再上个台阶的望头也成了泡影。当然,惟感幸运的是,自己受贿的事终于没有“东窗事发”,要不,他真伤在厚忠的手上了。
厚忠吃了个“闭门羹”,感到非常委屈和愤懑。他别转身,气冲冲地走了,心里却暗暗发誓:自己绝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以后,厚忠经常在村里遛哒。
村里人见状,困惑地问:“厚忠,你在干嘛?”
厚忠信心十足地回答说:“我在找‘把柄’!”
这样说的当儿,厚忠暗里告诫自己,找着了,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说出自己是哪个村的了!
第三部分:诱惑之殇寻找逃入城市的弟弟(1)
十五岁的弟弟说:“我想去城里生活。”
我说:“你书都没念完,怎么可以去城里呢?”
弟弟不以为然地说:“书有什么好念的!”
我说:“书不念好,你以后怎么能找到好的工作?”
弟弟便白我一眼,满不在乎地说:“人家阿林是大学生,书念得好好的,还不是照样找不到好的工作?”
我黔驴技穷了,忙说:“我们先不说那些吧,我问你城里有什么好?”
弟弟盯着我问:“你去过城里吗?”
我一时语塞了,好久结巴着说:“你,你这,这是什么意思?”
弟弟鄙夷地瞅着我说:“你城里都没去过,怎么能说那里不好呢!”话里夹杂着明显的嘲讽。
我无言以对,不再理会他,心里却讥笑他的异想天开!他好好地书不念,竟想去城里生活,真是可笑!
然而,跟我对话后的第二天,弟弟就真的失踪了。我们村前村后、山上地里的寻找了一整天,仍不见他的踪影。
这时,我对苦着脸的父母说:“弟弟肯定跑到城里去了!”
“不会吧!”父亲反对说,“城里路那么远,他会去?再说他书还没念完呢!”
我说:“弟弟昨天跟我说他想去城里生活,他说书有什么好念的。”
父亲凶着口气说:“他书不好好念,以后怎么能够找到好的工作?”
我说:“他说人家阿林是大学生,书念得好好的,还不是照样找不到好的工作。”
母亲气愤地插嘴说:“这小死尸就是歪理多!”
父亲不作声,沉思良久对我说:“那你去城里找找看,他说不定真跑到城里去了。”
我收拾了一下行李,去学校请了事假,动身去了城里。说出来不怕你笑,我都长到十七岁了,可从没去过城里。
我一到城里,便拉住一个行人问:“你见到过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吗?乡下来的,剃着个光头。”
那人深深地盯了我一眼,嘲讽地笑了:“你有没有搞错?你以为这里是你们乡下呀,你仔细瞧瞧,这里人这么多,你找得到吗?”
我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