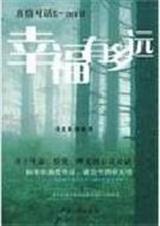幸福之路-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这些部分与在早期创设的某种一般性哲学保持一致。我建议首先去考虑这一哲学,然后再触及它在目前得以普及的理由。
对理性的反抗始于对推理的反抗。在18世纪的上半叶,正当牛顿统治着人们思想的时候,有一种信念流传很广,认为通向知识的途径只是对简单的、普遍定律的发现,由此结论可以演绎推论法得出。许多人忘记了,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根据的是一个世纪的细心观察,他们还想像一般规则是可以在自然的启发下发现的,就有了自然宗教、自然法律、自然道德,如此等等。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只是步欧几里得之后尘,从自明的公理中得出的证据确凿的结论。这种观点的政治结果就是美国和法国革命期间所宣扬的人权学说。
理性的圣殿看来正接近完工的紧要关头,却埋下一枚地雷,终于把这座大厦炸到了半空。埋下这枚地雷的人就是大卫·休漠。他干1939年发表的《人性论》有一个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运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这就说明了他的整个意图,但他只完成了一半。他的意图是以观察和归纳代替从有名无实的自明公理中得出的演绎。以其思想倾向而言,他完完全全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虽然他是属于培根的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变体。但以他学识上的诚实,他的敏锐的几乎没有例证的综合,引导他得出某些破坏性的结论:归纳法是一种缺乏正当逻辑的习惯,相信因果论并不优于迷信。依此,必然有这样的结论:科学和神学一起,被放逐到虚妄的希望和荒谬的迷信的地狱里去。
在休漠那里,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和平地处在一起。怀疑主义仅供研究,在实际生活的事务中却被忘却。而且,实际生活要尽可能地受科学的方法所支配,可是科学却为其怀疑主义所责难。这样的妥协,一个人只能是一半哲学家、一半是深港世故者才有可能;这里还有一种贵族托利党主义的味道,从而把初学者和涉世未深者拒之门外。一般来说,世人都拒绝全部接受他的学说。他的追随者们拒斥了他的怀疑主义,他的德国反对者则强调它仅仅是科学和理性的视野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作为他的学说的后果,英国哲学成了表面性的,德国哲学则变成反理性的——每一种情况都出于对无法忍受的不可知论的恐惧。欧洲思想从来没有恢复它从前的专心致志;在休漠的所有的后继者中间,心智健全意味着肤浅,深刻则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疯狂。在最近关于哲学适用于星子物理学的讨论中,休漠引发的!日争论仍在进行。
德国异军突起的哲学始于康德,而且是作为休漠的反应而发端的。康德决意相信因果关系、上帝、不朽、道德法则,等等,但他发觉体漠的哲学使所有这些变得困难起来。为此,他在“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作了区分。“纯粹”理性关系到可以证明的事物,但为数很少;“实践”理性关系到德行所需的事物,这就很多了。当然,非常明显,“纯粹”理性仅仅是理性而已,而“实践”理性却是一种偏见。这样,康德把那些被认为不属于理论推理领域的东西,又带回到哲学中来,这些东西自经院哲学兴起以来,已从各个学派被驱逐出去。
从我们的观点看,甚至比康德更为重要的,是其直接继承者费希特,他从哲学过渡到政治,开创了后来发展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但在谈论他之前,还要多谈一下“理论”这一概念。
由于无法找到东西抗衡作漠,“理性”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的东西,稍有偏离,就以理论上的理由受到指责。然而,这里有一个差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差别,存在于(比如说)哲学上的激进派和像早期宗教狂那样的心态之间。如果我们把前一种心态称为理智的,后一种为无理智的,那么很清楚,在近代,非理性一直在滋长着。
我认为,我们在实际中所指的理性可用三个特性来加以界定。首先,它依靠说服而木是强力;其次,它寻求以运用的人所确信的完全有效的论点进行说教;第三,在形成意见中,它尽可能使用观察和归纳,而少用直觉。这些规则的第一项可以免除进入宗教法庭;第二项不会采用英国战争所宣扬的方法,对此希特勒大为颂扬,缘由是宣扬“必须根据它所要掌握的群众数目,人数越多越要浅显易懂”;第三项不许使用这样一个大前提,像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提到密西西比时所使用的那样,‘宇宙之神有意让这片大流域隶属一个国家。”这对他和他的听众来说,是木言而喻的,但是对此存有疑虑的人,却不容易明白。
依照这样的界定,信赖理性要设想一个人和他的听众之间具有某种利益和观点的一致。确实,庞特太太想在她的鸭子身上做试验,她唤道:“来吃一刀吧,因为你们的肚子要填满,我的顾客们也要吃饱”;但是一般来说,诉诸理性对于我们想要吞并的人们,被看作是无效的。相信食荤的人们,不会试图去找出对一头绵羊看来是正确的论点,尼采也不会试图去说服他称之为“粗俗和笨拙的”乌合之众。马克思也不会试图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正如这些事例所表明的,当权力毫无疑问地局限于寡头政治的时候,诉诸理性是比较容易的。在18世纪的美国,只有贵族和他的朋友们的意见是重要的,这些意见通常能够以理性的形式展现给其他贵族们。随着政治选民人数越来越多,成分也更复杂,诉诸理性就更为困难,因为为人所普遍承认从而可以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变得更少了。当这样的可能找不到的时候,人们迫木得已依靠自己的直觉;由于集团不同,直觉各异,依靠直觉势必导致冲突和强权政治。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理性的反抗,在历史上是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早期的佛教是有理性的;它以后的形式,以及在印度取而代之的印度教则不然。在古希腊,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是对荷马式的理性的反抗。从苏格拉底到马可·奥勒留,古代世界的一些杰出人物,大体上是理性的;在马可·奥勒留之后,甚至保守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都是满腹的迷信。除了在伊斯兰教世界,主张理性在11世纪前一直受到了冷落;在那以后,通过经院哲学、文艺复兴以及科学,这些主张日益取得了优势。有一次反应出现于卢梭和威斯莱,但受制于19世纪科学和机器的胜利。在60年代,对理性的信仰达了顶峰:从那之后,它已逐渐减弱,而且现在还在减弱。从希腊文明之初以来,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一直共存在一起,当一方看来很可能完全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总是由于一个反应,导致了它的对立面的一次新的爆发。
现代对理性的反抗,从某一极其重要的角度看,不同于其先行者的大部分反抗。从俄耳浦斯神秘教理派起,以往的目标通常是拯救——一种包含善良和幸福的概念,而且照例以艰难的自我克制的方式来实行。我们时代的反理性主义者,其目标不在于拯救,而在于权力。因而他们发展了一种与基督教和佛教相对立的伦理,而且,由于他们的支配欲,他们必然卷入政治。在作家中间,其家谱是弗希特·卡莱尔、马志尼、尼采——还有诸如特列希克、罗德雅德·吉卜林、豪斯斯·张伯伦。柏格森那样的支持者。作为这一运动的反对派,边沁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可视为一个党派的两翼:两者都是世界主义的,都是民主主义的,都诉诸经济上的自身利益。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于手段,而不在目的,可是在希特勒那里(到目前为止)达到高潮的新运动,在目的方面与两者都不同,甚至和基督教文明的传统也有所差异。
包括几乎所有从反理性主义中产生的法西斯主义者,作为政治家所追求的目的,已由尼采说得得清楚了。在有意识反对基督教及功利主义者中,他拒斥边沁关于幸福和“绝大多数”的学说。“人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人类只不过是实验的材料。”他提出的目的是超乎个人的伟大:“目的就是要达到那种无穷的伟大能量,以此作为未来人的模型,通过训练,并通过几百万粗俗和笨拙之辈的消失,它看到由此产生的不为所动的苦难,如此能量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这一目的的概念本身不能被认作是反理性的,因为目的的各种问题不适于理性辩论的检验。我们可以不喜欢——我本人就是——但我们不能反驳它,就像尼采也无法证明它那样。不过,它同反理性主义有着自然的联系,因为理解性需要公正,而伟人的迷信常以这句话作为其小前提:“我是一位伟大的人物。”
法西斯主义赖以滋长的思想学派的创立者们都有某种共同的特性。他们在意志里寻求好处,而不是在情感或认知中,他们珍视权力甚于幸福;他们宁要权力,不要辩解;宁要战争,不要和平;宁要寡头政治,不要民主主义;宁要宣传鼓动,不要科学的公正无私。他们鼓吹严肃的斯巴达形式,反对基督教的形式;这就是说,他们把严肃精神看作获得奴役他人的手段,而不是作为一种自我修炼,以助于培养美德,以求在另一个世界中获得幸福。后来的人们浸透了流行的达尔文主义,把生存竞争作为高等物种的根源:不过它是人种之间的竞争,而不是像自由竞争的倡导者们所提议的那样,是个人之间的竞争。娱乐和知识被当作目的,在他们看来,都是消极的东西。他们用荣耀代替娱乐,他们所要求的都是正确的,这句自夸的大青就是知识。在费希特、卡莱尔和马克思那里,这些学说还用一件传统道德术语的外衣封裹起来;在尼采身上,它们第一次赤裸裸地、毫无羞耻地露面了。
费希特实际上是发起这个运动的始祖,然而他却没有享有这份应得的荣誉。他开始是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学家的,即使在那时已显示出某种专横、以自我为中心的倾向。他的整个哲学是从这样一个问题发展而来的:“我就是我”,关于这点,他说道:“自我随心所欲,它存在,是由于这个唯一的随心所欲;它是行为的动因和结果,是活跃的也是能动性产生的东西;我存在表示着一种行动。自我存在,因为它随心所欲。’”
根据这一理论,自我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要存在。现在它显示为非自我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我要它存在;但这样产生出来的一个非自我,决不变成对于自我是真正外在的东西,因为自我可以自主地处置它。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费希特说,“宇宙即我”。海涅把康德与罗伯斯庇尔作了比较,说道:“同我们德国人一比,你们法国人还是温驯的。”
确实,费希特随后加以了解释:当他说“我”的时候,他意指“上帝”;但是读者还是对此半信半疑。
耶拿一战,费希特只好逃离柏林,他开始想到,他以前实在过于卖力,把那个非自我放在拿破仑的形象上。1807年他一回来,就发表了他著名的《对德国民族的讲话》,在讲话里,一个完整的民族主义纲领第一次出台了。他首先解释道,德国人优于所有其他的现代人,因为只有他有一种纯粹的语言。(俄国人、土耳其人、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霍屯督人虽有纯粹的语言,但他们在费希特的历史书里却未被提及。)德国语言的纯粹性使得德国人具有深刻性;他得出结论,“具有特性和作为德国人无疑就是一回事。”但如果德国人的性格中还遗留着外来的不良影响,如果德国民族能够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话,那必需有一种新型教育,它将“把德国人形成一个法人团体”。他说的新型教育“必须基本上由此组成,那就是它彻底摧毁自由意志”。他又说,意志“是人的根底。”
除了绝对不可回避的之外,木需要有对外的商业。要有普遍的军事服役;每个人被迫去作战,不是为了物质的福利,不是为了自由,不是为了保护宪法,而是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吞噬一切的爱国主义火焰”的激励下,“它把民族合成一团,生生不息,为此,思想高尚的人愿意奉献自己,而卑微者本来只是为着他人而生存的,也必须效法,牺牲自己。”
这一纲领,把“高尚”者作为人类的目的,把“卑微”者当作无权要求自身利益的人,这是现代对民主主义攻击的本质。基督教教导说,每个人有一个不朽的灵魂,依此看来,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权”只是基督教教义的发展。功利主义,即使它拒绝给个人以绝对的“权利”,却对一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等同视之;这样,它和自然权利的教义一样,也达到了民主主义。但费希特,有点像政治上的加尔文,挑出某些人作为选民,而把所有其他人拒之门外,当作无足轻重之辈。
当然,困难在于去知道谁是选民。在普遍接受费希特学说的世界里,每个人认为他是“高尚”的,他要加入一定的派别,这里的人大致和他接近,看来可以分享他的崇高。这些人也许是他的民族,如同在费希特的事例中;或者是他的阶层,如同一个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员中;或者是他的家属,如同拿破仑的情况。“高尚”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除了在战争中获胜;因此战争是这一信条的必然后果。
卡莱尔的人生观主要是源自费希特,费希特对他的观念构成唯一的最强烈的影响。但是他添加了后来学派的某些有特性的东西:一种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对无产者的关心,其中对工业化和暴发户确实是不喜欢的。卡莱尔手段高超,甚至骗过了恩格斯,在1844年写的论英国工人阶级的书里,恩格斯以溢美之辞提及了他。由此看来,在国家社会主义中由于社会的表象许多人被欺骗,我们就木必诧异了。
事实上,卡莱尔还有他的一些受骗者。他的“英雄崇拜”听起来很高昂;他说,我们不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议会,但需要“英雄国王及一个非英雄的整体世界”。要理解这句话,必须研究一下翻成事实的译文。在《过去和现在》中,卡莱尔把12世纪修道院院长萨姆森作为一个典型;但是不信任那一代著名人物的人,只需读一下《布莱克隆特的约斯林编年史》,就会发现这位修道院院长是一个无法无天的流氓,集专横暴虐的地主和阴谋狡诈的恶棍干一身。卡莱尔的其他英雄们至少同样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克伦威尔在爱尔兰的大屠杀促动他作了这样的评论:“但是在奥利弗(即克伦威尔——译者注)的时代,依我说,‘仍然有对于上帝审判的信仰;在奥利弗的时代,还没有废除死刑’,让雅克①的博爱主义言语,在这个世界上,香水里仍然满是罪恶……只是在晚近衰败的世代中……才能不分好坏,把善与恶合成一种到处管用的独特的糖浆……在我们土地上大有效果。”在他的其他大多数英雄中间,诸如弗雷德里克大帝、法朗西亚博士和爱尔总督,只需指出他们的共性就是嗜血成性这一点就足够了。
那些仍然认为卡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或多或少是自由的人,应该读读他在《过去与现在》中关于民主的篇章。其中大部分是对征服者威廉的颂扬,并带有为他的时代里农奴们所喜悦的农民生活的描写。然后便是对自由的定义:“你可以说,一个人的真正自由,包含他发现或被迫去发现正当的道路,并走下去”。他接着陈述道。民主“意味着发觉任何英雄统治你后的失望,并且甘愿忍受对他们的需要。”文章以雄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