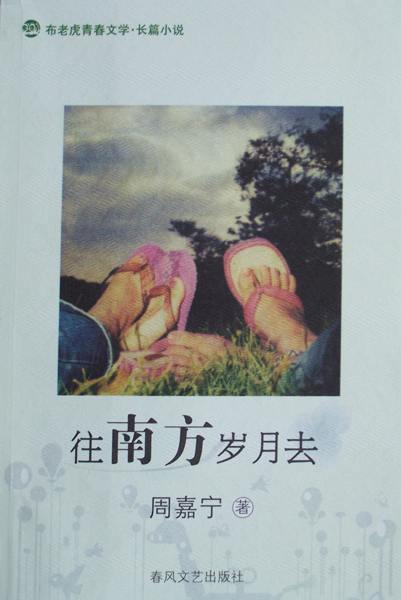走过肮脏岁月-第3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请你们告诫自己的亲友,以后不管在家在外,甚至坐卧行走,一定要擦亮眼睛,永远警醒自己。”
刘春等人好一阵沉默后,各自终于收下了象征弥补苦难的卡片,没有激动,只有哀叹和夺眶而出的屈辱悲泪。
刘春在征求赵悦等人意见后,向莫伟要过打火机。顷刻间,属于令狐春兰与张丽的另两张卡片在刘春姐妹哭泣中,火光里化为灰烬。
莫伟带罪的灵魂被四姐妹的举动撼动着。
“另外,大姐,这两个小纸包是我收藏三姐和幺姐的遗物,请替她们代管。”
刘春打开小纸包,黑绸带和红布包展现在大家眼前。
刘春对莫伟讲起了黑绸带和电子小女表的来历……
原来,令狐春兰在知道孤苦伶仃的婆婆因病去世后,发誓要为其挂孝终身,而电子小女表则是早前张丽男朋友送给张丽的订情物。
四姐妹临走时,刘春应莫伟的要求,以后每半月为不愿抛头露面的莫伟进山送一次生活用品,另转告山下可能出现的非正常情况。
莫伟一一打量着眼前的三间小茅屋——
进门第一间是厨房兼大睡屋。所谓厨房在正进门右边,锈迹斑斑的蛮夯大铁锅依然还安放在土灶上,简易碗柜里一应俱全,除了蟑螂成群便满是污垢,看似脏旧的大木床倒很扎实,床头外侧靠墙角有一只夯实的半人高大木柜,木柜旁有一张小巧四方桌;与外屋一破为二的是另外两间小屋,外间的一角堆放着不少破旧农具与茅草,另及几只鼓胀大麻袋,莫伟打开麻袋一看,原来竟是上好的木炭,另一角排放着养蚕用的一溜木架;通过外间向里走,进门左侧墙角有一架小巧的木床,木床一头有只小木柜,也很结实,小木床对面有一张陈旧而非农家所用的破旧办公桌,两只抽屉及桌柜分别挂着明锁,桌上有面裂痕无数且佈满灰尘的大圆镜。
莫伟好奇地摸了摸锁得很紧的挂锁,但最终还是没动它。
莫伟揭开小木柜,看见里面竟然有叠放得整整齐齐的棉被棉絮,和一对小花枕头、花枕巾、花床单,虽说物件显然都泛着霉味儿,但成色却不太旧。莫伟断定小房主一定是个女性。
莫伟由小木柜联想到外屋的大木柜,他快步来到外间,费了很大劲才掀开了大木盖,果然,只除霉臭夺鼻以外物件俱全。所幸的是小茅屋结构并非外人感觉那样破败,只除不尽灰尘以外,实际一切完好。
莫伟的手伤已经三天了,虽说当时尖刀并不大,但其串掌而过的伤势却也严重,因为从没上过一点儿药,事后他仅用自己的小便冲洗过几次,所以此时整个左手掌早已乌青肿胀,好在并没伤及筋骨,否则眼下根本无法动弹,包扎物是莫伟不忍换下的,刘春的衣料。
铺好床后,莫伟感到一种几个月来少有的疲惫……
仿佛冥冥中,莫伟被一阵轻呼慢唤加摇动弄醒,他睁眼一看,天色早已日上三竿,此刻“兰姐”正伫立在床前。
“兰姐,你……”
“谁是兰姐?你为啥总说‘天晓得 ’的话?”
刘春的快速紧问反倒将原本还未清醒的莫伟问清醒了。
从邪三年多,莫伟从没有真正睡过一个安稳觉,为策划邪恶时的绞尽脑斗,为开发邪恶“奇才”时的冥思苦想,收获邪恶小钱后对大钱的奢盼,有了邪恶大钱后的全身心防范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练就了莫伟“职业”性警觉,此时只因他心态不同了以往,身心松懈已趋于正常,所以漏了嘴。
“大姐,你在说啥?”莫伟边说边下床来。
刘春反倒不吱声了。
刘春开始主动收拾几间小屋的清洁……
经过刘春娴熟有序的忙碌后,小茅屋里更加改变了模样。
莫伟道:“大姐,其实小茅屋很结实,几根基柱摇动时虽然有些吱呀发响,但眼下绝对没问题,四周竹泥巴墙也基本无破损,主要是久没住人的原因,唯一草顶稀疏了些,4020弄些草梱甩上压住就一行,我以前当知青都做过。”
刘春没接话,只是自顾着走进里间,翻弄着那堆茅草并熟练地将它们打成一把把小梱……
刘春在茅草堆中翻出两只矮小竹凳,随后又在草堆中发现一个取暖用的大铁盆……
终于停下忙碌的刘春,走进被莫伟认定是女主人的小房间,娴静地坐在桌前, 面对着破损的镜子,漫不经心地梳理着自己的秀丽黑长发,在莫伟眼里,刘春这一动作酷似王兰。
站在小茅屋外的莫伟,久久凝视着暖阳下远处的山峰,直到刘春“喂喂”地唤了好一阵他才回转身来。
“你的手、不去看看行吗?”
幻觉中,莫伟听见“兰姐”的关切声。
刘春道:“我说你还是去看看吧。”
“对我来说不算啥,反倒可以分散另一种痛。”
“我只给你带了点儿口服药和外用药来,也不知合不合用,你试试。另外,你看看送上来的东西行不行。再有,我们乡街上没有你抽那种烟,我只有合计最好的买了。”
刘春所以要承担起每半月上山一次的任务,其中有三个原因:
其一,担心始终心存仇恨的赵悦;
其二,不放心有意拖拉的刘晓和太胆小的赵冰;
其三,自身心存解谜期盼,又特别是刚才莫伟朦胧中的一声“兰姐”呼叫,令刘春心中涌动着一种似明白非明白,但又总想探个真明白的急切心理。
“谢谢大姐,请你们以后千万别买滋补东西,我不需要,省得放坏也可惜,一般粗茶淡饭加烟,每月一百元足够了。再有,如果下次上来时,请替我买二十本带方格的稿笺纸,我想整理一些文字东西。”
刘春答非所问道:“你见过下雪吗?”
莫伟沉默了会儿道:“我的童年是在北京度过的,天晓得,城市雪景不好看,大地一片死沉,压着厚厚积雪的建筑物像一座座墓碑;大山里不同,奇姿异态,银装素裹,整座大山仿佛是让一袭玉被覆罩着,只是,我现在已无闲雅之心了。”
“为啥?”
莫伟以苦笑作答。
“以前没想注意你说话,也很少听见你说话,想来你文化不低。”
“一九七一年初中毕业,第二年下乡,仅此而已。”
“我渴望读书,直到现在,只要一坐在桌前就禁不住要心驰神往。高中毕业后,因为经济原因我不敢再读书了,好容易说服爸爸妈妈在家务了两年农,随后就外出打工,目的为了多挣点儿钱,把读书希望寄托在比我更想读书的弟弟身上,四妹也挺能读书的,要不是因为她妈妈一直重病,高中毕业她绝不会放弃高考,其他姐妹情况大致差不多,只是……”
“只是现在时间不早了,大姐还是请回了吧。”
收住话头的刘春,看了看时间,站起身来。
“山上特别寒冷,平均气温比山下低五六度,该生火盆时一定要生火盆。”
“谢谢大姐。”
莫伟默默目送着刘春,直到看见刘春走失于眼前才返回小茅屋。
莫伟没用刘春带来的药,只是常常放在面前看着,也不知喃喃地在说些啥,那神情仿佛像面对家人。
从此,住进深山小茅屋的莫伟砸了手表,并着手整理从记事以来的全部人生经历,按照灵魂思路,周而复始地过着自己回归的日子。
不管是莫伟还是刘春姐妹,心中在没有了恐惧之后,日子便觉过得很快。
(29)
转瞬清明又至,莫伟上山已近四个月了。
今天天气格外晴朗,暖阳高照,使人感到舒适与陶然。在以往生活中,莫伟极爱个人清洁卫生,现在只因其惧怕寒冷,又总觉山中多有不便故洗澡少了,但自从暮春时节起,每逢艳阳高照之时,他便要在小茅屋后简陋井台边尽情清洗一番,一则自己舒服,则则避免因肮脏外观使来人心厌。
莫伟数着木杖上的刻痕,他知道,明天又是山下来人的日子。
事实上莫伟早有所觉,在山下的四姐妹中,可能惟有刘春愿上山来,刘春之意并不在送物,而在于心中欲解之谜。但莫伟却在掂量着何时才是最佳揭谜时,此时他一门心思想得最多的便是如何按照自己的心路计划行走。
第二天上午大约九点钟,一夜未睡的莫伟,放下了手中的笔,早早伫立在离小茅屋不远的,一处正对着上山山道的山垭高坡野梨树前,遥望着山下。
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山道上一个极小的身影蜗牛似的慢慢向前蠕动着,时而拐入山道低洼,时而又隐入茂密林中。渐渐的,那蜗动般的人影越来越大,最后,莫伟终于看清来到自己近前的人。
山风吹动着刘春飘逸秀丽的黑亮长发,莫伟眼前幻觉出王兰的身姿……
莫伟接过刘春手里的东西,慢慢跟随其后。
端坐在小竹凳上的刘春,从手中小塑料袋里取出一方洁白小毛巾,幽雅地在自己脸上、脖子上、手背上擦拭着。
莫伟看见刘春手拿小方巾,没有变换过一下坐姿,甚至不顾扑进屋来的山风将其长发吹乱散开,活脱脱一个娴静无语的“兰姐”再现。
“外边坐坐好吗?”刘春说着自顾起身向屋外走去。
莫伟刚一坐定在大石头上,刘春就说话了。
“你未必就不想对我说点儿啥?”
“想,只是不知从何说起。大姐想说点儿啥吗?”
“不想说,但想问,你能回答我的提问吗?”
“是的,天晓得,大姐心中有太多的困惑,远远超过你任何一位姐妹,其实大姐,人心的创伤远胜于你的姐妹,原因是大姐在渴望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万没想到自己收获的却是一份破灭。”
“既然你如此体察人意,想必也绝非突然间所悟,为啥当初要干那些十恶不赦的罪恶呢?说说我三妹和幺妹的详细经过吧,好吗?”
莫伟怀着巨罪心理,将经过全部如实向刘春作了述说。
刘春两眼定定地望着远方,任其无声的悲泪长流着……
忽然,停住抽泣的刘春,再次逼问道:“‘兰姐’是谁?这个新出现的谜团困惑我又近四个月,莫非我真像极你某个深刻的,被你唤做‘兰姐’的女人?又如果说这位‘兰姐’本就是你、不,我曾否认过千万次,以我的亲身感受,凭直觉,在你家庭中绝对没有乱伦行为,但这些显然又都不成立,因为当初你在完全可能的情况下并没伤害我,后来反倒处处保护我,甚至不惜与麻子拼命。这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毕竟使我成为姐妹中唯一一个陷入污垢还能保洁的女人。你能把困惑了我三年多猜不出、悟不透的谜底告诉我吗?‘兰姐’到底是谁?就算我求你,好吗?”
此刻,刘春眼里没有了以前的仇恨,流露出的只一种深深期盼。
刘春一语切中了莫伟心中的最痛,他被刘春的目光逼得受不过了,终于收回旁投的目光,看着现实与不现实中的“兰姐”。
“大姐,就当时而言,我心中对金钱的占有产生着魔般的狂想,一切行为都围绕着金钱,我对金钱感到魔鬼般的渴望,但就当时而言,我对大姐却没有丝毫暴虐心理。你还记得四姐说我是冲大姐来的话吗?”
“莫非不是?你爱我,而且至今仍爱得奇怪的深。”
“我不完全否认你们的话,实际上你们都只说对了一半,我除了自己的妻子以外,还从没跟别的女人有过那怕一次的,本能的肉欲之交。大姐,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从没真正爱过你,但我愿意面对你。天、好啦,从今后,面对大姐我不再说天晓得。”
“好一个‘天晓得’,又好一个‘从没真正爱过却又愿意面对’,你这不是很矛盾吗?!我真听不懂你这些莫伟式语言。说实话,我并不因为假如你‘真正爱过’我感到半点儿高兴,更不因你当初出于某种原因保护我感激你。你以为自己从善了就不被人恨了吗?可能吗?!每当我一想到因为你们的魔鬼行径使我的追求破灭,使我永远失去两位最好的好妹妹时,我就对你有切肤之恨,你懂吗?”
“我懂。所以我更加愿意面对大姐。”
“还有一点,尽管我无时无刻不在痛恨你,但又总盼着能从你嘴里掏出困惑了我三年多的,一个又一个的不解之谜。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自己要永远弃恶从善吗?那你为啥又要如此不善地用困惑来烦恼,和折磨一个跟你没有任何瓜葛的,无辜的大山女人呢?再一次请你告诉我,‘兰姐’到底是你啥人?请你告诉我。”
莫伟收回了投向刘春的目光,垂下头去。
“兰姐全名王兰,是年长我两岁无辜失踪的妻子,我儿子的亲妈。兰姐曾经是一家中医院的药剂师,我们的婚姻是上了书的‘天地缘’,结婚后我一直叫她兰姐。大姐和兰姐的外貌实在太像了。”
刘春似有不信道:“未必真就那么像。”
“是真的,大姐。除了外形酷似之外,甚至举手投足,甚至一颦一笑,甚至轻轻柔柔的说话习惯,甚至一样的秀黑长发,甚至一样的娴静坐姿,甚至一样的善良,等等等等。在我眼中,你们只有三点不同,其一:大姐是左撇手;其二:大姐总是长发披肩,兰姐却是常常挽成发髻;其三:大姐比兰姐略欠丰满,少了女性生育后的成熟美。尽管大姐比兰姐年轻,但是兰姐特别不出老,别看兰姐今年四十六岁,如果用你们现在的照片相对,或许就连大姐自己都分辩不出来。”
莫伟的话犹如“天方夜谭”,六个“甚至”几乎“肯定”了刘春就是王兰。
刘春“噌”地一下站起身来,惊得张大了嘴……
刘春没想到事情竟然是这样,原来长时间在从暗中保护自己的,竟是大恶人的已故爱妻,这不等于是冥冥中有神灵在保佑自己吗?!
刘春仍旧惊立着,两眼傻傻地看着莫伟,微张着嘴却又说不出话来。
“大姐还记得五年前那个令你惊魂失魄的夜晚是啥日子吗?六月四号,那天正好是我三十九岁生日。”
终于缓过气来的刘春,坐下后仍在不时的吞咽着口水,好一会儿才道:“那,你现在还有你妻子的照片吗?”
“我来前祭奠过所有家人之后就烧了,并把灰烬吞进了肚子里。”
刘春惊恐着道:“啊!你咋会、为啥要、你不觉得这样会亵渎……”
“不叫亵渎。我反倒理解为对家人入灵入魂的缅怀,我曾经还吞食过养婆婆养爷爷的骨灰,这,未必大姐能说我是在仇恨他们。芸芸大众中,有时某些人的一些被看做反常的举动,但你却不能用常规思维去理解。人本来就是一种奇怪的思维型动物,世上最难测的就是人心所思,人心最宽阔,人心又最窄小;人心最知足,人心又最贪婪;人心最仁慈,人心又最凶残;人心最高尚,人心又最低贱。常言说得好‘同是一个天盖着,啥子人都有’,人上一百,万花不同。”
低下头去的刘春,内心不能不承认莫伟这番话与自己冥冥中某些观点很暗合,只是她从没想过自己也能像莫伟这样说得出来。眨眼间,昔日魔鬼变成了刘春的心路同伴。
刘春终于忍不住道:“我相信你的话,在大千世界里,相貌相同的人多得数不胜数,正如你说我与‘兰姐’奇妙的合巧一样,但是,我以为在除开奇与巧之外,还有一点你说不通4020。也正是因为这一点,那当时你的非礼企图不就更成立了吗?!这又咋解释?我估计你只破了一半谜给我,还有一半在你心里,对吗?”
“大姐,如果说你还有一点与兰姐不同的话,那就是,兰姐只能悟中悟,大姐却能悟中得,兰姐因美丽善良而高贵,而大姐则因美丽善良而圣洁。”
……
时间在莫伟与刘春的用心交谈中,不知不觉过去了。
刘春坐到了灶塘前,准备生火。
“大姐饿哪?”
“不是都没吃午饭嘛,都晚饭时间了。”
一时间,莫伟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