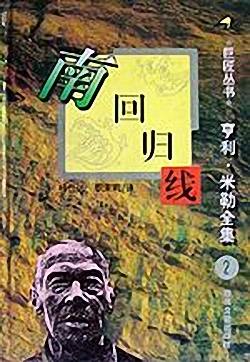北回归线-第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脚。”
关于文明,他说:“文明是毒品、酒精、战争发动机、卖淫、机器以及机器的奴隶、低工资、腐败的食物、低级趣味、监牢、感化院、疯人院、离婚、性变态、野蛮的运动、自杀、杀害婴儿、电影、骗术、煽动、罢工、停产、革命、暴动、殖民化、电椅、断头台、破坏、洪水、饥荒、疾病、土匪、大亨、赛马、时装表演、狮子狗、中国狗、暹罗猫、避孕套、子宫托、花柳病、梅毒、神经失常、神经病,等等等等。”他所罗列的这一大堆风马牛不相及的抽象概念和具体事物均暗示现存人类文明束缚了人(尤其是艺术家)的才能,不符合人性。所以他主张个人应尽力摆脱荒诞的人生之羁绊,避免人性的共性化或异化。因此,他笔下这些毫无信仰的人,丧失希望、爱心甚至“人生”的人,堕落透顶的人,几乎完全失去人的特性的人也都是言之成理的人、自然的人。
批评界对米勒的贬抑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言之成理的批判,也存在很深的误解。最主要的误解源于他对两性关系的随意态度和赤裸裸的、近乎病态的性描写。的确,性这个令人讳莫如深的话题在米勒笔下竟如一股一泻千里的流水,无处不到。书中以米勒本人、范诺登、卡尔及菲尔莫等人为轴心的一切人与事均直接或间接地与性有关。其实,性描写只是手段,米勒并不同于为写性而写性的色情文学作家。他并无意挑逗读者的情欲,这是西方司法部门辨别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淫秽”的标准。60年代末,米勒、D。H。劳伦斯及其他一些作家的著作均依据此原则在美国解禁。
米勒的性描写是为他的人生哲学及政治观点服务的,充分表现出现当代西方人特有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米勒在2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恰好赶上以旅欧美国作家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的步伐。在承继性、教育背景以及审美情趣上,米勒与这些作家并无多少共同之处,但将他们共同怀有的虚无、绝望的情绪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到极致,那就是尽情满足人的动物性需求,在放纵的性交往和通宵达旦的宴饮狂欢中忘却苦涩的人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一代雄心勃勃、抱负远大的青年发觉自己已丧失了人生的目标,在动辄便会降临的死神面前一切努力和拼搏都已变得毫无意义。于是,在荒诞的、由摇篮到坟墓的短暂一生中,人的一切行为都变得合理而又合法,“善”与“恶”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而已沦为人为的空泛概念了。海明威的亨利(《永别了,武器》)在女友因难产死后冒着雨沿街踽踽独行,永远告别了残酷的战争和美妙的爱情。试问这一代青年“君欲何往”?我们会很自然地、符合逻辑地想到,战后心灰意冷、厕身于布满残垣断壁的瓦砾中的亨利之流很可能也会加入米勒们的行列,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消磨这被辜负的青春。那不正是他们的必然归宿吗?尽管多数人对于一件令人开心的事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个别人却有可能以截然相反的方式来表达类似的情感,如号啕大哭。米勒正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极端方式来表达与“迷惘的一代”类似的茫然、失望的感受。
巴黎,这个以“现代巴比伦”著称的西方文化之都是近现代史上无数青年艺术家、文学家向往的圣地,朝拜缪斯的神殿。对于亨利·米勒是如此,对于斯泰因、海明威、菲茨杰拉德、阿那依斯·宁等人亦是如此。这个崇尚浮华的城市既为美国作家们带来创作灵感,也增强了包括性能力在内的体验生活的能力。美国作家观赏异国风光、畅饮美酒、从事性冒险,这些经历无一不成为他们创作生涯的一部分,而绝不是米勒独有的。海明威在50年代写就的《漂移的盛宴》中表达了对于最终把自己造就为名作家的巴黎的终生眷恋之情。在第一章中,他叙述了自己在一家咖啡馆里写作的情形,承认自己的创作灵感源于性憧憬。由于身边有一位迷人的姑娘,“故事自己跃然纸上,我只是很艰难地竭力跟上它……每写完一个故事我总感到空虚,既悲哀又快活,仿佛刚刚做过爱……”菲茨杰拉德在《夜色温柔》中写了一位迪克,他刚刚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便同年轻漂亮的电影明星接吻。后来这位登徒子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变得柔弱无能,先后被情人和妻子抛弃。他的性无能最终导致其事业上穷途潦倒、一事无成。在米勒的挚友兼情人、为《北回归线》作序的女作家阿那依斯·宁的日记(The Diary of Anais Nin;1931—1934)中,作为一种原始生命力的性能力多次与作家、艺术家的创造力相提并论。她在日记中记述,曾在1932年3月应米勒的建议一同去巴黎一家妓院看女同性恋者表演性技巧之事(近年来上演的传记片《情迷六月花》[Henry and June]亦再现了这一场面)。宁与男人和女人之间纷乱的性纠葛及她试图写一部研究D。H。劳伦斯的专著的计划使她觉得重新发现了自我,变得更加才思敏捷。在日记另一处,她写到同米勒做爱:“对于我,在米勒的旅馆房间里度过的最后那天下午像一只炽热的熔炉。在此之前我仅具有白热化的头脑和想像力,现在获得的却是炽热的血、神圣的完美。”Anais Nin:The Diary of Anais Nin; ed。 by Gunther Stuhlmann; Swallow Press; 1977。
第一部分痴人说梦(代译序)(4)
《北回归线》中的米勒们同海明威及其笔下的众多人物、菲茨杰拉德及其迪克以及宁本人一样体验到这“神圣的完美”即是创造力与性爱的相互认同:性能力是艺术创造力的表现形式,艺术创造力因性能力而被释放。倘若在性观念上米勒同别人有所不同,那只是他更直率、更坦诚。抛开一切伪装,在烟花巷中、酒吧间里寻找慰藉的米勒、范诺登、卡尔们比同时代人看得更“穿”。“哀莫大于心死”,米勒等的悲哀早已超越“迷惘”的程度,他们的心灵早已麻木、绝望。在《北回归线》中米勒写道:“就在此刻,就在新的一天到来的这宁静黎明之际,这个世界不是充满着罪恶和悲伤吗?可曾有哪一人类天性中的成分被历史无休止的进程所改变,根本地、重大地改变?”“我找到了上帝,但上帝也无济于事。我只是在精神上死了,肉体上仍活着,而在道德上我又是自由的……如果我是一条狗,我准是一条瘦弱、饥饿的狗……”作为客体的上帝仍活着,但已成为摆设;作为主体的“我”却已死去,成为一具行尸走肉,一条四处觅食的“狗”。
人的天性是自觉和自由,既然子虚乌有的上帝只是作为人的天敌的一整套社会价值观与道德取向而存在的,与之相对立的人的精神幻灭使其存在变得毫无意义。可见米勒这番话也就是尼采的“上帝死了”这一断言的翻版——在尼采那里是“上帝”死,在米勒这里则是自我之死,它也使我们看出笼罩在米勒身上的源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阴影。克尔恺郭尔说“生活是一个黑暗的格言”、奥托·兰克说“出生也即被逐出伊甸园”、萨特说“人是生来自由的”,这些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大师们的论断均可在米勒那儿找到注脚。性、食物、酒精及写作给米勒们带来暂时的欢悦感及幸福感,是麻痹其过于敏感的心灵使其逃避忧患的自我的麻醉剂。加缪“二律背反”式的命题认为西绪福斯的悲剧在于他知晓自己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人们必须假定西绪福斯是快乐的”Albert Camus:The Myth of Sisyphus;trans。by Justin O'Brien;New York;1955;P。91;P。30。,因为正是他的知晓使造成痛苦的境遇消失。“他的命运属于自己,他的巨石是他的财富。”同上。同理,以流浪汉兼恶棍面目出现的米勒这个现代西绪福斯也是“快乐的”(他在书中自称是“活着的最最快活的人”),因为他也有自己的“财富”,可以依赖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生活方式。
米勒对人类性行为的渲染当然是消极的,但他的本意是要抨击虚伪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撕去它罩在文明社会中人类性关系上的伪装,要通过性经历将自己造就为才华横溢的艺术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坛上的许多思潮和流派中均有米勒的影子——“垮掉的一代”、荒诞派戏剧、非虚构小说、黑色幽默、个性化诗歌……米勒的创作观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美国作家和诗人。围绕私人琐事的超现实主义新闻体的“自动写作”、“自白”与“剖析”相结合的写作技法、人生若梦的虚无主义思想倾向及肆无忌惮地发泄颓丧情绪的自我表现使不少美国作家为之心醉。他算不上主流作家,他的激进观点也并不新颖,但他的独特文体风格却在杰克·凯鲁亚克、约瑟夫·海勒、诺曼·梅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巴思等当代先锋作家的代表作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小说会逐渐让位于更感人的书,如日记和自传”(爱默生语),众多的《北回归线》式小说的问世使我们不得不赞同爱默生的预言。米勒曾称自己为“文化暴徒”,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痴人、怪人、狂人米勒及其作品的意义主要体现在社会和文化领域,其文学价值当然也有独到之处。
1991年是米勒诞生一百周年的“整日子”,为此美国出版了记述他的生平的两本传记,此举再次在美国文坛上掀起了一些不大不小的波澜。冯亦代:《两本亨利·米勒的传记》,载《读书》,1991(11),139页。昔日桑田今为水。抑或米勒终究有一天也会像爱伦·坡一样,成为超越其社会学意义的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才?
译者孤陋寡闻,学识浅薄,错讹之处在所难免,对原作风格的把握更不可企及,诚恳希望读者诸君不吝赐教。是为序。
袁洪庚
1993年2月28日于兰州大学
2003年10月26日修订
第一部分《北回归线》序
假如真有可能,眼前这本书或许可以叫我们恢复对一些基本事实的胃口。书的主旨似乎是要流露某种激愤悲苦的情绪,而且这种激愤悲苦情绪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的,然而书中还表现出狂妄的放纵和疯子似的欢欣,充满活力,趣味横生,有时则几乎沦为狂言呓语。它在极左和极右之间不断地来回摆动,留下味同嚼蜡、空洞无物的一段段空白。它已超越乐观或悲观的范畴。作者叫我们最终战栗不已。痛苦已不再有隐秘的藏匿之处。
在这个因内省而濒于瘫痪、因享用精美的思想之盛宴而便秘的世界上,这一番对客观实在的野蛮暴露像一股赋予人勃勃生机的热血汹涌而来。暴力和淫秽的东西完全保留下来,体现出伴随着创造性行为而来的神秘与痛苦。
本书再度申明作为智慧和创造力主要源泉的经验的补偿价值,然而书中仍有未成熟的思想和未完成的行动,像一捆破布乱麻,过于挑剔的人会用它们勒死自己的。谈到他的作品《威廉·麦斯特》长篇小说,分为两部:《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威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译者时,歌德曾说:“人们寻找中心,这不容易,并且也不对头。我认为展现在我们眼前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便足矣,不必非表明一定的倾向不可,因为那毕竟只是为知识阶级而做的。”
本书由它自己的线索连接起来,单凭种种事件的发展和演变构成。书中没有中心,因而也不存在英雄气概或自我奋斗的问题。因为不存在意志问题,它只是随波逐流而已。
粗俗的漫画式描写也许更富有生命力,比传统小说的全面刻画“更忠实于生活”,因为如今的人没有中心感,也不会产生一丁点儿有整体感的幻觉。书中人物与我们在其中濒临溺死的虚伪文化的空虚是不可分的,于是混乱的幻觉产生了,而面对它则需要最无畏的勇气。
作者以淳朴的诚实娓娓道来,他所遭受的种种耻辱和失败并不是以失落感、沮丧或万念俱灰的情绪而告终的,而是以渴望——对一种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如醉如痴的、贪婪的渴望而宣告结束的。其中的诗意非要剥去艺术的外衣方可发现,非得屈尊降低到所谓“前艺术水准”时方可发现。藏在分崩离析现象中永恒不变的形式之框架再度显现,以便以另一种形式在情欲的不断变化中出现。文化的助产士们留下的伤痕被烧去,于是我们这位艺术家瞠目结舌地望着撕裂的伤口,从中探寻人类希冀借助艺术曲折隐晦的象征手法逃避的严酷心理现实,以重新确立幻觉的潜在力量。在本书中,所有的象征都被剥去了伪装,被这位过于开化的文明人天真无邪地、厚颜无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似乎他只是一个颇有来历的野蛮人。
并非虚伪的原始主义引发了这一番野蛮人的抒情,它并不表明某种退化倾向,倒是向未曾企及的领域的冲击。即使以审视劳伦斯、勃勒东、乔伊斯和塞利纳大卫·赫伯特·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安德列·勃勒东(1896—1966):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爱尔兰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法国作家。这类与众不同的作家的评判眼光来看待这样一本赤裸裸的书也是错误的。让我们试着以一个巴塔哥尼亚人南美洲印第安人之一支,是世界上最高的人,此处意即“巨人”。——译者的眼光看它吧。在这些人眼里,我们的世界上一切神圣的、应对其有所顾忌的事物都毫无意义。由于将作者带入人类精神世界终极的历险也就是每一位艺术家的历史,为了表明自己的思想,他必须穿越自己幻想世界中的无形铁网。陷阱、无机盐废料、碎裂的纪念碑、腐烂的尸体、疯狂的吉格舞和乡村舞——所有的这一切构成一幅我们时代的宏伟壁画,一幅用支离破碎的话语和喧闹、刺耳的锤子敲击声构成的壁画。
如果本书中能诱发出一种能量,能令那些死气沉沉的人大惊失色,从沉睡中猛醒,那就让我们额手称庆吧,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剧恰恰就在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使它从昏睡中醒来。人们不再做噩梦,不再心情振奋,不再觉醒。在自我了解所产生的麻醉状态中,生命在流逝,艺术在流逝,它们就从我们身边溜过。我们同时光一道逝去,我们在同影子搏斗,我们需要输血。
本书予以我们的正是血和肉。书中只有酒、食物、笑、欲望、激情、好奇心——一些滋养我们最崇高、最虚无缥缈的创作之根基的简单事实,上层结构则被砍去。该书送来的一股清风,吹倒了枯朽的树木,它们的根部业已枯萎并且在我们时代的不毛之地中消失。该书触到了这些树根,以后继续向下挖,去发掘地底下的道道清泉。
阿那依斯·宁阿那依斯·宁(1903—1977):美国作家、精神分析学家。她生于法国巴黎,后入美国籍,1930—1940年居留巴黎期间同亨利·米勒过从甚密。
1934年
第一部分《北回归线》第一章(1)
现在我住在波勒兹别墅,这里找不到一点儿灰尘,也没有一件东西摆得不是地方。除了我们,这里再没有别人。我们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他身上生了虱子,于是我只好剃光他的腋毛,可是他还是浑身发痒。住在这么漂亮的地方居然还会生虱子?不过没关系。我俩,我和鲍里斯也许永远不会彼此这样了解,若不是靠那些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