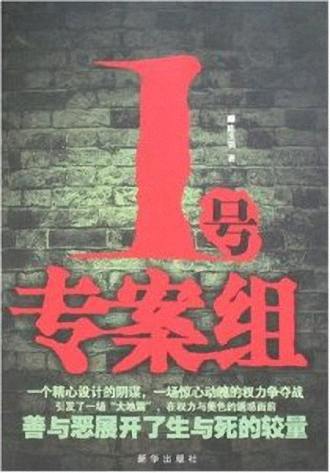专案组长-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林为驹慢慢走进烈士陵园里,他又想起四十年前的那个小姑娘,那个会写一手漂亮毛笔字的小姑娘,他每天都站在她的身后看她,越看越想看,越想看就越想抱她,拥有她。但后来一切都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她把自己投向了那个大她二十多岁的男人,而且不顾一切地奔向那个男人。他曾经告诫过她,威胁过她,她根本听不进去。
林为驹感到身上有些燥热,就解开了领口。他见方茹晰正伏在那块待刻的石碑上描字,其实那字写得已经很漂亮了,他知道,“西方市第一任书记黎明同志之墓”这几个字只能方茹晰写,才能写出这种水平。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书者的法理不在于形而在于情。
“你的毛笔字,四十年前写得就很漂亮!现在依然那么娟秀!”
方茹晰仍然伏着身描她的字,仍然在揣摩那字里的法理。
“不行喽,都快五十年了,真的是老了,手拿毛笔有点抖。这几个字我在心中已经练了四十几年,可是,一拿起毛笔还是不行。这块墓碑的字我一直想,应该是由他的后任来写的,你的字其实比我写得好。可惜,要你题写的东西太多啦,哪还有时间顾及到这些死人呢?不过,我想你不写也好,因为你一直不具备资格,真要写了,不仅黎明感到不舒服,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也会觉得不舒服的,你说呢?”
方茹晰慢慢收起了毛笔。
“是啊,快半个世纪了,眨眼过来了。没想到你生活得这么艰辛。”
方茹晰抬起目光,恬淡地冲林为驹笑了:“是吗?我倒觉得我生活得比你充实,也比你轻松些。”
林为驹立刻明白了方茹晰话中的含意,点点头予以认可:“其实,是你改变了我的生活。”
方茹晰不赞成地掠了眼林为驹:“我一直在想,是你误会了历史,还是历史误会了你?当年西方市并没有选择你,就像五十年前的人民不愿意选择国民党一样。你和黎明,你们无法相比。他的胸怀像他的名字一样灿烂,他单纯得像个婴儿,而你的心里却充满了阴暗。广袤的天空和阴暗的角落是无法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
林为驹沉重地低下了头:“这四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的微笑,我一直在寻找你。”林为驹轻轻叹了口气,“俄国一个作家说过:男人和女人不应该仇视,他们更多的是相爱。”
“那是因为这个作家还没有经历过什么叫恨。一个人当她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都献给一种崇高或者神圣的东西时,这种爱被魔鬼血淋淋的屠刀斩断了,她还会有爱吗?不瞒你说,黎明走了后,我再没有笑过。今天我也许会冲你笑,这种含义会是一样的吗?”
林为驹不敢再看方茹晰那平和而宽容的目光:“看来,你是不愿意原谅我了。”
“我想这不是你我之间的恩怨。黎明那一代人用鲜血换来的共和国,和雪山他们这一代人用生命捍卫的每一寸共和国的土地,是决不会让你们这种人下蛋生崽的!”
林为驹长长地叹口气,蹲在了那块躺着的石碑前,他想伸手把它立起来,但终于没有弄动那块石碑。
雪山打电话找了所有林为驹能去的地方,都说没有见到。雪山只得抱着林文姝的骨灰盒走出了家门。
“爸爸您去哪?”雪可见雪山又抱着妈妈的骨灰盒走了,不自觉地问了句。
“我和你妈出去散散步,你一个人先睡吧。如果想去奶奶家睡也可以的。”
“爸,让我陪陪您吧?妈……”雪可目光哀哀地投在林文姝的骨灰盒上。
雪山苦涩地一笑:“睡吧,还是让你妈陪我,我有很多话要跟你妈说,有很多事要跟你妈商量。”
雪山走了,雪可心里酸酸的。
雪山前一天已经同林为驹约好,他们要在英雄峰上谈谈。至于谈什么雪山没有说,对方也没有问。但他一整天都没有找到林为驹,他不知道这个昔日的岳丈大人能不能如约去赴英雄峰的聚会。
黎明墓前那块崭新的墓碑不知什么时候被什么人立了起来,墓碑高高地屹立在无名冢前,“西方市第一任市委书记黎明同志之墓”几个大字闪亮地写在高高的墓碑上。那字迹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墓碑没有刻字怎么就立起来了呢?
雪山默默地看着墓碑,双手将林文姝的骨灰盒安放在了墓碑旁:“爸,我和文姝看您来了。”
雪山将一束鲜花放在林文姝的骨灰盒上,默默地垂下了头。他在等那个人,他不知道那个人能不能来。
无名冢后低低的哽咽声渐渐大起来,随着那渐渐明晰的抽泣声,雪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那身影扑向了林文姝的骨灰盒:“我的文姝!我的文姝!你是爸爸最好的女儿,爸爸对不起你啊!”林为驹匍匐于地,双手紧紧抱住了林文姝的骨灰盒。
雪山一把从林为驹怀中抢过骨灰盒:“你……不要碰她!”
“她是我的女儿!我的女儿!”林为驹还在争夺雪山怀中的骨灰盒。
“你有资格做她的父亲吗?你配有这样的女儿吗?”雪山站起了身,“你不配的!”
“雪山……”
“我请你离开这里,你不要玷污了这块神圣的地方!”
雪山没有再看林为驹,而是一个人默默地走了,抱着他心爱的骨灰盒走了。
林为驹没有去追,也没有再哭泣,只是默默地看着雪山慢慢走下山去。
第七节人生自古谁无死
西方市又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人们发现西方市第一任市委书记黎明同志之墓的墓碑前躺着一个人,这个人已经死亡。
经法医鉴定,死者系碰碑自杀而死,现年六十岁,姓林,名为驹。
红军山(代后记)
《专案组长》敲上最后一个句号时,我有幸去了趟遵义。
遵义在中国现代史上的显赫地位,全在于1935年的那次会议。那是中国红色革命走进井冈山又走出井冈山后一次非常理性的会议。会议的沉重气氛从当时那个小小的会议室里就可以感觉出来。红军的30万人因指挥错误损失了27万,剩下的3万人还能不能走出云贵高原的那些高山大川,这可能是摆在当时每一个与会者面前最现实的问题。理性与冷静是狂热的天敌,困境中才能真正理解机会需要创造,机会失去不会再来。3万人四渡赤水,南下贵阳,硬是把中国革命拖出了死亡地带。但损失也是十分惨重的,看着当年那些志士们破衣烂衫的照片,让人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遵义城的后面有座红军山,红军山上有个红军集体墓冢。那墓冢里埋的是在遵义之战牺牲的七十余位烈士的遗骨。据说这还是全国解放后慢慢收集起来的零散在各处的骨骸。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梦回?站在红军山上,我当时无法说清楚自己的感受。《专案组长》的引子是三年前写就的,源于我在西部生活时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1995年我去敦煌的故阳关寻故,陪同的同志说起西路红军的事,情绪非常低沉,他说当时进入河西走廊的男红军们,全部被赶到了这些无遮无拦的戈壁滩上,被马步芳的骑兵挥舞着马刀砍草人似的削了脑壳。女红军被分配给了那些师团长们做姨太太。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后来陆续看到宁夏和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的几本写西路红军的党史资料,证实了那个陪同同志的话,心里就更感到沉重。
三次去云南,甚至两次深入到滇西北的小凉山深处,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云南的保山和老山看看,其实这是我去云南最想去的地方,据说那里的墓碑依山势而建,排列得很壮观,很雄伟,在那里你会对生命的意义有更深一层的认知。
红军山上有个红军坟,红军坟没有和那七十余名红军的遗骸埋在一起的原因,是因为它本来就在城南,是红军二进遵义时一名掉队的红军遗骨。据说这名战士掉队的原因,是出诊去为当地的百姓看病。1935年的遵义,百姓生活很苦,瘟疫横行。这名战士用当地的草药只顾为百姓治病,没想到大部队因战事紧急悄悄撤离了,因此她也就惨死在敌人手里。当地百姓念她平时治病的好处,就偷偷地把小红军埋了。不久,小红军的坟上长出了无数不知名的野草野花,曾经被小红军治疗过的百姓就说那些野草和野花他们见过,就是治好他们病的草药。有病的百姓就大着胆子去吃那些草药,奇怪的是大凡吃了草药的人百病消除。这件事不胫而走,越传越神,小红军坟被视为了救生救死的菩萨。敌人哪能让这种坟墓存在呢?几次挖掘破坏,但小红军的遗骨还是被当地的百姓保护了下来,并且坟上的草药也越长越旺,治愈的病人也越来越多(解说员说是有病者的心理作用,我不这样认为)。遵义的百姓并不知道小红军姓什么叫什么,甚至连小红军是男是女也搞不清楚,但他们只知道她是红军。解放后,随着红军山的命名和建立,小红军的坟墓被移到了山上。到八十年代初期,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经过千辛万苦才搞清楚小红军的真实姓名和性别。其实她是个男儿身。为了表彰他对人类生命的关爱,川大美术系的教授们仍把他的塑像刻画成了女性。
千年风云,几册薄卷,历史的灵动有时就在偶然间的冥冥感觉中。我喜欢这些故事和故事里的人物,写人世沧桑,书善良人性,歌正气男儿,为百姓立言,是我常反观自己灵魂的一个方法,也是我业余生活的终极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