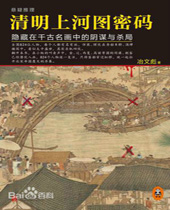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个少妇已拿了把小小的匕首出来:“这个成不成?”
墨儿接过来一看,刀刃很薄,便点了点头,随即将刀刃挤进门缝,慢慢拨动门闩,正拨着,听见右边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这是怎么了?”那声音尖亮,很耳熟,墨儿忍不住回头一看,二十来岁,瘦瘦尖尖一个人,是彭嘴儿的弟弟,街市上行走卖药的彭针儿。
墨儿没有作声,回头继续慌慌拨门,朱氏在身后给彭针儿解释缘由,彭针儿听了,用那尖亮的嗓子连声叫着:“这几天满京城都不安宁,怎么连咱们这里都出事了?康家嫂子去哪里了?怎么连着几天都没见着人影儿了?”
一会儿,门闩拨开了。朱氏和彭针儿就要推门进去,墨儿忙伸手拦住:“慢些!现在情势不明,不能贸然进去。”
止住两人后,他才小心推开了门,屋里一阵酒气扑来,康潜躺在厨房中间,一动不动,身边倒着一个瓷酒瓶子,瓶口处的地上,有一小片潮湿印迹。除此而外,看不到其他什么。墨儿小心走过去,见康潜微张着嘴,脸色枯憔青灰,面目已经僵住。他弯下身,伸手去探康潜脖颈的脉搏,皮肤冰凉,脉息全无,已经死了。
他心里一阵悲疚,慢慢站起身,若不是外面三人都睁大眼睛望着他,他几乎要哭出来。彭针儿尖声问道:“死了?”墨儿黯然点点头,朱氏悲嚷起来:“爷喽!这是咋了!”
墨儿朝里屋望了望,心想得去查看一下,便尽力压住心中内疚悲闷,小心走进中间小过厅,桌上一副碗筷,一个碟子里盛着些酱瓜,旁边两个酒瓶。四根条凳面上都薄薄蒙了层灰,只有碗筷这边的条凳上有人坐过的印迹,看来仍是康潜一人独自吃饭。左右两间卧房门都开着,他轻步进去都查了一圈,又到前面店里查看,都没有躲着人,前门也闩死的。他这才回到厨房,朱氏三人都在后门外张望,墨儿顾不得他们诧异,见右边那间小卧房门关着,又走过去,伸手轻轻推门,门没有闩,随手而开,他探身进去,和那天一样,里面空着,窗户也完好。
全部查完后,他才轻步走了出去,对彭针儿道:“彭三哥,这里我不熟,能否劳烦你去请这里的坊长和保正来?让他们赶紧找人去官府报案。”
彭针儿一脸不情愿,但若真是命案,邻里都要牵涉进来,他自然明白这一点,因此稍踌躇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一声,转身去了。
墨儿又对两个妇人道:“请两位大嫂不要离开,好做个见证。这位是武家二嫂吗?”
少妇点了点头,她就是康潜所说的柳氏,康潜妻子失踪那天,就是和她约好去庙里烧香。墨儿打量了两眼,见柳氏中等身材,容貌虽然一般,但神色沉静,看到康潜死,虽然也脸带悲怜,却不像身边的大嫂朱氏又悲又叹,始终能够自持。
墨儿打量她,她也打量着墨儿,随后轻声问道:“敢问这位公子是……”
墨儿这才想起来这里的缘由,正要从她们口中探问些讯息,忙答道:“在下是康大哥的朋友,康大哥前几天找我来帮他查找他妻儿的下落。”
墨儿盯着妯娌两个,朱氏本来望着房内康潜的尸首,正在悲念,听他们说话,才停住嘴转头来听,听到墨儿这句,她愣在那里,似乎没听明白。柳氏眉头一颤,露出些诧异:“哦?春惜姐姐和栋儿?他们娘俩不是回娘家去了吗?”
朱氏也才回过神,大声道:“是喽,她娘俩回娘家了呀,查什么下落?”
墨儿摇了摇头,继续盯着她们:“不是,他们母子被人绑架了。”
“绑架?!”朱氏嘴张得更大,“爷喽!这是闹的哪一出哦?”
柳氏也一惊,望着墨儿,并没有说话,等着继续听。
墨儿便继续道:“绑匪要挟康大哥不许说出去,他才谎称妻儿回了娘家。这件事关系到两条性命,两位大嫂一定要保密,万万不要告诉任何人,包括你们的丈夫。”
朱氏忙道:“好!好!好!”
柳氏则望着屋内康潜的尸首,喃喃道:“难怪那天康大哥神色不对。我本来已经和春惜姐姐约好去烧香,早上去叫时,康大哥到后面转了几圈,出来却说她回娘家去了,他当时面色极差,言语也不清不楚,我还想着他们夫妻又斗气了,没敢多问……”
“哦?他们夫妻经常斗气?”
“起先还好,两人和和气气,相敬如宾,可是这一向,不知怎的,开始斗起气来。”
“他们争吵吗?”
“这倒没有,两个人都是闷性子,最多争一两句,便不作声,各自生闷气。”
“是喽,有两回,我看着他们夫妻神色不对,还替他们说合了呢。几天前,为孩子打碎了一只茶盏,两人又还争吵过,孩子又在哭。那回争得声音有些大。”朱氏附和道。
康潜未曾讲过这些,墨儿听了,都记在心里。
柳氏忽然问道:“康大哥为什么不去报官府,反倒要找你?公子难道有什么来历?”
“我姓赵,没有什么来历,只是跟我哥哥开了家书铺,替人写讼状,查案子。”
“公子的哥哥难道是那个赵将军?”
墨儿点了点头,柳氏又要问,刚开口,就见彭针儿引着一个胖胖的盛年男子急急赶了过来:“坊长来了!”
第八章醉死
蹇便是处蹇之道,困便是处困之道,道无时不可行。——《二程遗书》那坊主遇事老练,在门外见到康潜的尸首,没有进去,守在门边,让墨儿他们退后一些,但都不许离开,挨个盘问前后情形。
墨儿回答过后,心里一直在寻思,是谁杀了康潜?为何要杀康潜?难道是为了催逼他交出香袋里的东西?但康潜身上看不出伤口,房内也没有扭打争执的迹象。何况康潜一死,就算他弟弟康游能找回香袋里的东西,恐怕也不会交出来了。杀死康潜对于绑匪来说,不但无益,反倒有害,更会暴露自己。难道绑匪和杀人凶手是两个人?彼此不相干?
劫走康潜妻儿的人可能是左右邻舍,刚才探问武家妯娌,她们似乎并没有嫌疑,大嫂朱氏一直在悲叹,她和康潜比邻多年,那种伤怜应该不是装出来的。二嫂柳氏虽不像朱氏那么伤悲,但三月初八春惜母子失踪那个早上,柳氏还在前门唤春惜去烧香,更没有嫌疑。至于武家三兄弟,二弟阵亡,老大武翔那天见过,一个极和善的人,老三武翘还是太学生,他们应该很难瞒住朱氏和柳氏去做绑匪。
比较看来,左边彭家嫌疑更大。不过墨儿记得,寒食前后那几天,彭家老二彭嘴儿一直在香染街口说书,每天都能见到,应该没有嫌疑。
墨儿向彭针儿望去,坊长正在问彭针儿发现尸首的经过,彭针儿连声说“我并不知道,听到他们嚷才出来看到。”他常日在街头到处游走卖药看病,行踪不定,不过看他的神情,对康潜的死似乎也很意外,若他是绑匪凶手,刚才请他去找坊长时,为了伪装,便不会有推拒之意。
目前只有老大彭影儿不曾见过,彭影儿在京城勾栏瓦舍里演影戏,难道绑匪和凶手是他?
他正在沉想,却见顾震带着万福和一个年轻男子骑马赶了过来。
顾震一眼看到墨儿,十分纳闷:“墨儿?你怎么会在这里?”
墨儿见旁边有人,便略过绑架一事,将前后情形简要说了一遍。顾震听了,转身吩咐那个年轻男子:“姚禾,进去查一查。”
墨儿才知道那年轻男子姚禾是仵作,他和众人一起站在后门外,看着姚禾检查康潜尸首,万福也进去帮忙填写验状。
姚禾查验完尸首,又进到屋子里看了一圈,出来向顾震禀告道:“顾大人,并非凶杀,事主是醉死的。”
墨儿和其他人听了,全都大为诧异,朱氏更是大声叫道:“哦喽!爷啊!”
姚禾继续禀告:“事主身上没有任何伤口、伤痕,也没有扭打迹象,屋内桌上两瓶酒都已喝光,尸首身旁酒瓶里还有些残酒,卑职尝了尝,酒性极烈。看事主面色、眼白都泛青黄,是肝病之兆。头发燥枯,皮肤干薄,嘴唇发青,应是连日缺少饮食,空腹喝猛酒,又倒在地上,受了一夜寒气,肝脏衰竭而死。”
墨儿听了,浑身一阵发冷,心里顿时又涌起悲疚。越拘谨的人,心事便越重。康潜性格极拘谨,妻儿在他心中所占分量,恐怕远过于他人。我答应他,会找回他妻儿,可直到现在仍无头绪。康潜愁闷难消,只有借酒抒怀,他之死,有我之责……他正在沮丧自责,身后忽然传来一阵粗粝的悲声:“哥哥!哥哥!”
一个衣衫破烂、满身污垢的年轻汉子,一把推开门前围着的人,几步奔进门里,扑到康潜尸身上哭起来——墨儿忙问身边的朱氏,朱氏抹着泪道:“这是康家二郎。”
康潜、康游两兄弟五官虽然相似,但康游生得十分壮实,一看便是个武人出身。他是开封县尉,不知为何这样衣衫脏破、满脸泥垢。看着康游这样一个粗猛汉子哭得如此伤恸,墨儿心中越发愧疚难当,呆立在一边,不知该如何是好。
墨儿走到顾震身旁,放低声音道:“顾大哥,请到一边说话。”
两人走到五丈河边,墨儿才低声把事情的详细经过讲了一遍,顾震听了之后,皱了皱眉:“我还道这个康潜既然是自己醉死,这里也就没事了,谁承想里面还有这么多原委,你既然已经查到这个地步,就拜托你继续查下去,若有需要哥哥处,尽管说!”
墨儿却已毫无信心,沮丧道:“我已经害死了康潜先生,再不能查了。”
顾震忙劝道:“莫乱说,是他自家心气窄,想不开,与你何干?眼下这桩案子,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只有你最熟悉,何况你跟着你哥哥查办过许多疑案,另找一个人来查探,又得从头摸索,而且也未必及得上你。你莫胡思乱想,更不要怪罪自己。若你真的不成,我也不会把这事托付给你。”
墨儿虽然沮丧,但心底里其实始终难弃,听顾震这么讲,便点了点头。
顾震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这么才对嘛。这案子眼下你怎么看?”
墨儿略想了想,才慢慢道:“康潜妻儿仍在绑匪手里,安危难料,这背后藏了些什么,还不知道。我和哥哥商讨过,绑匪应该就是康潜的左邻右舍。事情到这个地步,恐怕再不能暗查了。得请顾大哥给他们明示一下,我才好名正言顺地去查。”
“这个好办,我们这就去说明——”
墨儿随着顾震回到康潜家后门边,顾震对门外诸人大声道:“康潜之死还有一些缘故未明,我已委托这位赵公子继续查证,你们不得推诿避逃!”
诸人都望向墨儿,这时康游已停止哭声,也转过身睁着哭红的眼望过来。
墨儿之前只是受尹氏私托查这案子,这时当着众人被正式授权,才真正感到责任在身,不容他再犹豫推脱。
于是他鼓起勇气,叉手正声道:“还望各位能多多关照,赵墨儿先行谢过。”
顾震又诫斥了众人几句,这才带着万福和姚禾先走了。
墨儿回身先望向彭针儿:“彭三哥,能否问你一些事情?”
“我?”彭针儿尖瘦的脸上露出诧异,一双细眼游闪不停,“有什么事赵公子就问吧。”
“这里不太方便,能否去你家里?”
“家里?”彭针儿目光忽地一霎,不过随即笑起来,“好啊,请随我来。”
彭针儿还未走到自家后门,就朝里喊道:“嫂嫂,家里来客了!”
墨儿微有些诧异,觉得彭针儿像是在特地报信一样,不过他装作不知,跟着彭针儿走了过去。
彭针儿走到门边,却没有进去,俯下身摸着门板自言自语道:“这门板裂口已经这么大了,门轴也快朽了,得换了。”说了一阵才直起身推开了门,墨儿越发觉得彭针儿是在有意拖延什么,彭针儿却露出在街头哄人买药的笑容,“赵公子请进——”
彭家屋里格局和康潜家一样,后边是厨房,也套了间小卧房,应该是彭针儿在住;中间一个小过厅,左右各一间卧房;前面却没有开店面,是间前堂。屋里只有些粗笨家什,东西胡乱堆放着。
彭针儿引着墨儿到了前堂,请墨儿在中间方桌旁坐下后,又朝里面喊道:“嫂嫂,来客人了!”
后边卧房的门开了,随后一个矮瘦的中年妇人走了出来,高颧骨,宽嘴巴,一双眼里闪着警觉,她朝墨儿微微侧了侧身子,小心问道:“这位是?”
墨儿知道她是老大彭影儿的妻子曹氏,忙站起身,未及回答,彭针儿在一旁道:“这位是赵公子,是官府差来的,隔壁的康老大昨晚死了,他是来问事儿的。”
“康大郎死了?”曹氏张大了眼,十分惊异。
“隔壁才闹嚷了一阵子,嫂嫂没听见?”彭针儿问道。
“我身子有些不好,才躺着,听到有人哭嚷,没在意。原来是康大郎死了——”
墨儿见曹氏言语神色间似乎始终在遮掩什么,听到邻人死,也并不如何伤悲。
他开口问道:“大嫂,你知不知道隔壁康家的妻子和儿子去了哪里?”
“他家妻小?不是回娘家去了?”
墨儿盯着曹氏的眼睛,见她神色虽有些纳闷,却并没有躲闪,似乎真的不知情,于是转头问彭针儿:“彭三哥知不知道?”
彭针儿笑起来:“我哪里会知道?那康老大心胸极窄,最爱吃醋,多看他家娘子一眼,都要嗔怪你。平常我就是见到他家娘子,也装作没见。那孩子倒还嘴甜,有时我也会卖点糖果子给他。怎么?他家娘子和儿子也出事了?”
墨儿见彭针儿说话虽然油滑,却也只是惯常形色,并没有什么遮掩躲闪。他心里暗暗纳闷,这叔嫂两个心里一定都藏着什么,但对于康潜及其妻儿,却似乎真的并没有嫌疑。
于是他避而不答,又问道:“彭大哥和彭二哥今日都不在?”
曹氏的目光又忽地一霎,彭针儿倒仍是笑着道:“大哥回家乡去了,二哥还在街上说书赚口粮呢。”
墨儿发觉这叔嫂的隐情似乎在彭家两兄弟身上,便继续问道:“哦?彭大哥走了多久了?”
彭针儿眨了眨眼,转头问曹氏:“嫂嫂,大哥是寒食那天走的吧。”
“嗯——”曹氏语气稍有些犹疑。
墨儿确认隐情在彭影儿身上,又问道:“你们家乡是哪里?”
彭针儿答道:“登州。”
“来京城几年了?”
“十来年了。”
“你们是去年才搬到小横桥这里?”
“嗯。是二哥找的房子。比我们原先赁的那院房子要宽展些,钱却差不多。”
墨儿想再问不出什么,便起身道:“打扰两位了,在下告辞。日后若有事,恐怕还要叨扰。”
彭针儿随口道:“要到饭时了,赵公子吃了饭再走吧!”
墨儿看曹氏白了彭针儿一眼,便笑道:“不了,多谢!”
他仍从后门出去,临出门前,彭针儿悄声问道:“隔壁娘子真的出事了?”
墨儿见他眼中全是猎奇偷鲜的神色,越发确证他的确并不知情,便只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他回到康潜家,武家妯娌和其他围观的邻人都已散去,康潜的尸首仍横在厨房地上,蒙了一条布单。康游跪在尸首边,已不再哭,垂着头木然不动。
墨儿又悲疚起来,但随即告诫自己,悔之无益,尽快查清案子才是正理。
于是他小心过去,低声问道:“康二哥,有些事得问你,不知——”
康游仍然不动,不过沉声应了句:“你问吧。”
他的左额刺了几个墨字:“云翼第六指挥”,是当初从军时所刻军旅番号,虽然如今已经由武职转了文职,这黥文却仍旧留于额头,有些刺眼。
“康二哥,是你去取的那个锦袋吗?”
“是。”
“康二哥是从哪里取来的?香袋里那双耳朵又是怎么一回事?”
康游目光微微一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