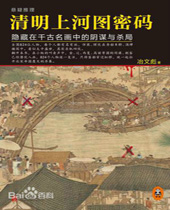清明上河图密码-第51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有天天气晴暖,阿慈端了盆热水进来,拧了一把帕子,伸手要解开他的上衣,看来是要给他擦身子。他猛然想起自己锁骨上有颗痣,阿慈的丈夫丁旦定然不会有。他吓得身子忙往后缩,阿慈有些诧异,抬眼望向他,他更加惶愧,脸顿时红了。
阿慈越发纳闷,盯着他看了一阵,但并没察觉什么,便又低下头,伸手轻轻撩开他的前襟,他再不敢动,只能听之任之。果然——阿慈低低惊呼了一声,身子一颤,手里的帕子掉落在他胸口,随即,急往后退了两步,盯着他,满脸惊怕。
何涣心里顿时冰冷,但也随即释然,他鼓了一阵勇气,又清了清嗓子,才低声道:“我不是你丈夫……”
阿慈眼中一惊,在他身上慌乱扫视,良久才轻声问道:“你是谁?”声音有些发颤。
“我叫何涣,那天在独乐冈被你丈夫打伤,换了身份……”
阿慈眼中闪过一阵悲怒。
“我并非有意要欺瞒你,那天你丈夫是从后面偷袭,我并没有看到他。醒来后就已经在这里了,我想明白后,本要说,但嘴肿着,说不出话来,这两天能说话了,却又怕惊到你,因此始终不敢说……”
阿慈身子一直颤着,听到后来,眼中滚下泪来,她忙伸手擦掉眼泪,低头转身,疾步出去了。
何涣躺在床上,怔怔望着幽暗空门,心中不知是悔,是怅,还是释然。
呆卧在床上,他正在忐忑思虑,那个老妇人急匆匆赶了进来,是阿慈的婆婆蓝氏,这一阵她曾进来取过几次东西,却根本未看过何涣一眼。
这时蓝婆却圆瞪着一双老眼,满是惊怒:“你是谁?!”
“在下……在下名叫何涣,是府学学生。”
“你好大的胆子!读的那些书全读到猪肠子里去了?竟敢装头扮脑,混到我家里来?”
“老伯母恕罪,在下绝非有意欺瞒!”何涣忙坐起身子。
“呸!”一口唾沫喷到何涣脸上,何涣却不敢去擦,蓝婆伸出皴皱的老指指着他的鼻子,大声痛骂,“到这时候了,你还装出个竹筒样儿来混赖?说!你究竟想怎么样?”
“我这就走……”何涣忙翻身要下床,腿伤未愈,疼得一抽。
“你在我家白吃白喝,臭气都没散,就想走?”
“依伯母之见,该当如何?”何涣正挣着要下床,只得顿住。
“你这等泼赖货,欺负我孤儿寡妇,抓你到官府,打断你腿,揭了你皮,发配三千里外,都抵不了你这罪过!”
何涣吓得全身发软,忙连声求告:“伯母,我真的并非有意欺瞒,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何受了伤,醒来就躺在你家床上。据我猜测,恐怕是你家女婿将我弄成这个样子……”
“什么?”蓝婆顿时惊住,瞪着他,半晌才问道,“他为何要这么做?”
“我也不知,恐怕是贪图我家门第家业。”
“门第家业?你究竟什么来路?”
何涣犹豫起来,他不愿说出家世,但若不说,恐怕难让蓝婆消气,便只得实言:“我家住在金顺坊嘉会苑。”
“嘉会苑?何丞相是你的……”
“祖父。”
蓝婆眼睛睁得更大。
“伯母若不信在下,可以去嘉会苑瞧一瞧,你女婿应该正住在那里扮我。”
“好,我这就去!反正你也逃不掉。”
下午,蓝婆回来了,何涣忙又坐起身子。
蓝婆满眼惊疑愁闷:“那烂赌货果然在嘉会苑,我见他走出门来,虽然装出个富贵样儿,但那贱赖气几世也脱不掉。他那狗友胡涉儿也跟在身边。我向看门的打问,说他家公子前一阵头脸也受了伤,才刚刚好些……”
何涣虽然早已料到,但真的听到,仍然浑身一寒,像是被人猛地丢进了阴沟枯井里,用烂叶掩埋了一般。
蓝婆望着他,竟有些同情:“不能让这烂赌货这么便宜就得计,我去找人来抬着你,咱们一起去告官!”
何涣正要点头,心里却随即升起一丝不舍,不舍这贫寒但轻松无重负之身份,更不舍……阿慈……蓝婆催道:“喂!你还犹豫什么?你堂堂宰相之孙,还怕他?其他的你不必担心,我已经问过媳妇了,你并没有玷污她的清白。”
“但……毕竟我与她同……同床了这许多天……一旦告官,她的名节恐怕……”
蓝婆一听,也踌躇起来,气叹道:“唉,这倒也是……我这媳妇命太苦,怎么偏偏尽遇上这些繁难……这可怎么才好?”
何涣鼓足了勇气,才低声道:“她若是……若是不厌烦我……”
蓝婆一惊:“你是说?”
何涣抬起眼,快快说出心中所想:“我愿娶她为妻!”
“这怎么成?”
“只看她,若她愿意……”
蓝婆张大了嘴,愣在那里。
话说出口后,何涣也觉着有些冒失,自己和阿慈毕竟只相处了十来天,又没有说过话,是否自己一时情迷,过于仓促?
自那天说出真相,阿慈再没进来过。何涣正好摒除杂念,躺在床上,反复思量,想起祖父所教的观人之术。祖父由一介布衣书生,最终升至宰相,一生阅人无数。致仕归乡后,他曾向何涣讲起如何观人,他说:“静时难查人,观人观两动,一是眼动,二是身动。”
眼动是目光闪动之时,有急有缓,有冷有热,有硬有柔,以适中为上。但人总有偏移,极难适中,因此,以不过度为宜。目光动得过急,则是心浮气躁;过缓,是阴滞迟钝;过冷,是心狠意窄;过热,是狂暴猛厉;过硬,是冷心酷肠;过柔,是懦弱庸怯。
至于身动,是举止。急缓,软硬,与眼动同。另外还有轻重之别。举止动作过重的人,性蛮横,多任性,难持久,易突变;而过轻的人,性狡黠,善隐匿,多伪态,难深交。
何涣以祖父的观人法仔细度量阿慈,阿慈当是轻、缓、柔、冷之人。
她的轻,绝非轻浮,也非隐伪,只是多了些小心,不愿惊动他人。
她的缓,并非迟钝,除小心外,更因天性淡静,不愿急躁。
她的柔,不是柔懦,而是出自女子温柔性情。
她的冷,乍看似如冰霜,但绝不是冷心硬肠之人,看她这些天照料自己,丈夫虽然令她寒心,她却不忍置之不顾,换药喂饭时,再不情愿,也仍旧细心周至。
这样一衡量,何涣心中顿时豁然:我绝非只贪图她的样貌容色,更是爱她的性情品格。
至于门第身世,世间择婿择妻,无非看重富贵二字,对我家而言,这两个字值得了什么?我只需看重她的人,只求个一心一意、相伴终生。
只是以他现在身份,没办法明媒正娶,但他想起祖父当年成亲也极寒碜,那时祖父尚未及第,两边家境都寒窘,只能因陋就简。父亲成亲,更加仓促,当时祖父远在蜀地为官,祖母在家乡病重,以为不治,想在辞世前看到儿子成家。母亲则是同乡故友之女,孀居在家,祖母一向看重她温柔端敬,并不嫌她是再嫁,自作主张,找了媒人,将纳采、问命、纳吉、纳成、告期、亲迎六礼并作一处,才两三天,就将母亲娶进门来,只给祖父写了封急信告知,祖父一向开通随和,并未说什么。何涣来京时,祖母和母亲都曾说过,信他的眼力,若碰到好的亲事,只要人家女儿人品心地好,他自己做主也成。
于是,何涣便想了个权宜的法子,只用一对红烛,一桌简便酒菜,完了婚礼,只在心诚,无须豪奢。
等蓝婆进来送饭时,他郑重其事说了一遍。
“你这是说真的?”蓝婆仍不信。
“婚姻岂敢儿戏?这两天,我反复思量过,才敢说出这些话。”
“你这样的家世,婚姻能由得了你?”
“我家中如今只有祖母和母亲,来京前她们说若有好的亲事,我可以自己做主。”
“我仍是不信,你真的愿意娶阿慈为妻,不是妾,更不是侍女?”
“正室妻子。”
“这样啊……”蓝婆皱起眉想了想才道,“我得去问问阿慈,她看着柔气,其实性子拗得很。上回招丁旦进来,她百般不肯,是我逼了再逼,最后说留下万儿,要撵她一个人出去,她才答应了。谁承想招进来这么一个祸患。这回我再不敢乱主张了。你等等,我去问问她——”
蓝婆说着走了出去,何涣听着她将阿慈叫到自己房中,低声说了些话,始终听不到阿慈的声音。
过了半晌蓝婆才又走了进来,摇着头道:“不中——阿慈说不得已嫁了两次,命已经够苦了,不愿再有第三次。”
何涣一听,顿时冷了,他只想着自己如何如何,竟没有顾及到阿慈的心意,不但一厢情愿,而且无礼之极。
“不过,她让我来向你道谢,多谢你能这么看重她。”
“她就没有一丝一毫看中于我?”
“她说你是极好的人,是真君子,自己万万配不上你。”
何涣一听,心又活转:“她是极好的女子,说什么配不配得上?求老娘再去劝说劝说,何涣并非轻薄之人,这心意也绝非一时之兴。”
“我也这么说了,她说自己虽不是什么贞洁烈妇,但毕竟还是丁旦之妻,就算夫妻情分已尽,但名分还在,怎么能随便应许别人?若答应了你,不但自己轻贱了自己,连公子的一番深情厚谊也糟蹋了。”
“那我去找丁旦,用我家京城全部家产,换他一纸离婚书契。”
“你真愿意?”
“嗯!”
“小相公,那个赵不弃又来了。”齐全在书房门边低声道。
何涣一听,心里又一紧,看来是躲不过这人了。他只得起身迎了出去,赵不弃已走到院中,脸上仍是无拘无束略带些顽笑:“何兄,我又来了!哈哈!”
何涣只得叉手致礼,请他进屋坐下。看赵不弃一副洋洋之意,实在难以令人心安,但说话间,又的确并无恶意,反倒似是满腔热忱。自己瞒罪应考,的确违了朝廷禁令,既然赵不弃已经知道内情,他若有心害我,何必屡屡登门?直接去检举,或者索性开口要挟就成。难道是想再挖些内情出来?但除了瞒罪应考,我再无其他不可告人之处。看来不坦言相告,赵不弃恐怕不会罢休。
于是他直接开口道:“你那天在应天府见到的不是我,应该是丁旦。”
赵不弃略有些诧异,但想了想,随即笑道:“你和丁旦……原来是两个人?对……只能是两个人……你们可有血缘之亲?”
何涣摇了摇头。
“那真是太奇巧了。”赵不弃眼里闪着惊异之笑。
何涣苦笑一下:“是啊,我自己都没料到。”
他慢慢讲起前因后果——
关于和阿慈的亲事,经不住何涣苦苦恳求,蓝婆又去反复劝说阿慈。阿慈终于答应,不过始终坚持和丁旦离婚后,才能和何涣议亲。
对何涣而言,这其实也是好事。不告而娶,于情于礼都有愧于祖母和母亲。一旦泄露出去,阿慈也将背负重婚偷奸的罪名。等阿慈和丁旦离婚后,禀告过祖母和母亲,再明媒正娶,才不负于阿慈。
于是,他继续留在蓝婆家里,央求蓝婆不时去打探丁旦的消息,但丁旦现在是堂堂相府之孙,根本难以接近。何涣曾想过去告官,但又怕传扬出去,坏了祖父清誉,更怕丁旦反咬,会牵连到阿慈的名节。
一来二去,转眼又拖过了一个月。这短短一个多月,却是他有生以来最欢喜的日子。
他占了阿慈的卧房,阿慈便去蓝婆屋里挤一张床。但老小几个人,每天在一起,竟像一家人一般。不但阿慈,连阿慈家中的事事物物,何涣都觉得无比新鲜,每天帮着弄豉酱,筛拣豆子、泡水、蒸煮、调味、搅拌、腌存……都是他从未经见过的事,做起来竟比读经书、看诗词更加有滋味。
而阿慈,虽然言语不多,也时时避着他,但脸上似乎有了笑意,蓝婆和万儿也都格外开心。虽然何涣自己家中也和睦安宁,但毕竟有些规矩讲究,在这里,凡事都简单松活,让他无比舒心自在。
赵不弃一路听着,并不说话,但一直在笑。听到这里,才开口问道:“你一直没有去看看那个丁旦?”
“只去过一次,腊月底的时候,我趁天黑进城,到了我家宅子门外,远远见大门关着,看不到人,等了一会儿,我怕被人认出,就回去了。”
“丁旦赌光你家房宅钱物,你知不知道?”
“知道。是蓝伯母去打听来的。”
“你不心疼?”
“家祖、家父从来不愿我贪慕钱物。我只是有些惋惜,那些钱物本该用来救助穷困。”
“好!”赵不弃笑着赞了句,又问道,“你这一路奇遇,才过了一半,接下来,那位阿慈就变身了?”
“这你也知道?”
“当然,正月里到处都在传。”
何涣叹了口气。
第七章穿空移物术
五常百行,非诚,非也;邪暗,塞也。——周敦颐腊月转眼过去,到正月十五,阿慈说要去庙里进香还愿。
她和朱阁、冷缃夫妻约好了,何涣也想出去走走,他们四人便抱着万儿一起去。只要有外人来,何涣怕被看破,便尽量沉默,能少说话就尽量少说。朱阁夫妇只是笑他病了一场,竟连舌头都病硬,人也病木了,不过幸好没有多留意,也就没有察觉他的身份。
本来打算去大相国寺,但冷缃说那里人太多,四人商议了一下,说拜佛何必择庙宇,便就近去了烂柯寺。烂柯寺里果然没有人,连那个小和尚弈心都出去化缘了,只有住持乌鹭一个人迎了出来。
何涣不信佛,心里念着庙廊两侧的壁画,上次未及细看,阿慈和冷缃去烧香,他抱着万儿和朱阁去细赏那壁画。乌鹭禅师为人慈和,也陪着他们,边看边讲解画中佛祖、菩萨、罗汉、天女来历。
院子中央那一大树老梅开得正盛,这些年,天气越来越冷,黄淮以北,已经很难见到梅花,这株梅树却不知有几千几万朵,簇满枝头,一大团胭脂红霞一般。阿慈和冷缃见到,并没有立即进殿,一起走到梅树边赏玩。过了一会儿两人竟嬉闹起来,何涣听到笑声,忙回头去看,原来冷缃摘了一小枝梅花非要插到阿慈头上,阿慈不肯,两人绕着梅树追逐笑闹。
何涣和朱阁看着,都笑了起来,万儿在何涣怀里拍着小巴掌直乐,连乌鹭也忍不住笑出了声。冷缃正追着,裙脚被树后的铁香炉挂住,险些摔倒,阿慈笑着回去扶住了她,两人这才停止嬉闹。冷缃整理好裙子,去左边的茅厕净手,阿慈则独自先进了佛殿。
何涣见阿慈进去跪在蒲团上,才拜了一拜,忽然倒在了地上。他忙赶过去,冲进佛殿扶起阿慈,但一看到阿慈的脸,吓得手一抖,惊呼一声,险些坐倒——阿慈竟变了另一张脸!
粗眉、扁鼻、龅牙的嘴。
“阿慈变成了个丑女?”
赵不弃想着当时情景,觉得很滑稽,忍不住笑着问道:“怎么个丑法?”
“比起阿慈,远远不及……”何涣眼中露出当时之惊怕。
“她是在你怀里变的身?”
何涣黯然点头:“阿慈晕倒后,我忙去扶,才扶起来一看,她的脸已经变了。”
“后来你们找到这丑女的父母了?”
何涣点了点头:“那女子醒来后,看到我们,立即哭叫起来,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她说自己姓费,叫香娥,家住在酸枣门外,父亲是个竹木匠人。她正在后院编竹笼,忽然头一痛,眼前一黑,不知道怎么就到这里了。我和朱阁带着她去了酸枣门外,找到她家,她父母因她忽然不见了,正在哭着寻她。”
“这么说,那个费香娥没说谎?”
“嗯,我们送她回家后,她家的邻居都来围看,应该不会假。”
赵不弃和堂兄赵不尤一样,也从来不信这些鬼怪巫术,最早听到这件事时,便已觉得是有人施了障眼法,只是这法子使得极高明,能在众人眼皮底下大换活人。这手法纵使不及堂兄所查的客船消失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