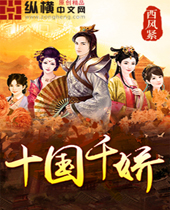十国千娇-第28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冯进珂听罢良久沉默了。
赵匡胤留意观察了一眼,当下便不再多言。
过了好一会儿,冯进珂才道:“我一个武将,不便对国事指手画脚。不过朝中司空郭元为与我交好,这事儿我与他说说。若是他认为有理,上书进言陛下,必能凑效。”
赵匡胤听罢,起身道:“大恩不敢忘。冯将军军务繁忙,末将便不多叨扰了。”
……果然不多久,北汉主就明确拒绝了交出赵匡胤的事。并且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理由,说是大周的武将受到了不公的对待,到北汉来,朝廷随时诚意款待云云。
……
周朝廷出主意的人是魏仁溥。东京得到消息,又一次在谈判上失败;不过朝廷再一次采用了老办法(耍流氓),谈不赢就要动手。
魏仁溥进言皇帝,趁议和不成,马上对北汉开战!
魏仁溥道:“此时便意图一举灭掉北汉,准备尚不充分,时机尚不成熟。但可先对北汉进行袭扰、试探,攻打蚕食其边境。此战的动静不能太小,咱们的主要目的也不是袭扰,而是试图吸引辽军来援。”
他回顾诸重臣,似乎已经忘掉了被北汉国拒绝和谈的不快,侃侃而谈,“北汉举国也就几万兵力,精锐不过两三万。我朝只要一支偏师出辽州,虚张声势,作势要大举进攻晋阳;北汉必请辽军来援。
辽军远道而来,一到晋阳,大周军便撤出北汉国。南撤观望,疲劳消耗辽军和北汉国力。为将来攻取晋阳做好准备。”
郭绍听罢觉得颇有道理,反正暂时还没把握一战攻下晋阳;和北汉进行拉锯袭扰的战争也是利大于弊。因为大周的国力远超北汉,最不怕与北汉消耗,正是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郭绍顿时就问:“尔等以为,调动哪些兵马妥当?”
魏仁溥最近很积极出谋划策,当下又拜道:“得要一股精锐,尚能在野战时保有优势。驻相州的龙捷军张光翰部,有精兵两万;另外新任昭义军节度使慕容延钊,手里有镇兵、淮南感德军数万之众,可调动一部人马为援。”
郭绍心里又想着授权给谁来主持此战,乍一想,侍卫司厢都指挥使张光翰、或昭义军节度使慕容延钊都可以胜任。但郭绍一时间想起了另一个人:符昭序。
河北的近况,没有大战。符昭序去河北部署兵力后,辽军应该不愿意在此时与大周军决战,迟早退走;郭绍就等他的奏报。
只不过河北那里的功劳,仍然不够提升符昭序的军功。
第五百三十一章不愿回头
阳光从木窗前的绳编帘子透进来,洒在桌子上形成一道道斑驳的横杠。郭绍已经搬了办公之地,从金祥殿西侧搬到了东侧。夏天这个方位很好,上午采光,下午庇荫,不像西边那么热。
这个地方经过修葺整理,十分宽敞。郭绍坐的地方就是办公的书房,北侧有一套宽敞的房屋,不仅可以“贴纸条”、存放军机卷宗,还能就近休息。西侧有一道门,出门又是一间房屋,而且有后门,郭绍可以在那间屋子里私下召见大臣,而且往来不用经过前面的正门。南侧是内阁辅臣办公之地,周围还有耳房可供内臣存放东西、休息……最前面才是翰林院、政事堂等每天派过来做杂事的当值官员。
郭绍正在翻阅一份卷宗,是前阵子从晋阳逃回来的细作头目写的,一些关于晋阳的情况。但是他们呆的时间太短,很多情报只是个大概,并不详细。
郭绍查了好一会儿,没有查到汾水和晋阳城的细致描述……他查这东西,是刚刚看到一份奏书,有人建议挖开汾水,水攻晋阳城。
另外还有人上书,用火药炸城,类似攻下寿州的干法。
……但是郭绍觉得故技重施,这回不一定能凑效。首先晋阳城的城墙比寿州更厚、更结实,寿州在南方虽然也是重镇,但墙体显然不如晋阳这种大城(寿春在北宋时期进行了重建,之前的厚度还不如后来)。而晋阳不可同日而语,据报,打地基的条石都砌了一丈高!底部墙体厚约二十步!
郭绍心道:厚度二十几米的包砖土墙,下面还有三米多高的条石地基,黑火药能炸开?理论上看,只要火药够多,应该有可能,但这就要求地道藏药室的空间更大,地穴工程也更难搞了。而且炸开的豁口极可能不像寿州城豁口那么容易攀爬、连马都跑得进去;有可能只是坍塌,夯土砖石对在豁口堵塞。
最要命的地方,赵匡胤在北汉国,他对火药炸城比较了解、也很重视,否则打晋州也不会学着干了……这回炸城,可能无法像寿州那般出其不意,北汉守军应该有所防备。
郭绍琢磨了一阵,仍旧觉得很发愁。
“晋阳,晋阳……”他低声念了两声,转身看着地图上的毛笔线条。
北汉国比南唐、蜀国都小得多,但这块地方着实让郭绍发愁。南方诸国灭亡前,内部问题很多,兵不堪战,且攻打有巨大的好处;北汉国恰恰相反,很像一块没肉的硬骨头。但是必须得拿下这块硬骨头,否则大周基业格局就没法打开。
郭绍很愁,也很不爽。这颗楔子一样的东西塞在那里,像一块阻挡理想的石头!
另一种愿望,这回若是打下了晋阳,必然不会让赵匡胤跑掉!
就在这时,书房门口左攸的声音道:“臣有事禀报陛下。”
郭绍抬头道:“进来说话。”
左攸走到御案前,弯下腰将两本奏疏放上来,说道:“臣刚刚才看到奏书,河北雄州来的。符将军(昭序)已将辽军驱逐出河北,正在雄、霸、易三州加强防备;请旨侍卫司龙捷军左厢还驻相州。”
郭绍听罢点头回应,他和朝臣们都料定了这样的结果。幽州辽军兵力有限,不可能愿意在河北大周地盘上与周军对决。
左攸又道:“这一份是大名府魏王(符彦卿)的上书,请旨来京朝贺。”
郭绍听罢心道,有的地方节度使请都不来,就像西北的折家、原来在河东的李筠这等人,若是下旨他们来京,还可能激起猜忌。符彦卿这个军阀却不同,主动要来朝贺;毕竟两个女儿都是大周朝的皇后。
郭绍便道:“我亲自批复,准魏王所请。另外叫人下旨符昭序,准龙捷军左厢回相州;让符昭序到京觐见,叙河北之功。”
“臣遵旨。”左攸拜道。
……郭绍给儿子取名字时,符二妹的儿子叫“翃”,是个不常用的生僻字,也有一点心思:若是符二妹的儿子将来继承皇位,能让天下人省事一点,少一些避讳;反正皇帝的名字基本不用,其实平时是用不上的,谁还能直呼皇帝的姓名不成?
他内心对两个儿子的选择,一则因为郭翃是嫡子,二则他觉得符家更可靠一点。但若符金盏也生了儿子,郭绍现在便没考虑清楚。
当天下直后,郭绍便去了滋德殿用膳。见了符家姐妹和李圆儿,在吃饭时谈起了符家的父兄都要进京的事。
如同往常一样,符二妹和李圆儿在饭后陪着喝了一会儿茶,便先离开了。郭绍要和符金盏单独谈“国事”,当然他们并非孤男寡女相处,饭厅后面的敞殿里,周围都有人走动。
又是一个黄昏时分,郭绍好几次和符金盏坐在这里说话了。
他确实提起了正事:“先帝驾崩后,二李谋反,符昭序亲身涉险在潞州取回了李继勋长子的头颅,避免了李筠和二李结盟,有功于国家。此番率军驱逐辽军,又立一攻……但他从未在战阵上立下实实在在的大军功,若是这样就建节,可能在军中要遭人非议。”
符金盏认真地听着。
郭绍继续道:“如今新建节的节度使,基本没什么实权了。但长久以来,建节仍然是武人进入高级武将行列的一种象征,仍旧很有作用。
我的意思,朝廷最近想对北汉用兵,可以让符昭序借着驱逐辽军的风头,挂帅带兵打这一仗。”
符金盏一直没有打岔,耐心地等郭绍说完,这才开口道:“陛下所言极是,可我有一事不解,为何陛下要专门栽培昭序?”
郭绍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道:“魏王虽有威信,却已年迈,符家虽有不少镇守武将,但仍缺一个真正有实力的大将。”
他顿了顿,“世事难料,万一我有什么意外,我希望金盏手里能用的实力能多一些。”
符金盏脸色一变,看着他摇摇头:“你还是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郭绍随口问道。
符金盏沉声道:“你贵为皇帝,仍不是天下人的全部,但你是我的所有。”
“可是……”郭绍有些不解。
符金盏轻轻说道:“人是不愿走回头路的。”
第五百三十二章心都乱了
天刚蒙蒙亮,古朴的三清殿的一间房里,亮着朦胧的灯光。早早就起床的人是太贵妃张氏,青灯古砚,张氏正在慢慢地抄写庄子的字句。只有跟随古人留下来的妙想,她才能游离天外。
夜太长,张氏没什么事做睡得早,睡眠时间太长头都睡晕了,还会造成难以入眠的困境;所以她起得很早。
一个中年妇人敲门走了进来,小声说道:“昨夜李太妃召奴婢见面了。咱们要进出万福宫本就不容易,还好奴婢常来往做些杂活;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奴婢便来不及来告诉娘娘。今天一早,奴婢便赶紧来禀报……”
这妇人是太祖时期就在张氏身边的人,人倒是忠心耿耿,就是很啰嗦。张氏当下打断她的话:“李氏见你所为何事?”
妇人道:“她想见您一面,说是有话与娘娘谈谈。”
“哦……”张氏手里拿着毛笔,在砚台里的墨水上反复蘸来蘸去,就好像一个无聊的小孩在玩泥巴一样,做一些琐碎而无用的事。
过得片刻,张氏又问:“她想谈什么?”
妇人道:“奴婢不知,李太妃也没说。”
张氏觉得和这个人没什么好谈的,多年来一直都有怨仇。最起初是怎么结怨的,连张氏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根本原因是争宠,那人认为她没怀上龙种全怪张氏;后来各种大小恩怨太多,积怨便是如此。但张氏又忍不住想见见,看她究竟想作甚么,不然这事儿会在心里挂念着,猜忌和担心……
“我又不怕她,见见她又能如何?”张氏道,“你和我一道回去,等会我换衣服,你去让咱们的人准备一下,随我去见李氏。”
有点职责的宦官宫女进出万福宫还比较容易点,嫔妃一旦住进去,一般是不能出来了。张氏能出来,完全是因为上位者的旨意允许她到三清殿清修。
没多久,张氏从三清殿回到万福宫时,心里仿佛一下子感到了凉意。三清殿比这里还冷清,但不知怎地,张氏觉得万福宫更加可怕。
她回去收拾了一番,带上了平时和她要好的十几个宫妇一起去见李太妃。
李太妃竟然到迎接到了门口,看到张氏带这么多人,神色微微一变。她稍微一愣,忽然一屈膝把双手抱在腰侧作了个万福,眼睛看着张氏的脚尖说道:“恭迎太贵妃娘娘。”
李太妃这般做法,却是让张氏感到十分意外。虽说也有的妇人虽然有隙、表面上也能客客气气,但那种多半积怨不深;张氏和这妇人不同,以前两个人当面也没有好话。
张氏打量了一番李太妃,从举止神态上,倒看不出有什么敌视的迹象。此人年纪照样不大,不过身宽丰腴,看起来就没有丝毫修长纤细之感。
张氏冷冷道:“李太妃多礼了。”
李太妃请她在榻上入座,回顾她带过来的十几号人,轻轻提道:“太贵妃娘娘,可否借一步说话?”
张氏立刻回应道:“有什么话现在说不行?我们行得正站得直,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要说罢?何必窃窃私语,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在商议什么秘密阴谋,平白遭人猜忌,你说是也不是?”
李太妃听罢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沉默了好一会儿。张氏见状也提防着她当场发作了,但是她却忍了下来,竟然露出一丝讨好的微笑。
张氏心里揣测,此妇定然是从哪里听说自己的外甥得到新君的重用了。加上张氏居然能去三清殿清修……出家不是那么容易的,正如多年的经验、嫔妃一旦住进来了几乎出不去,哪怕是去三清殿,那里至少还有机会和外面的人接触。除非是得到了皇宫里真正有权力的人的准许,张氏便是如此。
李太妃恐怕已经从种种迹象猜出张氏重新攀上权贵了;说不定新皇在三清殿见面的事儿都泄露了出来。不然的话,李太妃能在自己面前做出低眉下眼的表情?
想起以前的种种委屈、受过的闷气、背地里的中伤,此时张氏心里忍不住冒出一股子快意,就仿佛在闷热的房间里忽然感觉到了一阵凉风一般,通透而爽快。
但是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丝寒意。因为张氏明白,李太妃无论表现得多么诚意,实质是没有办法之下的忍耐求全;一旦她有机会,肯定是想报复回来的!
果然李太妃沉默许久之后,当众小声道:“今天见太贵妃娘娘,妾身是想道歉……”她说的时候脸都憋红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服软,声音小得像蚊子扇翅膀。
张氏冷冷看着她,自己都替她难受,听那声音就知道说出来挺不容易。但张氏沉住气,目光直视着她,心道:反正积怨已经够深了,我怕她也没用。
李太妃吞吞吐吐道:“以前有些误会,太贵妃娘娘大人不记小人过,我们重归于好如何?”
张氏不动声色,缓缓开口道:“哪里有什么误会?我对李太妃从没什么成见的。”
李太妃喃喃道:“那就好,那就好……”
张氏既没有让步同意重归于好,因为不可能;也未得志就太过分。
她既不是害怕李太妃,也不是气量大。实在是经历过起落,明白不是什么时候都能得意。特别是妇人,本来就是依靠别人的……
在外带兵的曹彬,自然是符金盏、郭绍等对自己比较宽容的原因之一;但张氏很清醒,她不能把曹彬当作自己得意的筹码。曹彬又不是她的儿子,绝不会因为姨娘影响他的忠心;何况就算张氏继续住在冷宫,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曹彬也不愿意管这事。张氏能够很具体地考虑到一种情况:假设权贵听信了什么谗言,对自己不喜,那就没必要宽容了。
而新皇郭绍不过是见了自己一面,究竟会怎样?张氏也不敢确定。最有利的情况,当然是郭绍对自己有好感,他一句话就能决定自己命运。
这也是张氏想方设计亲近郭绍的原因,她的动机当然不纯,里面夹杂太多现实和权谋……可是,张氏回忆起来,越微小的地方却莫名很温暖,那些细致之处却不是权谋。
她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双粗糙的大手,放在他的绶带上,那一刻,他不知该不该解衣关怀。她仿佛感受到了那一瞬间的徘徊。
……
金祥殿内,郭绍青筋凸出的粗手拿起了一块玉石镇纸,放在墨迹未干的一张纸上。温润光洁的和田玉与他的手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这里是位于办公书房北面的一套数间房,作为休息的地方。不过仍旧很宽敞,特别是作为几间暖阁中央的厅堂,占地很大。这里非常安静整洁,坐在这里十分舒适,甚至宫廷里的人专门对开了窗户、考虑通风,窗户用编制帘子遮掩,既比较隐蔽,又偶尔有凉风吹过丝毫不觉得闷。所有的摆设和用度都用料贵重,做工精细;连他咳嗽时捂着嘴的手绢,也是上等丝绵料子,拿在手里既透气又柔滑。
郭绍这两天有点感冒,倒是不严重,主要咳嗽。
他一个风餐露宿的武夫,而今却坐在了这里,有种在温室里享受的感觉。不过这样的环境还是很有好处,思考事儿的时候更容易集中精神,因为所有的细节都很顺心,不容易造成莫名细微的烦躁。
就在这时,李尚宫走了进来,款款执礼道:“陛下,您要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