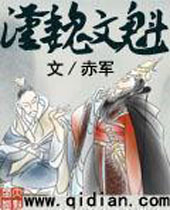汉魏文魁-第5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后结论不对,判案不公。耿县令他们就奇怪了,既然证据确凿,那宁可就该死罪啊,判得有什么不对了?
只见是勋面带微笑,胸有成竹地问道:“那宁可虽为隔壁老王之子,但自小即从宁彤,为宁彤认为己子,老王亦未曾前往索要过,是吧?”
屠县丞说:“即便如此,亦无借种之事,亦非正式过继,故此老王实为宁可之父,宁可殴父是实……”
是勋微微点头,打断了他的话:“君之误判,正在于此。”说到这里,他缓缓地扫视在坐众人,一字一顿地说道:“有一段书,各位或者读过:‘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
耿县令听到这儿,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心说要完!
第十五章、春秋断狱
是勋背诵的,乃是《春秋断狱》当中的一段话。
《春秋断狱》,又名《春秋决事比》或者《春秋决疑》,乃是儒家圣人董仲舒所写。因为汉律直承秦律,虽然作了一定程度的删改和简化,仍然显得太过死板和繁琐,所以董仲舒就代入儒家思想,对几十个他认为判得不公的案件加以重新审定。到了东汉朝,儒家思想已经彻底占据了主导,于是董仲舒这一套就被广泛运用在了审案当中。
说白了,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道德应该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凡是法律上条文有漏洞的,可以用儒家思想来填补,凡是法律上合理但不合情的,也可以用儒家思想来修正。
其中,董仲舒就说过这么一个案子:某甲有一个儿子某乙,很小就送给了某丙,某丙一直把这某乙抚养长大。后来某甲因为喝多了酒,就对某乙说:“我是你爸爸。”某乙当场就怒了,说我才是你爸爸呢,你丫又不是黑爵士我也不是天行者……好吧,这一句可以忽略。总之,某乙一怒之下,就打了某甲二十棍子,某甲因此就把某乙给告了官。
这情形就跟宁可和隔壁老王之间发生的纠纷很象,按照汉律,没有正式的过继文书(也包括借种生子的文书),那某甲就是某乙的爸爸,某乙打爸爸就是大不孝,该当死罪。但是董仲舒却说,某甲虽然生了某乙,却并没有养育之恩,事实上他跟某乙之间父子之义已绝,所以某乙不算打爸爸,不该判大不孝的罪。
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东汉的活人为了践踏死法律,就经常拿这种“春秋断狱”法出来办事儿,而且朝廷还真认,士人当中也会引为美谈——无他,因为儒家思想最高,法律你且滚边儿上玩去啵。
这回是勋也用了这个法子,当场就要判宁可交纳打人的罚金五百钱,然后当庭释放。黄县尉当场就急了,连叫:“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律法上不是这么说的啊!”是勋轻蔑地瞥了他一眼,心说你也就这水平了,白长着一张士人面孔,竟然如此的无学、不文。
还是屠县丞有点儿学问,还打算强辩,说:“董子原文‘甲有子乙以乞丙’,定是签了过继的文书,故此不该死罪,这与宁可之案……”是勋冷冷地答道:“若真如此,按律判定即可,董子又何必堂皇记录在册?”
耿县令长叹一声:“罢了。”他把袖子一扬,露出半截牍版来,问是勋:“阁下可知此为何物?”是勋摇头。耿县令说:“此乃耿某弹劾阁下索贿之章!”
是勋闻言,不禁仰天大笑:“哈哈哈哈哈~~耿令尽可上章,几位皆可上章。”说到这里,突然把脸一板:“且看诸君可能动某分毫?再一事说与耿令听,卿以为曹济阴罢免汝等,还需要奏于朝廷吗?如今朝廷安在?!”
照道理来说,县令都是朝廷任命的,也该由朝廷来罢免,即便郡国守、相,甚至是州牧、州刺史,都没有直接的任免权。倘若按照正规流程来走,是勋身为督邮弹劾耿县令,曹德就应该把他的弹劾理由抄上一遍,再呈给朝廷,由尚书台作出决断。虽说只要理由充分,尚书台一般不会驳回郡国守、相的弹劾,但有了这么一个缓冲,耿县令还能想办法转圜,或者去走走别的路子。既然耿县令同时也弹劾了是勋,那么倘若他因为种种原因不被罢免,是勋肯定就得吃不了兜着走啦——起码面子是丢光了。
可问题是现在不是太平时节啊,没几个人再走这种正规流程啦!关东诸州,往往连刺史都由地方推举,还有几个郡国守、相或者县令长是由朝廷任命的吗?还有几个郡国守、相或者县令长是由朝廷下诏罢免的吗?正相反,往往被关西军阀控制的小朝廷任命的很多地方官员,还没到任所就会被人轰回来,某些是文轰,更多的是遭到“操戈而逐之”,能保住小命儿就很不错了。
曹操这个兖州刺史是朝廷任命的吗?曹德这个济阴太守是朝廷任命的吗?他们要想罢免一个县令,还用得着奏报朝廷?
所以是勋这句话一出口,耿县令立刻面如土色,哑口无言。
是勋一行人当天就离开了成阳县城,当晚寄宿在宁可的一处庄院当中。宁可小命得保,对是勋是千恩万谢,是勋说不必谢,你昨晚曾说愿意献出所有财产来酬答我,这承诺还有效吗?宁可犹犹豫豫地点头。是勋就说,你也不用把全部财产都拿出来,我也分毫不取,你尽快把一半的田契和一半的浮财,全都捐到郡府去,并且把这些天的所历所经,所见所闻,全都备悉禀报给曹济阴知道。否则的话,嘿嘿,“我能活汝,亦能杀汝!”
宁可得保一半家产,于愿已足,当下喏喏连声。是勋转过头去又问吴质,说我还要继续行县,你是继续回乡去做你的游徼呢,还是愿意跟着我,做我的宾客。吴质连连鞠躬,说:“上官清廉正直,又救下了宁可的性命,小人感佩万分,愿意从此跟随上官,以效犬马之劳。”
是勋接着又问卢洪,说先生大才啊,何必屈身于寿张县内,做一名小小的上计吏呢?不如也跟了我吧,或者等我回去以后,禀报曹兖州,给你个大点儿的官儿做?可惜卢洪只是笑着摇头,说:“程令于某有大恩,暂时不愿相背。洪无尺寸之功,也不劳长官荐举。”是勋劝他不动,只得暂且作罢。
第二天一早,他们离开宁家的庄院,转道向西,前往句阳县。果然正如吴质先前所说,句阳的吏治还算清明,起码是没让是勋挑出什么错儿来,也没发现什么不轨的蛛丝马迹。再往后乘氏、成武、单父……这么一路走下去,所到之处先是微服私访,接着封查府库,又揪出来两名贪赃的县丞和一名怠政的县令,全都向曹德具文弹劾,其余官吏,也都好生地受了一番敲打。
一大圈子绕下来,等最后进入郡治定陶,都已经初夏了。是勋进城见了曹德,交卸任务,曹德摆宴给他接风,又详细询问了这一路的见闻,二人相谈甚欢。虽说两人的身份都不同往日——当初即便曹德戴着个故三公之子的帽子,终究和是勋一样都是白身——如今在官场上等级差很明显,但曹德完全没把是勋当下属来看待,是勋也觉得跟曹德真可以脱略了形迹,以朋友相交。
终于宴罢,曹德坐到是勋的身边来,拉着他的手连声说:“宏辅啊,这趟可是辛苦你了。”是勋假模假式地摇摇头:“为曹老板工作嘛,不辛苦。”曹德一愣:“你叫我什么?”是勋赶紧撇清:“故乡土语而已。”心里话:我说的曹老板还真不是指你,是指你哥。
可是眼见得曹德就把脸给拉下来了,把眉毛给吊下来了,连声叹气:“那些贪官污吏实在可恨,可是你这一路上也弹劾得太多了点儿……就说成阳吧,一县官吏都被你给弹劾了……”是勋一愣,忙问:“你不打算罢免他们么?”曹德说上个月就连锅端啦,可是这么一搞,我手头本来可用的人就少,成阳便彻底变了空县——
“我已经跟我哥说好啦,再借宏辅你几个月,暂代一下成阳县令,如何?”
我靠!是勋闻言不禁勃然大怒,心说你借我还借上瘾啦?我这儿一大圈兜下来,连家还没回呢,你又要我奔成阳县去蹲着,你丫还有没有人性了!可是当不住曹德连番央告,还答应他可以先回家歇几个月,只要八月前赶去上任,别耽搁了秋收就成,是勋推了半天推不过去,也就只好捏着鼻子认了。
曹德这家伙,你别瞧他表面老实,其实一肚子都是坏水儿,别瞧他跟戴个石头帽似的存在感很低,真要黏上身来,还真跟鼻涕似的甩都甩不掉。最终是勋只好感叹自己遇人不淑……啊不对,应该是交友不慎。他不禁想起了前一世常听损友们说起的那句话:“队友嘛,就是用来坑的。”
低下头去想了一会儿,是勋对曹德说,不如我给你推荐几名人才吧。曹德说好啊好啊,愿闻其详。然而是勋先不提人名,却问对方,说我这好几个月到处乱跑,消息闭塞,不知道青州如今情势如何?
曹德说你问我还真问对了,我哥前几天才刚有信来,顺便就说明了一下周边形势——徐州很稳,司隶表面平静,其实暗流涌动,至于青州……
“去岁,袁绍与公孙瓒争夺青州,袁军自勃海而入乐安,平原相刘备发兵以邀其背,于河上为袁将蒋奇所破——此事宏辅或有所闻。逮至年终,袁军已尽取乐安、齐国,驱逐朝廷所命青州刺史焦和,而以蔵洪代之,公孙瓒所表青州刺史田楷则据平原、济南,连番鏖战,胜负难分。前闻袁绍已命其长子袁谭驰援,先在邹平大破田楷,又在漯阴击破公孙瓒所署兖州刺史单经,刘备只得退守黄河以北。此外,袁军游骑出入北海、东莱,孔文举、蔡伯起皆不能御。以此形势来看,袁谭尽得青州,也就在此数月之内了。”
是勋一边儿听一边儿点头。袁谭跟田楷、刘备等人争夺青州的大战,史书上语焉不详,光知道前后打了两年,杀得“野无青草”而已,穿越过来以后,终于可以补上这块空白啦。等到曹德说完,他伸出两枚手指来:“眼见孔北海不能保国,则可遣人于其署中去迎来二人……”
“愿闻其名。”
“一个,便是某大伯父,营陵是子羽,现居北海国相五官掾之职;另一个亦营陵人也,姓王名修字叔治,现为高密令。此二人政务娴熟,持身亦正,皆国之循吏也,若不往召,或为袁氏所得。还有北海太史慈字子义,奉养老母在家未仕,某前致书,请他南下,尚未回复,君可……”说到这儿,他突然脸色一变,就此顿住话头,不肯再往下说了。
第十六章、举贤任能
是勋说要给曹德推荐人才,提了一个是仪,提了一个王修,然后才刚提了半个太史慈,突然间就哑了火。曹德不禁就问啦:“太史子义之名,我亦有所耳闻。宏辅住口不言,莫非此人不易招致么?”
是勋心说招不招在你,来不来在人家,这我可打不了保票。要是按照slg游戏的惯常设定,只要“相性”别差太多,只要你派个合适的人去招,对方肯定上门,但在现实社会当中,那问题可就复杂多了。在他印象里,王修最后是跟了曹操的,但那要等官渡大战以后,这会儿论起招牌来,明显袁绍比曹操亮,袁谭也比曹德亮,曹德后下手是肯定遭殃啊,先下手能不能为强,也还在未知之数。
是仪和太史慈在原本的历史上都跟了孙家,那就有一半儿出于无奈——你都已经跑江东呆着去了,不跟孙家还能跟谁?可是如今凭空多出了自己这只小蝴蝶,更因为这只小蝴蝶,使得曹德保住了小命,还一步登天当上济阴太守,要是趁这二位南渡长江前就先给拦下,那就有罗致麾下的希望。当然啦,希望归希望,成功的几率谁也算不出来。
可是为什么是勋提到太史慈,才说了一半儿就突然打住呢?他随即就给曹德亮明了答案:“子义文武并兼,非百里才也,可为大将。召来济阴,恐有所屈……”王修和是仪过来,你把他们当属吏,当宾客,或者放出去做个县令、县丞啥的,那都不算屈才,可是太史慈不同啊,人家将来有希望做江东有名的上将,跑你这么个小小的济阴郡来窝着,那不是大材小用吗?
“原来如此,”曹德听了这话,倒是也不生气,反而腆着张脸凑过来说,“我即刻派人去延请这三位。太史子义终究是白身,来我这儿当个属吏、县尉啥的,也只是第一步而已,他的能耐要真有宏辅你说的那么强,难道我就不会把他推荐给我哥吗?人才从来不嫌多,我这儿是缺人,我哥那儿也不是说就已经人满为患,挤不进去个太史子义了呀。”
好吧好吧,随便你。是勋想了一想,干脆又把卢洪推荐给了曹德,说程立是只鹏鸟,当县令委屈了点儿,卢洪也是只大雁,当上计吏更委屈。曹德顺手就取了笔墨来,把这几个人名儿全给记下了。
是勋在定陶盘桓了三天,然后暂别曹德,返回鄄城。他先进城见了曹操——曹操才刚打败了侵扰陈留郡的袁术军,征尘未洗,就先扯着是勋,大大地夸奖了他一番。曹操说让宏辅你做个假佐确实太屈才了,你就暂且先当一段成阳令吧——关于举孝廉的事情儿,你先别着急,我今年已经举了自家兄弟曹德了,等明年再让曹德把你给举上去,那就皆大欢喜。
汉代举孝廉是做官的正途,就跟后世考进士差不太多。按照原本的规矩,得要各郡国的守、相每年从自己辖区内挑选“孝顺亲长,廉能正直”的士人各一位,刺史是没有这个资格的。也就是说,是勋只有去求北海相孔融来举自己,而曹德得去央告老家豫州沛国的国相。可是到了最近这些年,一方面各地士庶的流动量都很大,守、相往往无人可举,而真正的人才又距离自己老家十万八千里,另方面随着刺史的权柄扩大,从监察官员跃升为地方军政首长,所以经常就有刺史举孝廉的事儿发生,也经常有守、相推举原籍不是自己辖区内的人士。所以曹操可以推举兄弟曹德,但曹德要是在自己都不是孝廉出身的情况下推荐是勋,多少有点儿不好听,恐怕有碍清议,所以曹操要是勋再等上一年。
照道理,孝廉不是说举就举了的,还得派公家马车把人送到京城里去核查,等待朝廷正式批复。可是到了这年月,朝廷又算神马东西了?关东诸侯当中,胆子小点儿的比方说陶谦,就还时不时地派人往长安送点儿贡品,假模假式地表示服从中央领导;胆子肥点儿的比方说袁绍,压根儿就不承认汉献帝(当然啦,献帝是死后才给上的谥号)是正统,说那是董卓擅立的伪帝。袁绍就曾经还想拥戴幽州牧刘虞当他控制下的“真皇帝”来着,可惜反对的人太多,刘虞本人也不乐意,这才无疾而终。
所以说,曹操推举自家兄弟为孝廉,只要装模作样写道荐表,然后往自家档案库里一塞,那就算齐活。等明年曹德推举是勋为孝廉,也可以照方抓药,只要济阴郡的档案库里有相关文件,手续齐全就行,至于长安的朝廷知不知道这情况,那又关我屁事儿了?
是勋倒是不着急,终究他表面上的年龄才刚二十一岁。汉顺帝时代曾经规定,士人得年满四十岁才能举孝廉,当然这规定压根儿就没人理,比方说曹操就是二十岁举的孝廉。但是自己终究出身不高,不能跟曹操这种三公的衙内相比,能在三十岁以前挂上个孝廉的正途,那就已经心满意足啦。
这一路回来,应该说是勋的心情是颇为轻松愉悦的。兖州迭经兵燹,才开春的时候他南下去行县,所到之处,就见城镇成墟,田地荒芜,好一派凄凉景象。“迩来村屯虚”那句诗就也是有感而发,当然啦,不如吴质的“乱塚连为埂,白骨浮为菰”之惨痛更深入骨髓。可是这回返回鄄城附近,就见曹操已经开始了屯田,播种既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