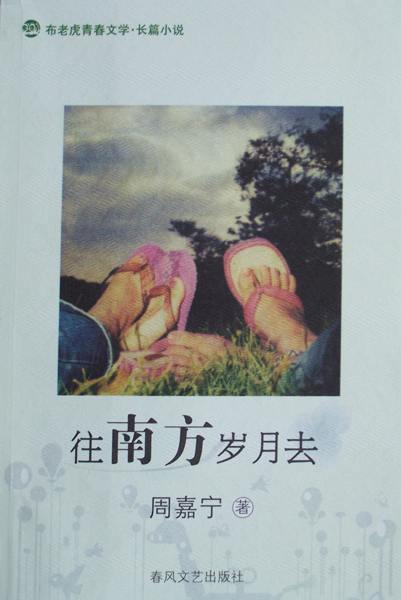劳碌岁月-第10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她有些喜悦又有些忧虑。
风吹过去,夜气里一切都似梦一般。一切都如风一般。
她站起身子,她走回房间里去,房间亮着灯,显得异常宁静。
她的对面是一面大的穿衣镜,她看到了镜子里的自己,冰清玉洁,静美若水。
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美丽。
她想起木青来,木青也保持了一种东西,一种最美的东西。
她躺到床上去,她睡去了,梦见了月,月光如水洒在庭院里,她看到了林箕天,还有陈莫与铁文,陈莫与铁文相互依偎着,好像是在芦苇地里,芦苇地里有风吹起,吹起陈莫乌黑的秀发,陈莫秀发上有橘黄色的小花,那小花艳丽,如同艳艳的唇,铁文望着陈莫,他发现那花儿狂乱了,陈莫的身子颤抖着,他听到了一种声响,竟似火一般哔剝燃烧,他抱紧了陈莫,他吻她芬芳的香腮,他的骨头都快酥软了,而白玉宛笑,她看到了林箕天,她搂着林箕天的笑,她的内裤已褪去,她两腿间水淋淋一片汪洋,她在快乐的呻吟,她快乐,她叫做白玉宛,她终于可以了,终于了……掠过那些恶毒的目光与眸子,掠过那些禁囿的天空,她一丝不挂与林箕天抱在一起,她笑了,幸福的笑了,有一种声音在在歌唱着,丧失了就是获得她犹若一只彩凤向上飞升,飞升,最后化作一声尖利的嘶叫,她睡去了,满足的睡去。在风声里,在芦苇丛里,在月下,她看到了铁文与陈莫紧紧搂抱在一起,他们赤裸裸的胴体上有亮晶晶的液体在流动,那是泪水是汗水还是露水,白玉宛的心中涌动着潮水。
那个夜晚很美。
那个夜晚铁文静静地在河边走着。
那个夜晚白玉宛静静地坐在院子里。
22
一切都在悄悄发生,一切都在渐渐消失,包括时间包括空间包括一切的规定,当然也包括恋情。
悲哀就这样产生了,无声无息地,如做了一场梦。
白玉宛是不是做了梦,当她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与一个男人躺在一张床上,发现自己赤条条一丝不挂,而那男人却正是屈小钱,她哭了,她被奸污了,她从床上爬起来,她穿好了衣服,她呆呆地望着窗外陌生的街陌生的人群。
她是在一个夜晚被屈小钱掳到县城来的,没有想到她竟被糟蹋了。
白玉宛真想杀掉屈小钱。
白玉宛洁白的牙齿把嘴唇咬出了血。
白玉宛身子在颤抖,心也在颤抖。
而屈小钱又一次从背后搂住了她,她挣扎,她嘶咬,但都无济于事,她的嘴被毛巾塞住,她的身子再一次被剥的精光。
她的泪水若瀑布般淌落,她要死去,她无力地任屈小钱在她美丽的身体上胡作非为。
她想念林箕天,她恨……
她心中燃烧着恨之火焰,她要杀死屈小钱,她会的。
她的眸子紧闭,她的心碎了。
以后的岁月将是黑暗的,她的眼前一片黑暗。
她哭着,阳光若飞瀑照射在房间里,照在她凄楚的脸上。
林箕天呢,他在哪里呢?他还在文学社办公室里吗?他走在路上,他匆匆忙忙,他寻找她吗?
那时街上吹着风,河岸上也吹着风。
白玉宛呢?白玉宛到什么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再见到她,林箕天与她的家人四处寻找,再没有见到她。
白玉宛被囚禁了。
这是一种悲哀。
林箕天从此学会了抽烟,他的脚下有一大堆还冒着青烟的烟蒂,林箕天的心焦虑,他担心白玉宛会出现什么差错。
纪春福、木青、铁文、陈莫,他们也都在关心着白玉宛,她往哪里去了呢?她肯定是遇上坏人了。
白玉宛的失踪给“秋野”文学社带来了麻烦。林箕天已无心工作,《乡韵》也宣布停刊一期。
镇党委政府非常重视白玉宛的失踪,让镇派出所迅速出动民警侦察白玉宛的去向。
但一天天过去了,就是不知道白玉宛到了哪里。
时光是飞快地过去了一年,人们开始失望了,认为是再也找不到白玉宛了。
而有一天纪春福的心猛烈跳动了一下,那不是白玉宛么?他飞快地追上去,而那人却在一个胡同口蓦地消失了。
纪春福呆呆地望了很久,叹息了一声,无奈地往回走。
自此纪春福有空便到那胡同口去,但一月两月过去了再没见那个熟悉的身影。
那是不是白玉宛呢?纪春福有时会这样想,有时他又很确认。
直到一个雨天,大雨若滚珠般急骤,他撑着伞在街上走,他穿过一条巷子到朋友家去,在一处拐弯的地方他忽然就发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透过雨帘他看见那人竟是短头发,穿着超短裙,双手紧抱在胸前,身子在雨里竟瑟缩着发抖,她没有撑伞,她是不是白玉宛呢?他想:“玉宛,”他还是叫了一声,那人便站住了,回过头来冲他笑。他望着,一下呆在了那里。
那人真的是白玉宛,但明显变了,一头长发剪掉了,本来清瘦的脸更明显的瘦,眼窝黑而深陷了下去,唇上涂了鸡血似的口红。
她还是白玉宛吗?还是当初那个美丽的白玉宛吗?
但她分明是白玉宛,她在笑。“纪春福,”她说。
他望着她被雨水淋的一身狼狈的模样,便走过去与她同撑一把桑“这一年多时间里你在哪里了?”他问。
而她不回答,她说:“春福,你能找个地方吗?找个地方我们好好谈谈。”
纪春福望她,纪春福点点头。
于是他们走进一家酒店里去,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下了,而白玉宛就要酒喝,纪春福望着她,脸上不禁露出了惊讶,“玉宛,学会喝酒了?”纪春富说。
白玉宛笑了一下,白玉宛说:“现代女人饮酒也是一种美丽呢?”
纪春福听了就更为惊讶起来,他没有想到白玉宛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他微笑了,他说:“玉宛,这一年多时间里你到了哪里?”
白玉宛没有回答而是一口气把杯子的酒喝干了,她叹了一口气。
“你怎么不说话?”纪春福又问,而白玉宛望着他就又倒满了一杯酒,但她又要喝时,就被纪春福伸手拦住了,纪春福说:“你怎么了?”
她一下拨开他的手,又一次把酒倒进肚里去,她脸有些红了,眼睛也显得有些湿润。
“你不要问我好么?我现在怎么了?”她说,“我一直这样的吧。”
纪春福望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木然了,她分明变了,变的不再是以前的白玉宛了。
“我一开始被屈小钱掳掠,受尽了折磨,”她开始诉说她这一年多的经历,“后来,屈小钱把我带到了南方,在去南方的路上,屈小钱的几个哥们儿相继把我给糟蹋了,我本来盼望林箕天会救出我,但是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都没有盼到,我绝望了,我心碎了,我学会了喝酒,醉了后我任他们奸淫我,我不会感到痛苦,唉、人好像就是这样的,所谓痛苦,尤其是心理上的痛苦,全部都是人自己制造的,现在我不再给自己制造痛苦了,我已不在乎,现在想来那一切原本是无所谓的,”她说,“至于跟谁睡觉,真的是无所谓的。”她这样说着眼泪就淌了下来。
想来,她只有用那样的话来安慰一下自己了。
“再后来,到了南方那个城市,”她继续说,“屈小钱就把我抛弃不管了,那个时候我一个人在那个城里孤单地走,我心里满是失落无助感觉,我不敢往家打电话,我感到羞耻,但我还是要生存,于是我到一家做了三陪女,现在有些人把干这行的年轻女子叫做边缘女孩子,”说到这里她的眸子里有了些光彩,但一闪就逝去了,“其实我真的不把与人睡觉当做一回事了,”她又说,“女人吗,女人总要与男人睡觉的,既是这样,就不必在乎是哪个男人了,何况像我这样一个早被男人糟蹋的不成样子的破女人呢?”她叹了口气,她又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现在就可以与你上床。”她好像是为了证明她很不在自己,竟很是无耻地说了这样的话。
纪春福感到了痛心和悲哀,他不想再听她讲下去了,他问:“你还记得林箕天吗?”
“记得,”她说,她低下头去,她好像一下子陷入了极大的不安中,“但你不要再提及他,”她继续说。
“为什么?”他问。
“不为什么?”他回答。
“到底是为什么?”他又问。
“不为什么,”她依然这样回答。
他笑了,他说:“你害怕见他对不对。”
而这次她不再说什么,她脸上的表情有些激动。
他就冷笑了一下,“其实你很虚伪”他又说:“同时你像一只空皮囊,你什么都没有了。”
白玉宛望着他忽然就笑,但他并没有说话,而是再一次倒酒喝下去。
“其实你也想见林箕天,因为你一直爱着他,”纪春福继续说,“你不愿提及他正是因为你还爱他,你没有勇气面对他,在他面前你自觉渺小可耻,你甚至不能正视自己。”
白玉宛听着他的话,她只觉他的话像一根根犀利的针直刺的她心滴滴淌血。
她的心在剧烈地颤抖,她的瘦削的双肩也在抽动。
她的头伏在桌子上,她哭泣了。
他就任由她哭泣,他知道其实她内心很苦。
她毕竟只是一个女人,严格起来讲她还只是一个女孩子。
当一个人陷入了困境,当她面对困难没有选择死,尤其像她这样受到严重摧残的女人还能够生存下来,就足以说明她是坚强的。
至于她为自己的选择辩说些什么,本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显得不很重要。
因为白玉宛毕竟还是白玉宛,她的良知并没有完全泯灭。
如今她回来了,并且坐在了他的面前。
他抓住了她的手,他说:“我通知你爹娘和箕天吧。”
“不!”她抬起头来,她说,“我……”但她并没有说下去。
纪春福就笑了。
那时候窗外的雨就停了,但有风在吹,风在嘶嘶的吹,直吹过街头去。
后来,纪春福回到家里,他把白玉宛的事告诉木青,木青叹息,木青说:“我见惯了现代都市生活,玉宛在都市里选择那条路并不稀罕,因为乡下人在城市里要生存太不容易了。”
木青说:“这是社会的悲哀。”
木青说:“最可恨的是屈小钱。”
23
白玉宛是做梦了么?大雨一定是在梦里下了。包括面前的纪春福也在梦境里了。而今她是坐在县城的一家酒店里,一张桌子边,面对了纪春福。
这不是过去,不是未来,是去了的已去了,来了的已来了,非梦境,不是虚幻的。
现实就是这样的,白玉宛面对着纪春福恍如踏入了梦境了。他她的心跳的“怦怦”,一条鱼在手心里猛烈地跳动。她哭了。泪水正若淋漓的雨。
她坐在那里。其实她已走在回家的路上,她破碎的心有了一丝希冀。她破碎的心何时未曾希冀。她笑着,坐在那里。
她坐在哪里呢?问题是她要不要回去?她想起了春敏,想起了在那个冷冷秋日悲愤投死的春敏。
她甚至想起了春敏的那条鲜艳的内裤,甚至想起了抚摸春敏尸体的那双兴奋的手。
她发觉自己的胃部一阵痉挛,她离开桌子向卫生间里跑去,她一阵干呕。
但当她走出卫生间,她发现大厅里竟空无一人,雨似乎早已停了,圆圆的太阳明晃晃的照着,有一种孤独的感觉像游荡的风一样侵蚀着她。
她很寂寞的坐在大厅里,她向外张望,外面的脸孔陌生而可恶,那些人的鼻子与眼以至脸色都那么地夸张,她处在那种情景里,泪水悄悄流下来,打湿了她已憔悴的脸庞。
她是哭着走出那家酒店的,她穿行在小城陌生的人流里,她像一只孤独的虫子爬来爬去。
这时,她就深深地想起林箕天来,那是一条深刻在记忆里的烙痕,她不敢去碰触,不敢去抚摸。
她害怕自己的心会掉入无底的哀伤的河里,害怕自己不能走出痛苦的围困。
她习惯了麻木的生活。
她走着,弄不清哪条是通往乡下的路,不知道自己是走在哪一条路上。
田野里一片水汽,明净的水面掠过轻柔的风,阳光的温情如芳香的唇,轻咬着大地上绿绿的草与树。
一切都似过去了又回来。她的心明明灭灭,她发现有什么东西已不切实际?
她定是走在乡间的路上。
回来了,她的感觉;(她飞舞的长发,清秀的脸庞,洁白的裙裾)她笑着,阳光照着她的脸,像照着一朵艳美的梅花。
可是她的笑容僵硬,她已不是以前的白玉宛了,不是了。
她从那辆红白相间的客车上走下来,她走在乡间的路上,路之上泥泞不堪,她的松高鞋上沾着了泥浆。
阳光是那么的照着,有一点儿异样。
她似乎走入了陌生的一群里,被异样的目光叮咬,她的心痛。
她的心原本在她家的闺房里,原本应平静的存在并生长,她的思想本应只属于这片土地。而现在她竟是漂泊流浪着;如今她竟如走在陌生的世界里,天空里有洁白的云,但如薄似蝉翼的衣衫,游弋的她的心飘忽闪烁,让她的身子小心翼翼的且抖瑟。
风是冷冷的吹着,吹着路边的小花小草,那太阳都有些苍白,她的灵魂竟似被什么一丝丝抽走了般,但仍在大地上行走,她走着,走回家里去,她脸上挂着笑,而没有院子的房屋仍用篱笆围着,篱笆边依然栓着一条狗,狗冲着她吠吠地叫,她的心在跳。跳的竟如乱撞的野兔与乱摇的草。
她走进了家门,望着瘦了很多的娘,望着大病不愈的爹,她的泪水若瀑布般淌落。
她的泪水打湿了双腮,她望着村边的那条河,望着河里那淙淙的流水,她的心被浸湿了,一定是被河水浸湿了,阳光里她曾随林箕天肩并肩在这里行走。
那时秋风吹着落叶,他说他与她会永远呆在一起。
而今大雨过后,田野里一片静寂。她不见林箕天的影子,她的心空洞而凄凉。
家门就在眼前了,她却感到恐惧和慌乱,她的脸发烫而赤红。
她忽然踌躇起来了。
她更加恨起屈小钱了。
路边有一棵枣树,她想起吊死在树上的春敏,她的手颤抖的厉害,她甚至要要丢掉挎包爬上树去,她甚至要……
她呆呆的站在那里望着那树,那是一棵什么样的树呢?她触摸,她触到了冰冷,触到了一根肋骨似的东西,插在大地之上,坚硬且枝繁叶茂,不肯倒下。她甚至听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故事,纠缠着,牵牵扯扯,很遥远的,很现代的,关于到粱山伯祝英台许仙白娘子,关于到徐志摩陆小曼,更关于到了春敏,那绝对是一棵凄凉忧伤悲惨的树,那树的皮肤光洁而冰冷,那树绿色的长发鬘鬘,她的心冰冷了冰冷了。她听到了,也看到了,千百年了,骨头是这般坚硬。
但她还是要走下去,她擦干脸上的泪水。她走过一条又一条的胡同。
谁家的小孩在哭泣。走在深深的胡同里,风里仍见墙上曾有红杏伸出的影子,那杏树的枝梢与绿叶正在墙外摇曳,她的心也摇曳着,摇曳着去找林箕天,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她的心里有一棵疯狂的草,在有风无风的天气里狂长,那是爱,不可遏制的爱情啊!而在乡下,她想着,乡下的爱情呢?它只是一棵野草,她也是,不敢理直气壮地走在大道上。
她就那样的走在街上了,低着头,摇摇摆摆。
她不望街上的人,她的心是那样的痛苦。
而有人就望她,终于认出来了。